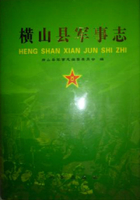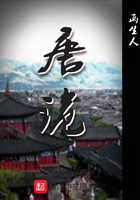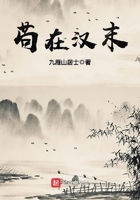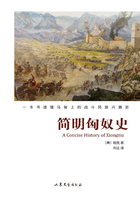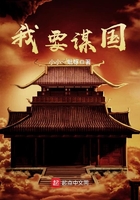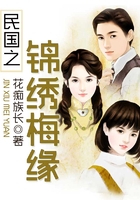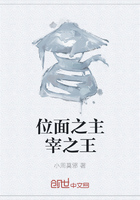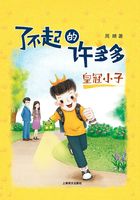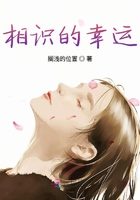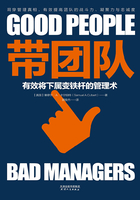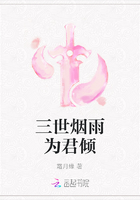一
冬日的江汉平原,若是雨天,那种辽阔的灰蒙蒙的色调,树林、牲畜、田野与村庄皆如烟凝,若真若幻,这是一种让人忧郁的景象,然而萧瑟并不冷清,枯寂并不衰败。不知为何,我一直喜欢在这样的冷色调中旅行。
现在,我们乘坐的面包车正穿行在江汉平原的冷雨之中。车上除了我,还有三位著名的学者,他们是王春瑜、王先霈与何镇邦。此行的成因是王先霈的一位学生在秭归县当领导,他邀请我们前去参观已经蓄水的新三峡。在我的动议下,临时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顺道去荆州城中拜谒张居正墓。
二
张居正的墓在沙市市郊一处名叫张家台子的地方,荆州与沙市两城合并后,该墓便在荆州城内。
我自1993年对张居正产生兴趣,从此开始了对他长达数年的研究。在这次拜谒他的墓园之前,我已独自前来凭吊过两次。第一次是1998年清明节。那时,我对张居正的研究和史料搜求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正准备选择一个吉日动笔写作四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清明节的早上,我独自驾车从武汉出发,沿宜黄高速前行约两百公里,至沙市站下。友人刘心宇君在出站口等着我,带我去墓地。约半个小时,我们的车停在一片泥泞之中,心宇领我走进一畦散发着粪臭的菜地,指着菜地中的一个土堆说:这就是张居正的坟墓。
尽管动身之前,我对该墓的毁坏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及至亲临其境,仍不免深深地惊讶。
这座在平地上垄起的土堆,陷在难以插脚的泥淖之中。墓的后头地势稍高,即当地人所说的“台子”(我不知道张家台子的地名,是不是因张居正的坟墓在此而得),上面盖满了两层的农舍。墓之两侧,左为民居,右为村人筹资修建的一座名为菩提寺的小庙。据说所用寺基,是侵占墓园的用地。
我走到墓碑跟前,两条裤腿溅满泥浆,而台子上的村民,莫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由此可以揣测,前来墓园拜谒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土堆前的墓碑是极其普通的米青石,显然是今人所立。没有任何雕饰,仅“张文忠公之墓”六个隶书大字,用油漆涂红。也许又经历了一段岁月,碑上漆色剥落,字迹开始模糊。圆土堆的一圈墓墙,用约两尺高的青砖砌起,年久失修,有几处已经倾圮。土堆上的蒿草欲青还黄,在艳丽的阳光下,格外引发人的沧桑之感。
通过询问与调查,知道这座坟墓即是明万历十年(1582)钦天监为张居正选择的墓葬的原址,但坟墓却不是原来的。盖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们信奉帝王将相无一好人之说,当过万历首辅的张居正,焉能放过?小将们遂成群结队前来掘墓。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三百八十多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入夜,一张姓老农(据说是张居正后裔)悄悄来到墓地,将被红卫兵丢弃的张居正的散乱白骨收拾起来,装在一个临时找来的陶缸里,在原地挖了一个坑予以埋葬。又二十年过去,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的曾得了妄想症的民族部分恢复了记忆,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不再一概抹杀。时任沙市市博物馆馆长的侯先生与陈先生,终于鼓起勇气要重修张居正的墓园。首先,他们找到那位老农,将张居正葬于陶缸的尸骨挖了出来。那个陶缸过于简陋,他们便让当时尚在博物馆工作的刘心宇找来一个精致的青花坛子,将张居正的尸骨再次收殓。然后,在当年被推土机推平的墓基处重新挖坑,将青瓷坛埋于其中,又把散于原地周围的断砖捡起做了墓堆的护墙,并立了一块墓碑,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一座坟茔了。侯、陈二人本来雄心勃勃,要建一座张居正陵园,并在今已盖了菩提寺的地方修建一座张居正纪念馆。他们把报告呈给有关领导,可惜没有下文。两位老先生现已退休,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张罗此事。
所以,我第一次谒墓,在满目荒芜的墓园听完刘心宇的讲述后,心境之苍凉可想而知。这苍凉中,既有为张居正死后数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感到的悲哀,更有为我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后代子民对先贤的麻木不仁而感到的痛苦。
三
我是在三十九岁的时候,才有意识地研究张居正这个人。那时,因为唐浩明先生的小说《曾国藩》,国人的确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我在坊间购得《曾国藩》读过之后,遂开始留意曾氏著作。后来在湘中名士王闿运的著述中,得知曾氏非常推崇江陵人张居正,说他柄国于“窳盐之极,其功尤伟”。我便开始搜求张居正的著作。不久,便买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主编的皇皇四巨册的《张居正集》,又从友人处借到了朱东润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张居正大传》。这便是我研究张居正的发端。
我在另一篇《让历史复活》的文章中,谈到研究中国的政治,首先要研究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皇帝系列,二是宰相系列。称职的国务活动家,是宰相多于皇帝。在中国那么多可圈可点的文治武功的宰相中,张居正无疑属于最优秀的一类。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张居正不但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汉以降,也只有诸葛亮与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拟。这是因为,诸葛亮只是蜀国的宰相,局促的舞台,不足以让他运筹帷幄,摇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错,但缺乏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同张居正相比,他更像一个文人。他的源头是屈原,而张居正的源头是申不害与霍光。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功绩,却是远远超过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为的皇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称太祖与成祖。其后的十几位皇帝,依次为仁宗、宣宗、英宗(中间有一位景帝干了七年)、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与思宗。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与穆宗比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别是武宗与世宗两朝,共六十一年,已经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穆宗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继位时三十一岁,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几件事来,怎奈穆宗素无大志,虽然俭朴本分,但沉湎酒色。所以,国政在他手上,仍没有什么起色。到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国家除边防稳固(这其中也有张居正的功劳)之外,内政几乎乏善可陈。官腐民败,政以贿成。斯时之皇权,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实际的控制力已相当薄弱。京师百里之外的地方,盗贼成群——这是民不聊生的显著特征。
远在世宗中期,张居正还只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就痛感国运的土崩鱼烂,朝廷中的官员庸多贤少,于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的宰辅之志,并不是入仕之后才有的,当他还是一个青衿学子的时候,便想成为当世的伊吕。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于得到首辅徐阶的赏识,张居正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而参赞入阁。他的这一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张居正四十二岁。幸运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洞开。历代的内阁,都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一是与皇权的摩擦,二是阁臣之间的斗争,很少有人能在那枢机之地待得长久。就是能够待在里头,也极难有所作为。张居正却是一个特例。从入阁到去世,他一共在内阁待了十六年,六年次辅,十年首辅。其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政权嬗变、人事代谢,他都安居其位,岿然不动。不言施政,单从为官的角度看,张居正无疑也是最优秀的。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饱暖思淫欲”、普通百姓“饥寒起盗心”的明代中晚期,这理想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但张居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未放弃自己的渴求与梦想。隆庆二年(1568),他入阁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过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这是张居正经过长期思考而精心写出的一份相当完备的改革文件。自商鞅以降,漫长的封建时代曾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但没有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陈六事疏》那样切中要害,而且富于操作性。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遗憾的是,穆宗缺乏从根本上改变朝局扭转颓败的勇气。他只是对《陈六事疏》说了几句赞扬的话,在西苑搞了一次阅兵,仅此而已。经过这一次试探,张居正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他仍隐忍地待在内阁,在保全自己权位的前提下,做一些于社稷苍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为太子的老师,随着太子朱翊钧的登基,张居正迅速得到重用,取代高拱当上了首辅。万历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时才正式拉开。
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在副职的位子上干得太久,骤膺大任,很难摆脱“小媳妇”的心态,缺乏总揽全局的才能与朝纲独断的勇气。用这一观点来衡量张居正,显然不合适。他从翰林院的编修干起,到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务长),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师)以及入阁为次辅,他做过的官,不是无关国计民生的文职,就是与大办事员无异的副手。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当过。这种出身,很容易流于书生意气。但张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磊落伟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两京不到三万名官员,被他裁掉七千人。仅这一举动,就令天下士林为之侧目,并因此指斥其“与天下读书人为敌”。面对汹涌而来的道德的责难,张居正不为所动。为了改革,他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的话,没有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则他所领导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历史的飞跃。
四
后世对万历新政的评价,大都持肯定态度。但奇怪的是,对万历新政的倡导者张居正,却颇多攻讦之词。细究其因,是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两部分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势豪大户,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清流。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其实,自商鞅至康有为,封建时代的任何一次改革,莫不是拿势豪大户开刀。举凡江山易主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产生痼疾。所谓太平盛世,就是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某种平衡。士农工商各有天地,政治清明民淳事简。在这种和平环境里,耽于享乐的人愈来愈多,于是,攫取财富的贪欲也越来越强烈。此情之下,那些把握权柄的人总是能够通过不正常的手段,掠取和占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的领导才能,使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分配。但是,在封建专制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家并不多见。
张居正怀着安邦济世之心,一心想救赎饱受苦难折磨的黎民百姓。当上首辅之前,他曾说过“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对贪婪的豪强集团不加抑制,则胆小怕事的百姓都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是在豪强集团与弱势群体产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一系列举措诸如裁汰庸官、整顿驿递、减少生员、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疏解了老百姓的困苦。当然,也把势豪大户得罪干净。
关于第二点,张居正得罪清流的问题,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的读书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条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题名后做官。张居正也是凭着这条途径而逐步攀上权力巅峰的,但他一直对官场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谈相尚的陋习深恶痛绝。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学同乡莫不欢欣鼓舞,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可是半年时间之后,他们便深感失望。张居正并不任人唯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锄!”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锄——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另一个例子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他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驭下”。同时代中,除了这部书,另有张居正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这一点,使他得罪了读书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他横加指斥,大肆挞伐。这不是张居正的悲哀,而是民族的悲哀。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五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对朱明王朝来讲,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是,直接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却并不这样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朱翊钧才十岁,一应国家大事,全凭张居正做主。张居正的角色,类似于摄政王。随着朱翊钧逐渐长大,特别是十六岁大婚之后,他亲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加之他生性喜爱钱财,为花钱的事,屡屡与张居正发生龃龉。久而久之,他对张居正由当年的言听计从变为内心厌恶。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钧即开始了对他的清算。家产被抄,爵秩尽夺,家人死的死,谪的谪。朱翊钧本还想开棺戮尸,在众多大臣的力谏之下,才罢止了这个念头。自此,人亡政息。
仅仅两年时间,万历新政带来的中兴之象,便消失净尽了。好货的朱翊钧,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开始了横征暴敛,国事越发地糜烂了。在他主政的最后十几年,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止。朱明王朝,终于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彻底崩溃了。
张居正死后的数百年,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每遇国难之时,总有睿智之士感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而遇太平顺境,便有人站出来替皇权讲话,斥张居正是“威福自专”的权臣。平心而论,张居正是爱权力,有独操权柄的嗜好。但更应该看到,他绝不是那种以权谋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确确实实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张居正死于京城,遗体运回江陵老家安葬。当年他的葬礼十分隆重,享受到赐祭九坛的规格,可谓达到人臣之极。但仅仅一年后,墓庐尽毁,并且从此以后再没有修复。1966年,早已沦为荒坟的张居正墓也没有被红卫兵放过,终于开了棺,扔了尸骨。三百多年前的万历皇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红卫兵手上终于做成。同在1966年,万历皇帝的尸骨被付之一炬。此前的1958年,他葬于万寿山的寝宫就被考古部门打开。这寝宫,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十三陵。朱翊钧与张居正,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君臣、师生,而后又成为明代昏君与明臣的两极,在同一年以不同的方式暴尸骨于世间,兴许,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六
第一次谒墓,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离开。到了第二年的年底,我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已经出版。武汉电视台《读书》栏目决定为这本书做一个专题。在我的建议下,摄制组随我第二次去荆州谒张居正墓。薄暮时分,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仍然是踩着泥泞来到墓冢前。依旧的残碑,依旧的荒草,同行的编辑与摄影师,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破败的坟包里,埋葬的竟然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杰出政治家。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后,在政坛、在史坛,得不到正确的评价还可以理解,但在自己的家乡,也遭受如此的冷漠则令人费解。我告诉他们一个小故事。此前,我曾在友人的安排下,与荆州的某位领导见面。我向他讲述张居正,意在引起他的重视,能够修一修这座荒坟。可是,他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回答说:“我正在规划,在荆州城内给关羽修一座中国最高的铜像。”我听了甚为奇怪,放着自己的乡贤不管,却要大费钱财去为隶籍山西的关羽造像,这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我想问他,但话到嘴边又打住。道不同难与为言,面对这样的地方官,我还能说什么呢?又过了三年,我的四卷本《张居正》已全部出齐,我得以有第三次机会到荆州谒墓。在车上,在雪意渐浓的景色中,我向三位学者讲述了我头两次谒墓的经过。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说:“你的《张居正》一书出版,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想必张居正的墓不至于那么荒凉了吧。”我也如此期冀,但这次谒墓,我们仍深深地失望。
三年时间,荆州城区的建设日新月异,新建了许多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合并后的沙市、荆州两城,中间的接合部成了美丽的新区。我们乘坐的面包车驶进城中,已完全找不到前往张居正墓地的道路。司机多次停车问路边的行人:“请问张居正的墓地怎么走?”被问者皆一脸茫然:“张居正?张居正是谁?不知道。”车子在城里瞎转,这时,我想起了定居北京的刘心宇,便打电话问他。他回答说:“你不要问张居正墓,你问菩提寺。”果然,一问菩提寺,路人都知道。我们终于也在颇费周折之后,再次来到张居正墓前。
比之三年前,这墓园除了对面新添了一座巨大的垃圾堆外,别无任何变化。一样的泥泞,一样的荒草,一样的残碑,一样的断砖……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绕墓一周,对残冢一揖,也只能感慨唏嘘。
谒墓之后,车向三峡。过枝江,丘陵渐多,辽阔的江汉平原已在身后隐去。但三次谒墓的感受,却在我心中拂之不去。当夜,在秭归的旅舍里,我写了七律一首,名为《再谒张居正墓》:
忍向荆州寻旧冢,三年凭吊我重来。
残碑更欲迷荒草,梵磬悠然怅客怀。
社稷频添龙虎气,英雄谁上凤凰台。
伊周事业千秋在,岂让丹心化作灰。
写完之后,我就想,待有机会再到荆州,一定要把这首诗,焚化在张居正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