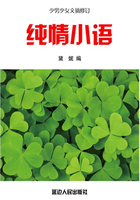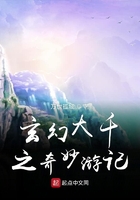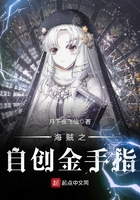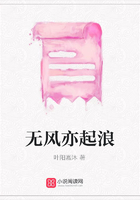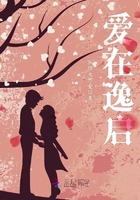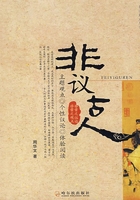村子里有几座零星的农庄,都有附属的干草堆场和放牛群的牧场。农庄上也有些村舍,里面住着牧羊人、马车夫或其他雇工,他们常年为同一个雇主干活儿。这些村舍可能是周边地区最好的了:不但房子更大更宽敞,连四周的空间也很大,靠近门口的地方还有个不小的菜园。十二个月雇佣期的体制已经受到严重冲击,但事实上,如果一家人能在某处定居生活,男人做长工,女人和孩子干点儿零活,日子无疑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些村舍并不属于任何农场——而是属于各种小业主——通常都十分不便,村舍拥挤闭塞,小径和公用通道经常相互交错,也就导致问题不断、争吵不休。
从整体来看,这村子找不到一点儿规划过的痕迹。就连犄角旮旯的地方都盖上了房子,甚至在小山的陡坡上都零星地散布着农舍,菜园位于至少四十五度角的平面上,这样,干起活来就会非常不方便。这儿有一片榆树,那儿有几间农舍,旁边还有一片狭长的条状农田一直延伸到村子的中心。还有更多的农舍是背对着大路而建的,屋舍的前门正好朝向另一边。这里还有一小片草地、一口井、一条很深的巷道——巷道很窄,每次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为了防止山上的石头滑落,巷道的两边还用粗糙的石头砌了堤岸——以及建在高处的农舍,非要走过层层台阶,拾级而上才能到达。这里还有块空地,三条弯曲的小路在此交叉相会,还有一处收费通行关卡,当然,紧邻关卡处还有一家啤酒馆。
每条弯曲的小路都通往一片农舍,每条小路也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是所有穿过村子的小径和大路都被口头上称为“街道”。辅路和房屋建筑都没什么规则,建筑风格独特,可谓十分随意;所有的农舍修得几乎一模一样,很像城里周边的那些现代建筑。当地的居民与他们的居所倒是颇为协调——大部分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他们的生活颇为随意。
这类老式住宅基本上都依烟囱而建。烟囱的主体是坚固的砖石结构,四周就是用碎石搭的矮墙。一旦农舍起火,几乎总是只有烟囱能得以幸存,然后农舍就会再次靠着烟囱修建起来。与烟囱的重要性相比,屈居第二位的是屋顶。屋顶就搭在矮墙上,然后一直向上拔高,实际上覆盖了一半的居住区域。
除了花园之外,农夫最渴望拥有的就是几间棚屋和厢房,用以存放木料、蔬菜等杂物,但是那些致力于设计“改良版”农舍的设计者往往都会把这一需求弃之不顾,绅士们总是急于让自己的雇工好好安顿下来,可这些新建的房舍却没有预想的那么令人满意。土豆、木材以及各种零碎物件对于物质条件不太丰厚的人们而言,价值自然要远超有钱人的想象。那些想要尽力为劳工阶层创造更好的居住条件的人应该牢记这一点。
紧挨着农场的庄园有一座农舍,里面住着一位踏实稳重的人,已受雇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或许在他之前他的父亲就已居住于此,屋里还有一些很上档次的家具。家具都是多年来一件一件慢慢购置的,有些还算得上是一份小小的遗产——手头有点小积蓄的村民都颇以立遗嘱为荣,还有些家具则可能是上一代遗留的财产中仅存的纪念。有些村民虽然祖上并不显赫,却也曾管理过甚至拥有过一处农场,但是家境逐渐败落了,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最后他们的子孙只能沦为在地里干活挣工钱的雇工——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那些在几代之前曾经放置在农场住宅之中的一把旧椅子或旧橱柜,如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
架子上有时还能找到一些书:《圣经》当然会有,能认字的村民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圣经》;还有用皮带捆扎的论辩神学的古老的书卷,可以追溯到宗教纷争相当激烈的时代,克伦威尔就是在那时显露头角的。书的卷首是一幅作者自制的粗糙版画,标题用红色的字母题写,前言冗长乏味,正文里到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引文。这些在村民看来极大地增加了书的价值,因为他们仍旧把懂得拉丁文知识看作是“有学问的人”的关键要素。显然,这本书已经作为传家宝传了好几代人,因为空白页上写着持有者的名字,还不可避免地标注了“他的”或“她的书”之类的文字。这一类的作品得以保存如此长久,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在这间小屋里,丝毫没有了那曾经使得十七世纪诸多纷争不断的教派得以建立的精神。不过,我知道有些人好像要重新恢复那些曾经激情洋溢地祈祷并参加战斗的剃短发的圆颅战士们所具有的精神特质。这些人仍然完全从字面上解读《圣经》,将其中的每个词当作上帝单独给予他们的启示,而且严格地按照坚定的信念来规范和塑造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人,通常白天在干草地里劳作了一天之后,晚上却可能在农舍旁给一小群虔诚的信众讲道。尽管只能有些费力地逐字逐句地通读圣经,他却早已把握了古代作家的风格,他可以用古老的风格表达自己,而且不乏实效。由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对内容产生广泛意义上的同感,农夫对圣经的内容自然理解有限,但他满心的热诚却是毫无疑问的。他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任何雄辩、花言巧语,甚至暴力都不能动摇他一丝一毫。他的信众也认可他说的话,时常发出长叹和惊呼。过去正是这一类人帮助克伦威尔获得了胜利,但在如今他们引人注目之处主要在于正直诚实、坚定沉着、无可指责的道德品质,以及稍显乖戾的特立独行。他们并非时下流行语中的“鼓吹者”,工人联合会在当地代理人好像是从完全不同的一个阶层遴选出来的。
我曾有一次停下来听这样的人布道,他正在路边的村舍里情绪激动地高声讲道,我发现他描述的是殉难者被宣判为异端后走向火刑柱的过程,语言固然粗鄙无华,却颇为形象生动。描绘这些情景时,他的想象力很自然地将其引向了让他自己从小就极为熟悉的田间景象。刽子手们拖着被锁链所缚的受害者,沿着小径穿过草地,最终来到准备要焚烧他的草堆。当到达第一处台阶时,他们停了下来,刽子手与囚犯发生了争执,刽子手许诺说如果囚犯改变立场,就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但后者至死不渝。
他们继续前行,刽子手一边走一边拷打折磨受难者,人群中传来嘘声和谩骂声。在第二处台阶,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了——许诺赐予宽恕,蔑视着拒绝改变立场,然后是更加严厉的拷打。再一次,到了第三处也是最后一处台阶,受难者接受最终的审讯,他仍旧坚持自己的信仰,于是被投到田地正中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这个故事无疑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讲道之人却将其染上了当地的色彩,使这个故事变得颇有个人特征。他谈论着绿草、鲜花、温顺的绵羊、柴草堆等等,把这些故事自然地镌刻进那些熟悉绵羊、柴草堆的听众们心中。随着故事的叙述达到高潮,听众们也会进入到极为亢奋的状态,直到故事结束时,讲故事的人用一声拖得长长的低吟作为结束语。没人为这些人支付报酬,也没人专门组织或训练,他们布道的原因只是为他人着想的善意。
不时地也会有女人在农舍小屋里讲道。小屋里十个、十五个甚或二十人挤在一块,空气简直令人窒息。有时她高声祈祷,其他人都大声应和。毫无疑问,有时候也会有不那么热忱的人纯粹出于虚荣和野心来这里布道——野心自然也是乡间生活的一部分,这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但我所提到的这些布道的男男女女都是真正虔诚、心怀热忱的人。
乡民都有自己的一套社会准则和传统习惯。在相互交往中,他们特别重视的一点是彼此了解或是熟悉。即便那些在道德准则方面称不上是最严格的人(乡下的道德有时真谈不上有多严肃),特别是妇女,也不会同意让陌生女孩在自己家里过夜,就算给得报酬丰厚,甚至由真正德高望重的人介绍来的也不行。乡下的女佣常被主人指派去看望需要帮助的情妇,她们常常要步行很长一段路,而那些地方甚至到现在都少有铁路,即便有,两站之间的间隔也非常远。女佣们若是走累了,当时也许天色已晚,再遇到旅店客满,她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乡民们的顽固则加重了她们的困难,除非恰好发现几年前见过这女孩的叔叔或表兄弟之类的人,否则他们绝不会让她留宿。
与这种冷漠相反的是,他们对朋友和邻居都非常友好,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如果说他们并不经常参加社交活动,那是因为他们白天经常碰面,在同一块田地里劳动,或许还十几个人在同一间外屋吃午饭。如果有他们认识的人从邻村前来拜访,他们也竭尽所能设宴款待。礼拜天,年轻人常常前去拜访几英里之外的朋友,和他们一待就是一整天。他们会带上些莴苣,或从园子里摘些苹果(具体品种据季节而定),把这些东西用花手绢包起来给朋友当作礼物。
一些上了年纪的牧羊人依旧穿着老式的长罩衫,包着白色的绲边就像粗糙的蕾丝。不过,年轻一代喜欢穿现代式样的厚外套,老人们会嘲笑他们说那种衣服在暴风雨席卷过毫无遮挡的山丘时完全不顶用。还有些老人用那种上个时代流行的巨伞,伞打开的时候堪比一个小型帐篷,能遮挡很大一片地方。奇怪的是,他们在田地里几乎从来不用伞,哪怕伞就在旁边也不用;但如果他们要沿着公路做短途旅行,就一定要把伞带在身上。老人用油绳拴住大伞挂在身上,就像士兵扛着毛瑟枪一样,如此他就可以把两只手都空出来——一只手拄着一根结结实实的木杖,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菖蒲编的篮子,脚步沉沉地走在路上。那根木杖比起男人们所用的拐杖要长很多,不方便走路,比起手杖来,它更像是个支撑:木棍顶端距离手的位置之上还足有六至八英寸之长。
如果说哪种劳动者有资格拿一份好薪水,那就是牧羊人了:很多农场整个一季的主要收入都仰仗于牧羊人的学识和忠诚度。到了产羊羔的时节,必须时时刻刻待在阴冷的山上精心照料羔羊。羊圈也会尽可能地修建在背风的洼地里,东面或北面就是突起的山丘,羊圈被建得就像厚实暖和的草墙,绵羊很快就会在里面弄出空隙来,因此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安居的洞穴。
牧羊人独立性很强,在自己的活动区域内,他通常要比一般雇工的观察力更加敏锐。他了解整个教区的每一片土地,知道什么样的天气与它的土壤最相配,并且,他只消看上一眼就能告诉你一处农场的大致情况。成天待在家里的人或许会认为这类知识微不足道,而实际上这需要记住整个村子方圆几英里内数不清的土地。就好像一位学生几年后还记得书的字体、纸张以及边距的宽度,还记得封面的卷边出现在他眼前,还记得长卷本书页的沙沙作响——他在图书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找到了它们。他激动地俯下身翻看,顾不得上面的灰尘、蛀虫,以及经年累积的味道——牧羊人也会回忆他的书本,那就是土地。因为这是天性,他天生就要在土地上流连,学习研究其中的每一个字母:羊群行进非常缓慢。
当树篱被挖走,山楂树开花的地方已然长出青草来的时候,牧羊人依旧可以给你指出各种树的位置——这儿是榆树,那儿是梣树。在山丘上,除了沉思外几乎无事可做,他把羊群放进洼地里吃草,自己就坐在斜坡上有草的地方等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因此,他逐渐养成了观察的习惯——观察对象总是与他的职责有关。即便在不当值的时候走过教区,牧羊人也准能注意到庄稼的长势如何,以及何处“饲料”最多。他们是所有行当里最后一个抛弃打长工的旧习惯的,当雇工们辗转奔波工作时,很多牧羊人依旧终生只在一个农场上工作。因此,得益于多年的观察习惯以及在某地的长期停留,牧羊人常常是当地的权威;一旦有了边界、水源和通行权之争,最终的裁决权通常会交到他们手中。
古老的绿色小径和马路过去曾来往交错从乡镇穿过,通向四面八方。但是随着年头渐多,这些路越来越少,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有时候,人们希望能封住小径的一部分用来盖房修屋。有时候,由于人口大量增长,马路就变成了十分重要的大道,随之出现的问题就是:路该由谁来修呢?这样的事情基本找不到记录——它只能借由人的记忆去追寻。于是,人们就找到老牧羊人,因为他在这里待了一辈子,还能记得五十年前到现在关于小路的情况。他总是赶着羊群在小路上走——一是因为这可以节省过路费,二是这样一来,羊就可以吃些草并且在厚灌木丛的树荫下休息。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他也并非全无用处,最后,往往是牧羊人发话解决了问题。
一场大雪之后,在冬日黄昏的暮光下,人们很难从大片的耕地上找到路,因为南边每条犁沟里的雪都融化了,只留下一条白线延伸到北边,直到最后犁沟变成了地面上连绵起伏的波浪,浪顶上覆盖着泡沫一般的白雪。积雪白茫茫的,十分晃眼,这里也没什么树篱或树木之类的可以用来引路。在北面的山坡上,有时雪一下就是几个星期,那里原本有些可用作地标的干涸的浅沟,如今也落满了积雪——昏暗的山体就像漆黑的船身上描画了白线。在这段被称为“圣诞前的黑夜”的时间里,地里几乎没什么活儿,人们不得不找些乐子度过漫长的夜晚——比如以酒作赌注,在啤酒屋用前膛枪打灭蜡烛,实际上如果距离不远的话,软帽扇出的风就可以把蜡烛熄灭了。
孩子从来不会忘了圣托马斯节,按照古老的习俗,这是布施的日子,孩子们从一处农庄走到另一处农庄,直到走遍整个教区来募捐。这样的活动一般局限在教区之内,尽管如今已是一个四海为一家的时代了,有些古老的、本土化的情感依然得以留存。到了圣诞节,孩子们有时候会唱颂歌,不过很难跟上旋律,但是别的方面还都相当不错,哪怕最坚硬的心也会被以往的记忆所软化。
几个星期以来,年轻人都在排练哑剧——尽管看似简单粗糙,但其实和那些在知名剧院上演的剧目一样,事先都需要经过大量排练。他们着装奇特,头戴面具,身缠彩带,怎么怪异怎么来,因为他们不太依照角色的身份性格进行着装。他们串遍自己教区内的每一处农庄,在厨房和酿酒间表演,结束之后,这些演员们还会被招待喝点啤酒,拿点儿小钱,然后他们就继续到下一家去。不过,如今哑剧比起以往已经衰落了不少,最近的十五、二十年间尤为严重。过去,如果预先得知演员们晚上要来,除了农场主一家以及他们当季的访客外,住在附近的乡民也都会聚过来,所以那时观众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现在演员会不会来已经是说不准的事了。
更受年轻人欢迎可能也更赚钱的娱乐活动,大概是组织铜管乐队。他们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兴致勃勃地排练,有时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只要时节合适,他们晚上就到农场上去演出,由于农场之间相隔较远,收工后剩下的时间就只允许他们访问一部分人家,穿越整个教区可要花掉不少时间。所以在年关前后的两三周,人们如果晚上外出,就可能在不经意间听到有小号声从田地里传来。近几年,请铜管乐队的习惯日渐增长,这些乐队也得以赚了不少的钱。
教堂的敲钟人也来了。他们站在窗前,踩着冻得干脆的绿草,将手铃摇出动人的声音——只不过,用手铃摇出的旋律总是显得哀伤。他们总会报酬丰厚,因为整个乡间的人们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铃声。
还有什么声音能比拉车的马脖子上挂的小铃铛的叮当声更悦耳呢?距离三弗隆远的时候,你就能听到一队人驾着满载稻草的马车而来,你若离开大路就能看到这些身躯庞大但体格匀称的马是如何将满满一车沉重的货物拉上山的。马的四肢泛着光泽,稍有些紧绷,但它们还是高高地昂着头,露出高贵的脖子,马蹄自豪而有力地踏在路上,擦得锃亮的黄铜马具闪闪发光,而那铃铛就发出悦耳的叮当声!车夫把马鞭甩在肩上,跟在车辕旁边走,他小助手走在前面开路,他对车队的感情就像水手对他的船一样无比自豪:连鞭子都不是随便拿的,必须要精心挑选,上面绑上一串黄铜的圆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打出的鞭绳是不会让他满意的。
因为即便是看似如此简单的小事,也有其特定的艺术,不经长时间的反复练习难以掌握其要领。车夫对马鞭、马具和马队所具有的自豪感要比除了周末的薪水之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陌生人要好得多。现代体制——人们今天来了,明天又走——没有给这种感情的成长留下空间,手工技艺的艺术与奥妙也就失去了其特有的魅力。如今马具上的铃铛逐渐消失不见了,二十支马队里能找到一支队伍挂铃铛的就不错了。
在农田里干活的人,他们的假期似乎要比在城里做工的人少得多。复活节假期的时候,会有大批工人从城市的工厂和仓库兴冲冲地回到乡村,他们在圣灵降临节也有假期。但是那些时候,农场主和工人却依旧要干活,银行或工厂歇业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停止耕种或放牧。到了五月份,村里的孩子仍然会记起国王查理;至于到了他们称之为“棚屋节”的日子,他们就找一些栎树果和栎树嫩叶,把梣树枝编在帽子或别在扣眼上:梣树枝上的叶子必须是偶数,奇数可不行。直到最近二十年,人们还认为必须佩戴这些绿色徽章,农工们几乎没有不戴的。老人们会告诉你,他们记得有一年春天来得很迟,人们苦苦搜索,却没人能找到栎树果或叶子——他谈到这一切就好像在诉说一场巨大的不幸。近来,这一习俗已经逐渐没落了,不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马车夫还是会把梣树枝和栎树叶别在马的头上。
很多乡村俱乐部或互助会都是在春天聚会,也有的是在秋天。聚会的时间有时是根据古代筵席的日期定下的。事实上,因为互助会受到当地家境好的居民的资助,俱乐部和游园会对筵席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几乎取而代之了。不过在很多地方,筵席日还在居民的记忆之中(这一天也是做礼拜的日子),比如在这个村子,年长的扬谷人会邀请他们的朋友过来,慷慨地招待他们一番。虽然还会有一群吉卜赛人带着货摊过来参加,晚上也有一小拨人聚在一起,但筵席的真正意义已经不再了。
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天还是会触发老人们的记忆,他们每年都会在日历上标出当地的大事,筵席日就是其中之一。在某个特定月份第一次满月后的很多年,才会组织一场集市;下一场则又要过很久。老人能告诉你方圆十到十五里内全部村庄市镇每场市集的时间,他并不在意现代的计时系统,而是依旧按照古代的教会历和月相判断时间。那些古代方法竟已在他们的生命中打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使他们在今天仍旧保有这种本能!
一部分筵席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些与自然有关的特定事件,它们会在日历上被标记出来,“樱桃成熟日”就是一例。你会发现,某些日子如果恰能和正常水平下水果的生长状态相吻合,这样的日子就比没有这种联系的节日好记。对于邻近的市镇来说,报喜节集市和米迦勒节集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这个集市有时也被叫作“雇工市集”,为了赶集,健壮的女孩宁可走上八九英里的路。在有集市的日子里,农场的女佣们总会向主人讨一个假期。对于乡下人来说,这两个大市集持续的时间也是公休日。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铁路和工厂都没能撼动这些集会的声望。
比如说,你可能会注意到某些市镇,由于铁路的铺设和工厂的建立已经远远领先于别的地方(那些地方依旧小而冷清),人口也许翻了两三倍之多,贸易量大概增长了十倍,吸引力之大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在这里每年举办的集市的重要性却远远比不上在那些远离文明洪流的沉寂旧世界举办的集市。后者也许离大路八九英里远,没有通信设施,在年代尚不可知之时就以集市闻名了。散居在各处的乡民定期就去那里赶集:他们不在乎距离多远,也不太在意天气情况——乡下有谚语说,有集必有雨,雨多携风雷。在集市上,人们聚在一起,按老传统享受生活——比如在大街上站着,给女孩买礼物,为了赢坚果参加射击比赛,观看各种演出等等。
要想从这样拥挤的人群中找出一条通道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乡下人并不是刻意要表现得粗鲁,但他们也丝毫没有意识到礼貌需要一点点谦让。你只能推开他,当然他也不会反感。在城里,人群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活动的——每个人都有让路的意识。但在乡下,人们往往像石头一样站定不动。
在演出现场,鼓的雷鸣、小号的巨响、排箫的反复吹奏振动着空气,那喧嚣之声在几英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乐声也给人群带来了极致的欢乐——冷溪卫队的一流乐团的影响力也难与之相匹敌。马戏团的人在讲解表演的时候,村民们毫不厌烦地盯着那只“旷野的鹈鹕”一动不动——这只鸟神色哀伤,低垂着羽毛站在入口处,这是传统表演的保留项目。还有一点同样引人注目(事实上这可能是最令人惊奇的一点):全村所有的人都聚在了这里。打工的男人女人们都从很远的村子赶来与朋友会面,他们已经数月没有见过彼此或是收到彼此的消息了。大半个村子的闲事都会被他们八卦一番。
秋收过后,对于村民来说捡麦穗的时节仍然十分重要,只是无法与从前相比了。如今机器大大提高了收割的速度,而且剩下的麦穗也不如原先那么多了。然而,当地还是有一半的妇女和孩子都出去捡麦穗了,只剩下很少的人在家里烤面包。村民现在都从面包店里买面包吃了,烤面包的往往是周围偏远小村落的人。过去他们很可能吃得更健康一些:那时,他们把捡来的麦穗送到村里的磨坊磨成粉,再把面粉带回家烤成面包。但是,机械师的狡黠打破了古老的习俗,现在收割机直接就把麦子打成捆了,乡村的下一代人恐怕很难理解《路得记》的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