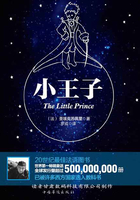终于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临上车前我又一次犹豫着是不是给爸妈打个电话,从上大学开始,他们还能固定的每月给我打个电话,话题永远是钱花完了么?要寄多少?除此之外再无一句关心的话语。毕业工作后竟然连这大姨妈一般规律的电话都不来了,偶尔我打回去,告诉我的也只是大姐夫帮大姐把宝莱换成了宝马;二姐相亲了,对象是某某局长的公子……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而我需要的,并不是聊这些。
“喂,阿姨啊!我宇城啊,我和依依一起参加了考古队,马上要出发了,依依让我拨个电话给您,您稍等啊,我叫她讲。”说完周宇城就把手机塞进了我的手里。
“妈……”喊完了,竟然不知道要讲什么。
“依依,你要去哪里考古啊?怎么宇城会和你在一起啊?”我妈居然良心发现的主动关心起我来了。
“这次考古是他爸出资赞助的,整个课题小组一起行动,宇城也参加了。”
“哦知道了。”我妈说完就有要掐了电话的意思。
“妈……等等……”我迫不急待。
“怎么了?还有事吗?”口气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平淡。
“哦,没什么事!您和爸,注意身体。”
“知道了。”说完那头就传来了短促的嘟嘟声。
很郁闷地把手机还给了周宇城,起身上了车。
列车就这么载着来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的牛鬼蛇神,在平行的铁轨上欢快的飞奔。过道里汗臭味,狐臭味,脚臭味,方便面味,酒味不断的混合又分开,强奸着每一个人的鼻孔。我强忍着想从行囊里拿出一只防毒口罩的欲望,爬到了暂时属于我的上铺,将铺位上已经发黑的毛毯扔到了一旁。盘腿坐在上铺摇头晃脑的听起了音乐。听了一会感觉到有人在扯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周宇城,嘴巴一张一合在对我说话,我赶紧拿掉了耳机。
原来我在订火车票的时候低估了周宇城的承受力而买了硬卧,估计他忍受目前这种脏乱差的环境已经到了极限,因此强烈要求与我换铺位。
“周公子,您可想好了,这上铺价格可是所有硬卧票中最便宜的。之所以这么便宜呢,是因为,一般有味的气体都比空气要轻,所以呢,它自然会往上飘,咱这头顶上呢,又没别的地方能发散,只能聚集在车厢顶层……”
我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算了算了,我去餐车坐一会。”
“呀小样,居然还知道火车上有餐车?”我之前还真以为周宇城没坐过火车,只见他理都不理我,头也不回的向餐车方向走去。
我、周宇城和穆子真安排在了一侧的上中下三个铺位,苏教授坐在对面下铺的位置上望着窗外不断出现又消逝的风景发呆。周宇城还没从餐车回来,我滑到下铺轻轻捅了捅正在闭目养神的穆子真,示意他研究研究苏教授,这老头刚上火车的时候还和我们聊了几句,从周宇城去餐车后就开始发呆,到这会已经维持着同一个姿势好几个小时了,我怕他再这么坐下去就石化了。
穆子真睁眼看了看,又闭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师遇到激动的事就平静了。”
我不理他,调头看向坐在苏教授铺上的另一个人,这人估计是买了中铺还是上铺的票,这会没睡意就一个人坐着抠脚丫子玩,我估摸着周宇城也就是被他这样子给赶去了餐车,我不禁皱了皱眉。那人估计是之前没注意到有女人,看到我厌恶的表情,脸噌的一下就红了,赶紧穿上袜子放下了脚,只是……却没有去洗手。
这会子列车员大叔领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过来,指着我的铺位对那姑娘说:“你就换到这儿吧!”
“啊?”我抠了抠耳朵,“等等,这儿是我的铺位啊!”
“啥?你的?车票呢,检票。”列车员大叔不理会我无辜的表情。
我竟然被他一吼吓得抖抖索索的从衣兜里翻出车票,大叔在仔细核对了几遍后,微笑着转向那姑娘,指着苏教授那侧的上铺说:“对不起,弄错了,你换的铺位在这儿。”说完就要走,被我喊住了。结果他一转脸,又黑了180度。
“那个……大叔”我声音低得象蚊子,“你车票还没还我呢!”
大叔那黑透了的脸又渗出了一丝红,在我眼里看出来象是紫色:“给你!”说完扭头就走。
“靠,这啥态度。”我小声嘀咕。
“对不起啊,姐姐。”说话的是那小姑娘:“其实这位列车员人挺好的,我之前在座位上遇到了咸猪手,找到了他,他就帮我安排到这儿了,他也不是大叔,我刚才跟他聊天的时候得知他30都不到。”
“不是吧,这么显老。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就一个人出远门啊?”
“哈哈,所有人都以为我年纪小,其实我已经25了,原来常驻外地,这次被单位紧急召回。”
连续认错两个人的年龄,我开始严重怀疑自己的眼神了,我把头转向抠脚男,“喂,我说你27岁,对不对?”。
抠脚男估计没料到我会忽然对他说话,傻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你……怎么知道的?”
确认我的眼神恢复正常以后,我冲他们挥了挥手,找餐车去了,周宇城那小子在餐车待了那么久,不是要把全车的食物都掠夺了去吧。
虽然是卧铺,但我向来认床,当我们风尘仆仆到达兰州的时候,又顶上了两只熊猫眼,还有另一只熊猫,周宇城。前来接我们的有两个人,都是苏教授的老友。一位是西北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罗仁峰,面子很大啊,所长亲自驾车载我们回去,把另一位资料室的秦严留在火车站,据说研究所有位驻外地的队员回来,将会是加入我们考古队的成员之一,让秦严负责把人接回来。
在招待所把自己折腾干净,吃完午饭就在研究所的会议室内集合,罗所长为我们介绍了即将加入队伍的成员,一位是研究所的研究员何昌荣,算起来也是我们半个师兄,早些年也曾在苏教授门下,戴着厚厚的啤酒瓶底的眼镜在道上也混了十来年了,另一位是看上去文质彬彬白脸小生朱新乾,我听到这名字憋笑憋到内伤。
“这次加入你们队伍的还有另一位研究员,之前她一直驻北京工作,这回我们急召她回来是因为她一直从事西北古文字的研究,虽然很年轻但也小有一番造诣,希望……”罗所长话还没说外,门外就传来银铃一般的笑声,随着笑声进入会议室的,不正是昨天火车上遇到的姑娘么?
来人进门也认出了我们,立刻显得非常兴奋:“天呐,原来是你们啊?”
“怎么你们认识啊?”罗所长一脸纳闷。
“是啊,我们坐同一列火车来的。”
“那太好了,我介绍下吧,这位是梅晓,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次打断罗所长的是周宇城。
终于,在进行完紧张的会议和休整之后,我们向着茫茫沙漠迈进了。车子渐渐地越开越荒凉,道路也慢慢变得颠簸崎岖起来,本来这种面包车坐着就不舒服,在经过我认为十分漫长的活络筋骨的活动之后,我们到达了营地,沙漠的边缘地带,之前联络的当地向导巴赛木老人已经在营地等待了,据说巴赛木在回语里有喜气洋洋的意思,老人长得很配合,很有喜感,每次一见到他瘦长的月牙脸我就不禁想起木偶阿凡提,不过这两个人似乎不是一个民族啊?看来全国人民一家亲是正确的。
所有的人东歪西倒地下了车,看来骨头散架的不止我一个人。
安营扎寨,生火做饭,周宇城忽然之间化身为野外生活的老手,熟练地指挥并操作着一切,原来他是做足了功课才来的。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负责生火做饭的朱新乾一定是来拖后腿的,自己抹成了大花脸不说,生堆火还是时有时无。不过也难怪,原本我们是打算用卡式炉的,但巴赛木老人带来了许多柴火,想到进入沙漠后可能卡式炉更需要,因此决定在营地就生柴火做饭了。眼瞅着刚燃起的小火苗又一次被他残忍的毁灭了之后,我实在忍不住了。
“猪心肝,你长这么大都没生过火吗?”
“你……你叫我什么?”
“猪心肝啊,让开,我来。”
虽然我之前也没有在野外有过生火经验,但一向自诩聪明伶俐的我自认为与农村外婆家的大灶台生火属于异曲同工的原理,在这种原理的坚持下,一堆旺火很快就冉冉而升了。
“你……为什么那样叫我?”朱新乾的小白脸在火光的照映下红彤彤的。
“你难道不知道‘乾’是‘干’字的繁体吗?”
“我知道,可是……可是我……这个字不是……不是干的繁体。”有些人一激动,就口吃。
“我知道,但那样我就不能给你起外号了不是?”
“你喜欢给人起外号吗?”
“也不是啊,看顺不顺眼了。”
“你看我不顺眼啊?我哪里……哪里惹到你了?”
“不是,是顺眼的才起外号。”
“那我们这些人里面,哪些人有外号?”猪心肝听到我只给顺眼的起外号,忽然就来了兴致。
“闹,那个出钱的冤大头,家里钱多没地方花,被老爷子送来沙漠烤人肉顺便找老爷子旧情人的,叫周公子;我那个同门师兄,我一直叫他‘小真真’,其实这严格来说不算外号;至于教授么,跟大多数人一样,当面叫老师,背后叫老板;你们的何研究员,我打算叫他啤酒叔;梅晓我打算叫小梅梅;你的外号你自己已经知道了吧;哈哈。”
“为什么管何老师叫啤酒叔啊?”小猪同学一脸好学的表情。
“啊?难道你没发现他的眼镜片就是啤酒瓶底吗?”
沉默……沉默……忽然……“哈哈哈哈……”小猪同学边笑边滚在了地上,所有的人都注视了过来,以为他肚子疼。
我很严肃地看着滚在地上的小猪同学,想得脑袋疼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在我看来很淡定的事儿,到了他那里能有这么强的喜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