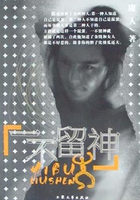牛河不得不一度放弃收集关于麻布老夫人的信息。他明白她身边设置的警戒线过于坚固,无论从哪个方向伸手,都会立即撞上高墙。他很想再打探庇护所的情形,但在那附近徘徊得太久会有危险。四周安装着监控摄像头,而牛河又生就一副惹人注目的外表。一旦招致对方警惕,以后就难办了。暂且远离柳宅,尝试从其他渠道调查吧。
而能想得到的“其他渠道”,无非是将青豆周围的情况重新调查一番。上次他是委托打过交道的调查公司收集资料,也亲自四下打听,制作了一份关于青豆的详细档案,从各种角度详加验证后,断定她没有危险。作为体育俱乐部的教练,她能力极强,声誉甚佳。年幼时曾经是“证人会”的一员,十岁之后退会,和教团彻底断绝了关系。以近乎第一的成绩毕业于体育大学后,在一家以体育饮料为招牌产品、在行业间是中坚力量的食品公司就职,作为垒球部的核心选手大显身手。据同事称,她不论在垒球部还是工作上都是优秀人才,积极热情,头脑也聪明,周围的评价很好。然而寡言少语,交际不广。
几年前忽然退出垒球部,从公司辞职,在广尾的高级体育俱乐部任教练,因此收入大约增加了三成。独身,一个人住,目前好像没有恋人。总之,根本没发现可疑的背景和不透明的因素。牛河皱起眉,喟然长叹,将反复研读多遍的档案扔在桌子上。我肯定看漏了什么。看漏了不该漏下的、极为重要的东西。
牛河从桌子抽屉中拿出通讯录,拨了一个号码。如果需要非法获取某种情报,他总是往那里打电话。与牛河相比,对方是生存在更为黑暗的世界里的人种。只要付钱,大多数情报都能手到擒来。当然,对象的防范越是森严,费用就越贵。
牛河索要的情报有两宗。一宗是青豆那至今仍是“证人会”忠实会员的父母的个人信息,牛河坚信,“证人会”统一管理着遍布全国的信徒的信息。日本各地“证人会”信徒人数众多,总部与各地支部间的往来与物流也很频繁。总部若没有储存信息,整个体系肯定无法顺利运作。“证人会”总部设在小田原市郊外,宽广的地盘上耸立着漂亮的楼房,拥有印刷小册子的工厂,还设有给来自各地的信徒使用的集会场所与住宿设施。所有的信息肯定都集中在那里,严格地管理着。
另一宗是青豆供职的那家体育俱乐部的营业记录。她在那里担任何种工作,何时给谁进行个别授课。那里的信息大概不会管理得像“证人会”那般严格。然而,如果直接登门拜访:“对不起,能不能让我查查青豆女士的工作记录?”注定只能被拒之门外。
牛河把姓名与电话号码留在了电话录音里。三十分钟后,电话打了过来。
“牛河先生。”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
牛河将要求详细告诉了对方。他从未跟此人见过面,始终通过电话交谈,此人将搜集到的情报快递过来。嗓音有些嘶哑,不时混杂着轻轻的干咳。也许是喉咙有问题。电话那端永远是完全的沉默,简直像在有完美隔音装置的房间里打电话。只能听见对方的说话声以及刺耳的呼吸声,别的什么也没有。而且传过来的声音都有些夸张。真是个可怕的家伙!牛河每次都这样想。世上似乎充满了可怕的家伙(在旁人看来我大概也是其中之一)。他暗地里给对方取了个外号,叫“蝙蝠”。
“这两方面,都是弄到和青豆有关的情报就行了吧?”蝙蝠用嘶哑的声音问道,干咳一声。
“对。这个姓很少见。”
“需要全部的情报?”
“只要和青豆这个姓沾上边,什么情报都行。可能的话,最好能搞到照片,可以看清脸部的那种。”
“体育俱乐部那边大概很简单。他们肯定想不到会有人来窃取情报。‘证人会’可有点困难。他们组织庞大,资金又很充足,防范可能也很森严。宗教团体是最难接近的对手之一。因为有保护个人隐私的问题,还牵扯税金的问题。”
“能办到吗?”
“只要去做,就总能办到。我有相应的撬门办法。更困难的是撬开之后,还得把门关好。不然,说不定会有导弹追击过来。”
“就像战争一样。”
“就是战争。说不准会有什么吓人的东西钻出来。”对方用嘶哑的声音说。从音调中就能明白,他似乎在享受这战争的乐趣。
“那么,能请你帮忙吗?”
一声轻轻的干咳。“我试试看。不过价格看来得相应地提高一些。”
“大约得多少钱?”
对方说了个大致的金额。牛河暗暗倒吸一口凉气,接受了。反正是自己能负担的金额,况且有结果的话,这些钱以后也能报销。
“要花很长时间吗?”
“你要得很急吧?”
“是很急。”
“无法准确预计,但我看起码得一周到十天。”
“这就可以。”牛河说。这种时候只能顺应对方的节奏。
“资料弄齐后,我给你打电话。十天内肯定会跟你联系。”
“如果没有导弹追击过来的话。”牛河说。
“对。”蝙蝠若无其事地答道。
牛河挂上电话,靠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蝙蝠是如何通过“后门”搜集情报的,牛河不清楚。他知道就算张口打听,也不会得到回答。总之,无疑是采用不正当手段。首先能想到的是收买内部人士。若有必要,说不定还会私闯民宅。如果牵扯电脑,事情会更加复杂。
使用电脑管理信息的政府部门和公司还很少,既费钱又费功夫。然而全国规模的宗教团体肯定有这样的余力。牛河对电脑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也明白那正逐渐成为收集资讯必不可缺的工具。亲自跑到国会图书馆,将报纸缩印版或年鉴之类摊在桌上,花一整天搜寻信息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于是,世界或许将沦为电脑管理员与入侵者之间的血腥战场。不对,不同于一般的血腥。既然是战争,流血大概是难免的,然而不会发出气味。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牛河更喜欢实实在在地存在气味和疼痛的世界,纵然那气味和疼痛有时会难以忍耐。但总而言之,牛河这种人一定会迅速化作落后于时代的遗物吧。
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变得悲观。他知道自己有本能的直觉,能凭借嗅觉器官嗅出周遭的各种气味,能根据肌肤感到的疼痛把握风向的变化。这是电脑无法进行的工作,因为这些能力是无法数字化、系统化的东西。巧妙地进入严加防范的电脑系统中窃取情报,是入侵者的工作。然而判断应当窃取何种情报,从窃取到的大量情报中选出可以利用的东西,却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做到。
我也许是个落后于时代的中年丑男人,牛河暗想。不对,不是也许。毫无疑问,我就是个落后于时代的中年丑男人,然而拥有几种其他人没有的资质。天生的嗅觉,以及一旦咬住便死不松口的执着。迄今为止,我一直靠着这些混饭吃。而且只要有这些能力,不管是怎样稀奇古怪的世界,我肯定也有地方混饭吃。
我会追上你哦,青豆小姐。你头脑反应很快,能力高强,为人又谨慎。不过嘛,我一定会追上你。你等着瞧吧,我现在正朝着你的方向走去。你听见我的脚步声了吗?不,你肯定听不见。因为我就像乌龟一样,悄悄地走路。不过一步接着一步,正在接近你。
但反过来,也有东西正在逼近牛河的背后。那就是时间。对牛河来说,追踪青豆,同时也是摆脱时间的追踪。必须迅速发现青豆的行踪,查明其背后关系,盛在托盘上说声“来啦,请慢用”,端到教团那帮家伙面前。给自己的时间有限。事过三月后才弄清一切只怕太晚。到现在为止,牛河对他们来说是个有用的人才。精明能干,头脑灵活,拥有法律知识,守口如瓶;又远离体制,行动自由。然而归根结底,无非是个花钱雇佣的“路路通”。不是自己人,也不是同类,全无信仰之心。一旦对教团来说成为危险的存在,恐怕会被毫不留情地除掉。
等待蝙蝠来电的时候,牛河前往图书馆,详细查阅了“证人会”的历史和现在的活动状况,做了笔记,必要的部分则复印下来。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他来说不是苦差事。他喜欢逐渐在脑中积蓄知识的真实感。这是从小时候起养成的习惯。
在图书馆查完资料后,又去了青豆住过的自由之丘的出租公寓,再度确认那里已是一座空屋。信箱上仍贴着青豆的名牌,但是房间里毫无有人住的迹象。牛河还找到了管理那间房子的中介,问道:听说那座公寓里有空房间,是否可以租用?
“空是空着,不过明年二月初之前不能入住。”中介说。与现在这位房客签订的租赁合同要到明年一月底才到期,到那时为止,每月都按老样子支付房租。
“行李全部运走了,水、电、煤气也都办妥了迁移手续。可是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就是说到一月底为止,一直为空房子付房租?”
“您说得没错。”中介答道,“说是全额支付合同期间的房租,希望维持房间现状不动。当然,只要支付房租,我们这方面没有理由说三道四。”
“好奇怪。明明没人住,还要白白付房租。”
“我们也有点担心,所以就请房东在场,进屋去看了一下。万一壁橱里扔着一具已经变成木乃伊的尸体,麻烦可就大了。还好,没有任何东西,打扫得干干净净,就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青豆当然早已不住在那里了。然而他们基于某种理由,试图维持青豆仍在租赁那个房间的名义,为此竟然继续为空房支付四个月的房租。这帮人非常谨慎,而且在资金上毫不拮据。
恰好在十天后的下午,蝙蝠给麹町的牛河事务所打来了电话。
“牛河先生?”嘶哑的声音问道。背景照例是寂静无声。
“我是牛河。”
“现在说话方便吗?”
没关系,牛河答道。
“‘证人会’的防范密不透风。不过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关于青豆的情报安然到手了。”
“追击导弹呢?”
“目前还不见踪影。”
“好极了。”
“牛河先生。”对方说,接着一连咳嗽几声,“不好意思,能不能请你把香烟灭了?”
“香烟?”牛河看看夹在指间的七星。烟朝着天花板冉冉升腾。“哦,我的确在抽烟。不过这可是隔着电话,你怎么会知道?”
“气味当然不可能传到我这边。不过,哪怕只是在听筒里听见吸烟的声音,我就会喘不过气来。我是极端过敏体质。”
“哦。怪我没有注意,抱歉抱歉。”
对方又干咳几下。“不不,这不能怪牛河先生你。注意不到也是自然的嘛。”
牛河在烟灰缸里揿灭香烟,还浇上了喝过两口的茶,并起身大大地打开窗户。
“我把香烟弄灭了,把窗户也打开了,换了房间里的空气。当然,外面的空气也说不上有多干净。”
“对不起。”
沉默持续了十多秒。那一端是彻底的寂静。
“那么,‘证人会’的情报弄到手了吗?”牛河问。
“嗯。只不过分量相当重。要知道青豆一家可是多年来的热心信徒,相关资料也多得不得了。有用没用,请你自己去区分吧。”
牛河同意了。不如说这样正中下怀。
“体育俱乐部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是开门进去,办完事情,再走出来关好门罢了。只是时间有限,只好全拿出来,所以分量也很多。总而言之,这两份资料全交给你。照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牛河写下蝙蝠说出的金额。比事先的估价高出两成多。然而他只能接受,别无选择。
“这一次我不想通过邮寄。我派人在明天这个时间直接去拜访你。请把现金准备好。还有,同以往一样,我不能出具收据。”
我明白,牛河说。
“再者,以前我告诉过你,为慎重起见再重复一遍。根据你的要求,能搜集到的情报我都弄到手了。因此,就算你对内容不满,我这边也不能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在技术上我已经竭尽所能。报酬是针对劳动的,而不是针对成果的。你不能说没有你想要的情报,还你的钱。这一点请谅解。”
我明白,牛河回答。
“还有,费尽力气也没弄到青豆的照片。”蝙蝠说,“所有的资料中都细心地把照片去掉了。”
“知道了。没关系。”牛河说。
“而且,脸说不定也变样了。”蝙蝠说。
“有可能。”牛河答。
蝙蝠假咳了几声。“再见。”他说着,挂断了电话。
牛河放回听筒,长叹一声,又叼起一根香烟,用打火机点着,冲着电话深深地吐出一团烟雾。
翌日午后,一位年轻女子拜访了牛河的事务所。也许还不到二十岁,穿一袭将曲线显露无遗的白色短裙,脚穿同样是白色的光面高跟鞋,戴着珍珠耳环。身材娇小,耳垂却很大。身高略略超过一米五,头发又直又长,长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上去有种见习精灵的感觉。她从正面直视着牛河,仿佛看见了难忘的珍宝,爽朗亲切地微笑,小巧的双唇间愉悦地露出整齐洁白的牙。当然,那也许是职业式的微笑。即便如此,初次见到牛河的尊容却不畏缩的人实在罕见。
“您要的资料,我带来了。”女子说着,从挎在肩头的布包中取出两只厚厚的大文件袋,然后像搬运古代石版画的女巫,双手端着放在牛河的桌上。
牛河从抽屉里取出备好的信封,递给女子。她拆开信封,拿出那叠万元纸币,站在那里数钱。手法娴熟,纤细美丽的手指疾速飞动。数完后将那叠钞票放回信封,再将信封放进布包,然后朝着牛河比刚才更夸张更亲切地微笑。仿佛在说,再没有比见到您更高兴的事了。
这位女子和蝙蝠到底是什么关系?牛河浮想联翩。然而,这种事情当然与牛河毫不相干。这位女子不过是个联络员。交付“资料”,收取报酬,大概就是赋予她的唯一的使命。
娇小的女子从房间里出去之后,牛河久久地凝望着房门,心潮难平。那是她从背后关上的门。房间里仍然浓烈地残留着她的气息。说不定作为交换,那位女子留下了气息,却将牛河的魂儿勾走了几分。他能觉出胸中新生出的那块空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牛河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概过了十分钟,牛河终于重新振作起来,打开文件袋。袋子用胶带封了好几层,里面又是打印件又是复印件,还有资料原件,乱七八糟地塞得严严实实。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短短几天居然搞来了这么多资料。虽然每次都如此,牛河还是不得不佩服。然而同时,面对着这成捆的资料,深深的无力感袭上心头。在这种东西里再怎么搜寻,最终还不是一无所获?我耗费巨资,难道不是弄来了一堆废纸?那是怎样窥视都深不见底的无力感。而好不容易映入眼帘的东西,却都裹在死亡预兆般的幽暗黄昏中。他想,说不定这也是因为那位女子留下的某种东西,或者是她带走的某种东西。
然而牛河总算恢复了气力,直到傍晚,一直耐着性子阅读那些资料,觉得有用的就分门别类,逐一抄写在笔记本上。集中意识进行这项工作,终于成功驱逐了那莫名其妙的无力感。当屋内变暗、桌上的台灯点亮时,牛河觉得支付巨额费用还是值得的。
首先从体育俱乐部的“资料”开始读起。青豆四年前到这家俱乐部就职,主要负责肌肉力量训练和武术课程。开办过好几个班,负责授课。阅读资料就能知道,作为教练的她能力极强,在学员中人气很高。除了主持普通班级,还受理个人指导课程。费用当然更贵一些,但对那些无法参加固定时间的课程的人,或者喜欢更私密的环境的人,这不失为便利的做法。有许多这样的“个人顾客”追随青豆。
青豆是在何时何处,又是如何给这些“个人顾客”授课的,可以根据复印的日程表追溯踪迹。青豆有时在俱乐部里为他们进行个别授课,有时则是上门授课。顾客中有著名的娱乐圈人士,也有政治家。柳宅的女主人绪方静惠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青豆与绪方静惠的关系始于来俱乐部工作后不久,一直持续到她消失踪迹之前,恰好是在柳宅的二层小楼正式用作“暴力受害女性咨询室”的庇护所的时期开始的。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不是。总之根据记录,两人的关系似乎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密切。
青豆与老夫人之间也许萌生了个人的羁绊。牛河凭直觉感到了这一点。原本以体育俱乐部的教练和顾客身份开始的关系,在某个时间点发生了质变。牛河的眼睛按日期追逐着平板的记述,努力想确定那个“时间点”。那时候发生了某件事,或者明确了某件事,以此为界,两人不再仅仅是教练与顾客,而是超越年龄与地位的差异,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此时,两人也许缔结了某种精神密约,于是顺理成章有了大仓饭店中刺杀领袖一事。牛河的嗅觉这么告诉他。
是怎样的顺理成章?又是怎样的密约?
牛河的推测无法抵达那里。
然而,其中恐怕涉及了“家庭暴力”的因素。看来这对老夫人来说似乎是重要的主题。根据记录,绪方静惠最初与青豆接触,是在青豆主持的“防身术”训练班里。年过七旬的女人参加防身术训练班,大概难说是寻常事。可能是某种与暴力性有关的因素,将老夫人与青豆联系起来了。
或许青豆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领袖则是家庭暴力的加害者。他们探知了此事,便对领袖加以制裁。但一切说到底只是“也许”这个层面的假设。而且这个假设和牛河知道的领袖形象相差太远。当然,不论是什么人,其内心都无从窥测,况且领袖原本就是个莫测高深的人。要知道那可是主宰一个宗教团体的人物。聪明睿智,却又有不为人知的一面。然而,即使他是个滥施家庭暴力的家伙,难道就真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值得他们制订周密的杀人计划、抛却自我抛却人生、不惜危及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要付诸实施吗?
总而言之,刺杀领袖绝非一时兴起、感情用事。其中存在坚定不移的意志、明确无误的动机和精细缜密的体系。这一体系是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和巨额金钱精心打造出来的。
然而证实这些推测的证据一个也没有。牛河手中有的不过是完全基于假设的间接证据罢了,是会被奥卡姆剃刀简单地削除干净的东西。现阶段还不能向“先驱”汇报。但牛河心里明白。其中有气味,有手感。所有要素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老夫人出于某种以家庭暴力为要因的理由,对青豆发出指示,置领袖于死地,然后协助她逃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蝙蝠搜集来的证据,全都间接地证实着他这种“假设”。
整理“证人会”的资料花了很长时间。分量多得吓人,而且几乎都对牛河毫无用处。用数字说明青豆一家对“证人会”的活动做出何等贡献的报告占了大半。阅读这些资料,便能知道青豆一家的确是热心忘我的信徒。他们将大半的人生都奉献给了“证人会”的传教事业。青豆的父母现住址为千叶县市川市,三十五年间搬过两次家,都在市川市内。父亲青豆隆行(五十八岁)在某工程公司供职,母亲青豆庆子(五十六岁)无业。长兄青豆敬一(三十四岁)毕业于市川市内的县立高中,后在东京都内某小印刷公司就职,三年后辞职,转去位于小田原市的“证人会”总部工作。在那里也从事印刷教团小册子的业务,如今已升任管理人员。五年前与同为信徒的女子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在小田原市内赁屋居住。
长女青豆雅美的履历在十一岁时终结。她在那时抛弃了信仰。而对抛弃信仰的人,“证人会”似乎便失去了一切兴趣。对他们而言,青豆雅美等于在十一岁时死了。从此以后她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连一行记述也没有。
这样看来,只有去找她的父母或哥哥当面打听,牛河想。没准能得到一点启发。然而单看资料,很难认为他们会痛快回答牛河的提问。青豆一家人——当然是在牛河看来——是一群抱着褊狭思想、过着褊狭生活的人,是一群坚信不疑地以为越褊狭越能靠近天国的人。对他们来说,抛弃了信仰的人,哪怕是至亲骨肉,也不过是步入了污秽歧途的人。不,只怕已不再认为那是至亲了。
青豆幼年时代遭受过家庭暴力吗?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即使遭受过,父母肯定也不会认为那是家庭暴力。牛河知道“证人会”管教孩子很严厉,许多时候还伴随着体罚。
即便如此,这种幼儿期的体验就会化作创伤深留心底,以致长大后竟然去杀人吗?这当然也不无可能,但牛河觉得似乎是相当极端的假设。有计划地杀死一个人非常复杂。伴随着危险,精神负担也极沉重。被捕的话,等待的将是重刑。肯定需要更为强烈的动机。
牛河再次拿起文件,仔细地阅读青豆雅美到十一岁为止的经历。她刚学会走路,就跟着母亲从事传教活动。挨家挨户地散发教团的小册子,向人们诉说世界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末日,呼吁他们参加集会。而加入教会就能逃过末日幸存下来,然后至福的王国即将降临。牛河也多次受过这样的劝诱。传教者大多是中年女子,手中拿着帽子或阳伞。许多人戴着眼镜,用聪明的鱼儿一般的眼睛盯着对方。很多时候都带着小孩。牛河想象着幼小的青豆跟在母亲身后走家串户的场景。
她没进过幼儿园,幼时就读于附近的市立小学,五年级时退出了“证人会”。弃教的理由不明。“证人会”不逐一记录弃教的理由。落入魔鬼掌心的人,就听任恶魔摆布吧。谈论乐园,谈论通往乐园的途径,就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善人自有善人的工作,魔鬼也自有魔鬼的事情。一种分工得以形成。
在牛河的脑袋中,有人在敲用胶合板拼的简陋隔板,呼唤着“牛河先生、牛河先生”。牛河闭上双眼,侧耳倾听那呼唤声。声音虽小却很执着。我好像看漏了什么东西,他想。有个重要的事实记载在这些文件的某个角落,可是我没看出来。敲击声就是在告诉我这个。
牛河再度查阅那堆厚厚的文件,不仅用眼睛追逐文字,还在脑海中具体地浮想各种场景。三岁的青豆跟随母亲四下传教,常常是在门口就被粗暴地赶走。她上小学,继续传教活动。周末的时间全用于传教。肯定连和小朋友玩耍的时间都没有。不,说不定根本没什么朋友。“证人会”的孩子在学校受欺负遭排斥的情况很普遍。牛河读过关于“证人会”的书,对这些有所了解。于是她在十一岁时弃教。这一定需要相当大的决心。青豆一出生就被灌输了信仰,与这信仰一道成长,它一直渗透到了身体的核心,不可能像换衣服般简单地抛弃。况且它还意味着在家庭内的孤立。这家人的信仰极其虔诚,他们绝不会畅快地接纳弃教的女儿。抛弃信仰就等于抛弃亲人。
十一岁时,青豆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她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千叶县市川市立某某小学,牛河想,并试着将那名字念出声来。在那里发生了某件事。在那里毫无疑问发生……这时,牛河轻轻地倒吸一口气。这个小学的名字,我在哪里听过。
到底是在哪里听到的?牛河与千叶县从无缘分。他生在埼玉县浦和市,考进大学来到东京后,除去在中央林间住过一段时间,始终住在二十三区内,几乎从未踏进过千叶县一步,只到富津去洗过一次海水浴。尽管如此,为什么会觉得市川的小学似曾相识?
花了很长时候,他才回忆起来。他用手掌使劲搓着奇形怪状的脑袋,集中意识。仿佛将手深深地插进泥淖中,摸索着记忆的底部。听到这个名字并非许久以前的事,就是最近。千叶县……市川市……小学。这时,他的手终于抓到了细细的绳头。
是川奈天吾,牛河想。对了,那个川奈天吾就是市川人。他好像也在市内的公立小学念过书。
牛河从事务所的文件柜中拿出关于川奈天吾的文件夹。那是几个月前受“先驱”之托搜集的资料。翻开一页,确认天吾的学历。他那圆滚滚的手指找到了校名。果然。青豆雅美和川奈天吾就读于同一所市立小学。从出生日期来看,两人大概还是同一年级。是否同一个班级,得调查后才能弄明白。但两人极有相识的可能。
牛河叼起一根七星,用打火机点燃。他感觉事物开始串联成线。点与点之间各自连起一条线段。它们最终将构成怎样的图形,牛河还不清楚。然而不久构图就会渐渐清晰。
青豆小姐,听得见我的脚步声吗?大概听不见吧,因为我走路时尽量不发出声音。然而我一步接着一步,正向你走近。虽然是蠢头蠢脑的乌龟,却在扎扎实实前行,终究会看见兔子的背影。你就等着吧。
牛河靠在椅背上,仰望天花板,对着那里缓缓地吐出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