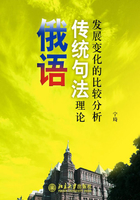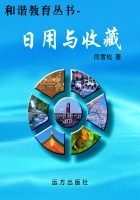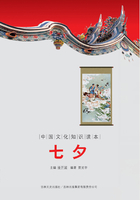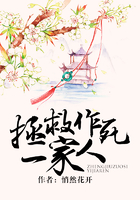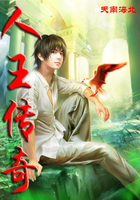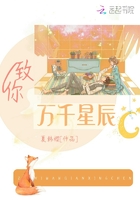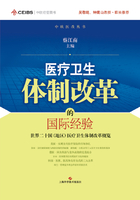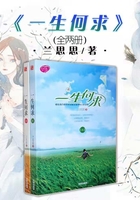论20世纪40年代的穆旦批评空间
易彬
引言
种种迹象表明1946年之前的穆旦缺乏反响。《中央日报?平明》(第225期,1940/5/29)、《柳州日报?布谷》(创刊号,1942/1/3)等处曾刊出穆旦同学赵瑞蕻、学弟杜运燮所作赠诗,《文聚》杂志曾两次(第2卷第2期,1945/1;第2卷3期,1945/6)刊出一份据说由穆旦本人撰写的诗集《探险队》的广告,这些文字表明了穆旦在当时的影响力,但均不能算作文学批评。穆旦1940年在《大公报》发表的评论,《他死在第二次》和《〈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未见相关回应文字,看来并未激起多大反响。而从常理推断,穆旦1935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夏毕业留校任教近两年;1943年从军回来后虽没有重新回到联大教席,但在昆明等地仍多有滞留,与联大教师之间应有较多交往,在相关老师的日记、书信乃至评论类文字里,也应有或多或少的记载,但并不多,闻一多书信有过一次提及,新诗选本《现代诗钞》选入穆旦4首诗歌;吴宓日记对于“查良铮”有较多记载,但诗人“穆旦”的一面没有任何呈现。
1946年之后,关于穆旦的批评文字出现较多,其中多热切颂扬之辞,也不乏严厉批判之语;有专论,也有某一种整体性视角的考察;其作者有年长的,如沈从文、朱光潜这类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文化人,穆旦作品的发表多得益于他们襄助;同辈人较多,有陈敬容、王佐良、周珏良、袁可嘉、唐湜、李瑛、吴小如等,是年轻的大学讲师或助教、新创的刊物编辑以及在校大学生,他们多是穆旦的同学与友人,也有些陌生人。至于批判者的身份,暂不得其详。年长者均是粗笔勾勒,同辈人所作多长篇大论。这表明穆旦诗歌激起了不同的反应。作为批评重要形式的选本也陆续出现,这也是穆旦反响得到加强的一个辅证。
由于学界对部分观点已多有引述,这里将更关注各人背景与观点的形成过程,他们所指涉的现象、问题及相关语境;部分时候,也将适当提及这些批评与穆旦本人的写作状况之间的关联。
一、新文学史序列:沈、朱的批评
沈从文、朱光潜二位用非常粗略的笔法将穆旦诗歌放置到新诗发展脉络当中。沈从文(1947年7月)曾将新诗发展分作五个阶段:“五四时代”;“新月时代”;1931年开始以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为代表的第三期;抗战后以高兰、王亚平、彭燕郊、艾青为代表的朗诵诗潮;最近,冯至、杜运燮、穆旦等人新印诗集,“若为古典现代有所综合,提出一种较复杂的要求”。另一次,沈从文(1947年10月)提出了辩解,有一二读者责备他“不懂诗”,在主编发稿的《益世报?文学周刊》50期中“专登载和编者一样宜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沈从文否认了这种责备,并为包括穆旦、郑敏、袁可嘉、李瑛等在内的一批年轻作者而觉得“光荣”。
朱光潜是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框架中提及穆旦的。同题文章(1948/1)较多谈及新文学发展的背景性因素,新文学“确是在朝一个崭新的方向走”;但新诗“对于西诗的不完全不正确的认识产生了一些畸形的发展”:早期新诗、新月派诗人“功夫都不够”;“卞之琳、穆旦诸人转了方向,学法国象征派和英美近代派,用心最苦而不免僻窄”,冯至、臧克家等人的写作也面临困境。其结论是“新诗似尚未踏上康庄大道,旧形式破坏了,新形式还未成立”。
能够进入两位在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前辈的批评视野,并被镶嵌到新文学史的序列之中,与一些重要诗人并称,表明在两位的视野中,穆旦诗歌具有超出一般写作者的价值。但非常微妙,尽管沈、朱二人被认为是有着共同旨趣的自由主义作家,在两种勾勒中,穆旦诗歌却呈现出近乎相反的诗学效果:既是“综合”的、“复杂”的,却又是“僻窄”的。这一局面的形成,可能与沈、朱二位评判新文学的基本价值准则有关。沈从文是新文学作家,对于新文学一直保持积极阐释的态度,对具体文本也常有细致分析,其结论往往即源于此。朱光潜更多理论家本色,其文艺批评多援例于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少有新文学方面的内容,这表明其价值准则多从古典与西方中来——放眼新诗评论文章,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例证和资料援引方面都有这种倾向,朱自清《新诗杂话》系列论文、阿垅的评论文字,多以古典诗歌为证,袁可嘉也苦于找不到“细致复杂的作品可充例证”。这多少表明新诗自身存在较大问题,虽有较为高远的理论视域,却缺乏可资例证的重要文本。不妨说,沈从文对于穆旦等年轻作者的肯定即是对于新文学现状的肯定,以年轻为“光荣”则透现了他对于新文学前途的乐观。朱光潜操持来自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带有普遍性的诗学标准,对于新文学的前景保持乐观;对于现状则多焦虑,目前新文学“距离理想还很远”,随着“西方影响的输入”,传统面临着“极严重”的问题。
沈、朱二人的分歧倒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一个自新文学发生就衍生而出的命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分歧被成倍地放大——穆旦也从一个简略例证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个案,这是后话,留待另叙。
二、“中国新诗人”:王、周的批评
同辈人士所作穆旦批评多有观点发明,其中出现最早、流传最广、引用频率最高、争议最大的是王佐良的《一个中国新诗人》。该文初刊伦敦Life and Letters杂志(1946/6);产生实质性影响应是附录于《穆旦诗集(1939-1945)》,特别是在《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刊出之后。从多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次富有开创性意义的批评。
王佐良是穆旦大学同学、联大外文系同事,对穆旦的成长背景了解甚多。他称当时联大的一群年轻写作者“毫不有名”,穆旦“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重要原因即“那些印在薄薄土纸上的小书”无法往远处传播。他所描述的穆旦1942年从军途中的生死经历确立了穆旦的基本形象:性格坚韧内敛,对于自身英雄传奇经历“觉得淡漠而又随便”。具体而言,文章既强调了穆旦作为一个写作者在抒情、文字、风格等方面的创造,也强调了他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与痛苦。这些观点奠定了穆旦研究的基本格局,也造设了穆旦研究的根本歧义——最主要的即是如何衡定穆旦写作的非中国化问题,即穆旦“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智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
争论焦点是“非中国化”到底是不是一种最好的品质。这自然值得好好辩诘,但首先需注意这一强调的话语逻辑及其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关联,王佐良多次将穆旦与“中国的智识分子”对举,以突出穆旦之“新”,这种带有夸饰色彩的文体,“五四”新文学以降使用非常广泛,现代读者非常熟悉,也即,王佐良这一夸饰文风乃是受自身隶属的一种急峻的历史意识所激发,在一种“中国式极为平衡的”、“缺乏大的精神上的起伏”的现实气候之中,在新诗尚未有效地确立自身传统的时刻,唯有“新”才能彰显他们这一代人独特的历史处境。
时间徙进,语境也发生潜移或蜕变: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佐良用“中国品质”取代了“非中国化”的判断,同一个“中国”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所谓“胜利”,既是因为对古典中国的无知,又是因为“中国品质”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王佐良关于“中国”的两个命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再者,今人基本上弃置了王佐良当年所施用的文体,却也激活了当年并未引起多大争议的命题——事实上,在争议话语出现之时,“非中国化”的观点一直统摄着穆旦研究,以致穆旦写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之间的关联被有意无意排除在外,同时却又将他置于新诗写作的高位,这无疑与学界对于“新”(“现代化”)的信仰有着莫大关联。
相比于王佐良,周珏良与穆旦的关系更为亲近:中学同学、姻亲——《读穆旦的诗》(1947年7月)发表时,穆旦与周珏良的妹妹周与良已确立恋爱关系。
《读穆旦的诗》开头部分简略提到艾略特、叶芝、邓、马威尔、奥登等人的影响,这一与王佐良相近的切入方式表明“外来影响”在两位非常熟悉穆旦成长背景的评论者那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也即,两者都是从辩解开始,周文的实际行文也采取了从写作者与知识分子两个向度深入穆旦诗歌的方式:先是强调穆旦诗歌中“情思的深度,敏感的广度、同表现的饱满的综合”;中段则转向“现代中国知识阶级”的精神问题,即“受苦”——“在精神上却情不自禁地踏进了现代文化的‘荒原’”;最终的结果是一种悲剧——“反复追求不过使悲剧更加庄严”(《甘地》)。
文章还标举穆旦诗中一种“特别可注意的”成就。《农民兵》文字“十分平易”、“老媪能解”,“然而句句清新,它深刻锐利的地方尤其使人感觉到搔到痒处的痛快”;《甘地》则是“用极近口语的文字写出了庄严的诗,在白话文已被提倡了二十多年的今日,而每有大制作还是觉得此种文字不够典雅非用文言不可的时候,这种成就是特别可注意的”。周珏良从20多年的白话文历史的角度强调了穆旦诗歌语言(口语)所具有的诗学力量。今人多以“欧化”来批评穆旦诗歌语言及其他现代文学作品,周珏良却不仅不认为它是个问题,相反,从“平易”与“庄严”相融汇的层面肯定了它之于白话文历史所具有的独特的诗学价值。可见,随着时间的徙进,问题本身也发生了潜移。
三、“新诗现代化”:袁、陈的批评
比穆旦略小的袁可嘉和唐湜在穆旦批评上倾力颇多。袁可嘉是联大外文系后期学生,20世纪40年代后期任北大西语系助教,其间在平、津、沪等地报刊发表较多新诗批评文字,其核心话语为新诗现代化。这一话语与前辈学者朱自清的新诗研究有所关联,但朱自清标举的“现代化”更偏向于题材,即“迫切地需要建国的歌手”,所谓“建国”主要指现代化的生活。袁可嘉则着眼于新诗的现代品质,他有着更强的文学史意识,穆旦成为了他非常倚重的阐释对象。
《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年3月)是较早的一篇,其核心观点后被广泛引述,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袁可嘉将“‘现代化’的新诗”作者称为“感性改革者”,其先例有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人。这一话语逻辑表明穆旦接洽了前辈诗人所开创的传统。与王佐良的夸饰观点相比,这种对于新诗品质的分析更为精细,对于新诗实际进程与成就的体认更为切实。
袁可嘉行文多为宏论,穆旦稍早发表的《时感》(1947年2月8日)是该文所举的唯一实例,《时感》表达的是“最现实不过”的内容,即“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沉痛心情,但作者并没有采取痛哭怒号的流行形式,发而为伤感的抒泄;他却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糅合为一个诚挚的控诉”。“这样的诗不仅使我们有情绪上的感染震动,更刺激思想活力;在文字节奏上的弹性与韧性(Toughness)更不用说是现代诗的一大特色。”
基本话语确立之后,袁可嘉又分四次阐释了新诗现代化的命题,《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是最后一篇,其时已是1948年10月。此文与“文学界的宗派倾轧”直接相关,民主是“全面的一种文化模式或内在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所要求的“辩证性、包容性、戏剧性、复杂性、创造性、有机性、现代性”,与那种仅仅将民主视为“狭隘的一种政治制度”的观点“构成尖锐的对照”。袁可嘉通过比较来彰显诗歌“如何从原始走向现代”,例证是徐志摩的抒情诗和穆旦的戏剧诗,这是“两个先后时代诗底本质底不同”:徐诗“是浪漫的好诗”,“明朗而不免单薄”;穆旦的诗“是现代化了的诗”,“晦涩而异常丰富”。价值如何区分呢?“不同时代的诗虽然都有相对的价值,但作为现代人,我们也自然不无理由对穆旦底诗表示一点偏爱。”不同时代的诗有“相对的价值”,“偏爱”是基于现代人的立场。这般标举现代性的视域与王佐良是相通的。
可特别指出的是,当年轻的袁可嘉以“宗派倾轧”来界定1948年的文坛现象时,他显然还没有来得及理会那其实是一场政治博弈,也就没有意识到它那异常强大的威慑力,这使得其论文保留着一股天真的热情。稍早,他作《诗的新方向》(1948年9月)也是为“近十余年来南北文坛的相互排斥的情形”感到惋惜。文章将《中国新诗》视为“新方向”,所登诗歌“极不相同的风格”证明了诗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青年诗人的合作是因为“有想在艺术和现实间求得平衡的一致心愿”,其创作是“艺术与人生,诗与现实间正确关系的肯定与坚持!”郑敏、穆旦、唐祈、杜运燮等为他所倚重,“穆旦的搏斗的雄姿,拼命地思索,拼命地感觉,而又不顾一切要诉之表现的镜头是北方读者所熟悉的,他的《世界》、《手》、《我想要走》仍保有一贯的dynamic的特质,我个人觉得他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动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才人之一”。“正确关系”的说法显示了袁可嘉的天真热情,“我个人觉得”、“可能”、“之一”等限定性词汇透现了他批评时的某种谨慎。“拼命”应和了周珏良的说法,“搏斗”关联起唐湜的观点(见后引),“艺术与人生”的说法则与陈敬容相通。
陈敬容也强调“诗的现代性”,即“强调对于现代诸般现象的深刻而实在的感受,无论是诉诸听觉的、视觉的,内在的或者外在生活的”;也对新诗传统提出了批评,即“尽唱的是‘梦呀、玫瑰呀、眼泪呀……’”与“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的“传统”;也强调“综合”的意义,现代诗所要求的是“一切的综合”。文章指出穆旦诗歌从“浪漫派”到“现代”诗的过程,穆旦“用深入——深入到剥皮见血的笔法,处理着他随处碰到的现实题材。无论写报贩,洗衣妇,战士,神或魔鬼,他都能掘出那灵魂深处的痛苦或欢欣”。不难看出,袁、陈二人既对新诗传统提出批评,又对新诗现代化命题大加阐释,其中显然包含了对于新诗实际境遇的强烈省思。
四、“搏求者穆旦”:唐湜的批评
与前述诸人的主动阐释不同,唐湜是1947年秋受与穆旦同出自西南联大的小说家汪曾祺推荐之后才写成批评的,带有不小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