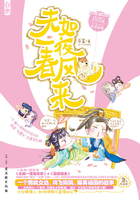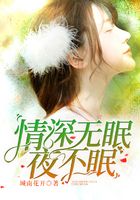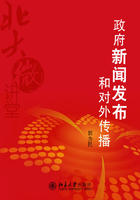吴元迈[1]
1994年9月20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在扬州举行,与会人员就如何反思过去、总结现在和开辟未来,更好地开展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进行了研讨。我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的发言,谈到了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和意见,即如何建立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加强外国文学评论工作,如何发展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以及冷战后世界文学的多元新格局等。发言还在其中一个地方提出,“为了适应外国文学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做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我以为我们外国文学界应该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2]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进一步探讨相关学术问题,以求教于前辈和同行。
进入21世纪后,当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国文学评审组,为了总结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收获与成就、经验与教训,为了更好持续前行,提出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评审,最后确定由北京大学的申丹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建华老师分别组队承担。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洋洋大观的12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就是陈建华老师及其志同道合者历经多年艰辛和持续努力奋斗的结果。在该书付梓之际,建华老师要我为之作序。我深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均无法担当此项重任,希望他另请高明,但建华老师坚持邀约。在这种情况下,盛情难却,我只能勉为其难。想了想,好在我自己前些年在这方面多少做过一点工作,即撰写《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部分,之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组织一个编辑小组完成了此项任务(该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2000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正因为有这点缘分,便写了如下的思考与感想,是为“序”。
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次转型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中,并从此进入多事的近代。与此时的西方相比,具有几千年光辉历史而且从未中断过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显然暂时落后了。一百多年之后,即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曾就此全面而深刻地讲道:“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又说,“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3]这无异于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艺要学习借鉴“前进了一步”的西方。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除少数时间以外,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文艺都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前行的,也不是平行地前进的;相反,它们总是在互相联系、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影响中,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地共同向前推进的。这几乎是世界文化文艺发展的一条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东方文化或东方文艺,也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西方文化或西方文艺。这是被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不仅于此,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化文艺发展的具体条件不同,它们的前进道路既不平衡也不平坦,既有高潮时期也有低潮阶段。在西方诸如中世纪的文化文艺,在中国诸如近代的文化文艺,均属于低潮时期,但是,前者在经历文艺复兴时代、后者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洗礼之后,两者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且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里程碑。因此从总体上看,中西文化和文学都是历史地开放的、历史地与时俱进的,这是人类文化及文学前进和发展的共同路径和方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转折,并且迎来了它的转型期。经过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期间的近代文学变革,过渡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之实质性变革,这种变革始终同民族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交织在一起,即同反帝反封建以及那个时代对于科学民主的基本诉求紧密相连。
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同借鉴和师法外国文学密不可分。“五四”时期文学的转型势在必行,它就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因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产生危机,它们的内部机制必须进行变革,以便与之相适应。那个放开眼光的“拿来主义”,便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五四”文化运动时期文学界的共识,按鲁迅的观点看,“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4]“五四”时期如此,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文学新时期,同样如此。
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和外国文学翻译休戚相关,尤其是在文学的大转型时期,更是如此。我们知道,20世纪曾多次掀起文学翻译高潮。其实,晚清时期的文学出版状况已有所变化,有人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1500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有全数的三分之二,仅林纾的译作就有100余种”。[5]鲁迅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译文》(1934—1936年),功不可没。《译文》翻译介绍了俄苏、法、英、德等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并推出了关于高尔基、罗曼·罗兰、普希金等的四期特刊。《译文》时代虽然渐行渐远,但我有幸在1981年同叶水夫同志一起,在浙江外国文学学会负责人宋兆霗的陪同下,在一处离西湖不远的寓所里访问了当年《译文》的参与者黄源,并聆听他关于《译文》创刊前前后后的故事。
“五四”时期,学者、评论家、作家和诗人以及翻译工作者往往一身多任,且学贯中外,诸如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郁达夫、林语堂等。在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老一辈的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等,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与他们相比,总体差距是明显存在的,值得我们今天思考。
应该说,“五四”时期的外来思想和外来文学样式的影响前所未有。举例来说,《新青年》杂志每期都有介绍欧洲文学思潮的文章,以及翻译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作家的作品。《小说月报》还推出了一系列“特号”,诸如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等。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各种文学观念、方法、样式,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后来有变化),以及同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相适应的种种文学观。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国文学领域的三大文艺思潮,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
中国新文学的批评模式除了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评外,还运用了现代人本主义、直觉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批评形态,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中国批评格局。同时可以看到,在西方三大思潮中,现实主义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当时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并非教条的、没有变化的,而是广阔的、开放的,师法了其他各种“主义”的有益成分;特别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既开放又密切联系中国之国情,是一种极具中国味道和特色的现实主义,从而使他成为中国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者。
在中国的“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演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和早期共产党人的提倡分不开的。当时的苏联(间接通过日本)的革命文学对中国革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沈雁冰兄弟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及《无产阶级艺术》,以及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均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仅团结了更多革命作家,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发生了重大作用,诸如组织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恰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之后又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在中国形成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因为种种复杂原因也产生了个别的“误读”,诸如把弗里契和波格丹诺夫的庸俗社会学著作视为马克思主义之作。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由于时代条件的关系,这在所难免。
新中国成立后17年及“文革”10年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伊始,“学习苏联”,“向苏联一边倒”成了中国各个领域的目标和使命。与此同时,学习苏联,以苏联的观点和方法,以苏联的经验和尺度为参照系,来审视世界各国文学及其作家作品,也成为中国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第一任务。毋庸置疑,中国在学习介绍苏联文学成就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是有成绩的。学习苏联,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的选择;因为那时的西方国家以及不少非西方国家,并未同中国建交,从而使我们在文化文艺上失去了与西方国家正式交流的机会。这是历史条件使然,今天我们不能不客观地看到这一点。
但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文学及其思潮持全面引进、全面接受的态度,不能以我为主,以民族的主体性为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哪些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普遍规律,是必须学习的;哪些是在苏联行之有效的艺术经验,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照搬的;哪些是苏联的问题和失误,属于简单化、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之类,是我们应该力求避免、引以为戒的。此外,苏联文学及其思潮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的一种动态文艺,必须进行全面、客观和长时期的考察,不能以一时的政治关系而不按艺术规律行事,便匆忙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可忘却,值得注意和重视。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具体地说从1980年代起的一段较长时间里,我们在文学领域重复了过去学习苏联的那些失败经验,对西方的种种理论模式,不求甚解,生搬硬套,反过来又唯西方文学样式和西方理论模式马首是瞻,不加分析地跟着走。当然,不是所有的文章和著作都如此。
其实,中苏文学的“蜜月期”并不太长,只有10年。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发生裂痕;1963年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开展大辩论,即所谓的“九评”。此后两国两党关系急转直下:双方火力全开,针锋相对,不断上纲上线。例如,苏联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发源地”。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的苏联文学被定性为“苏修文学”。苏联文学的翻译、介绍和出版,从此大规模地由公开转入内部,这就是后来人们提到的那些“内部发行”、“内部参考”的“黄皮书”(其封面是黄色的,由此得名),例如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解冻》、《生者和死者》等等译介的由来。那时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破烂货”的西方文学,具有同样的命运,例如西方作品中的《麦田的守望者》、《往上爬》等等,也被打入冷宫;英国作家和批评家T. S.艾略特被看成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被全盘否定;美国文学流派“垮掉的一代”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等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供内部参考批判之用的“黄皮书”,却为往后的外国文学研究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和有益的资料。
事情还不止于此。1966年5月,中共中央“5·16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它“要求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矛头所向十分明显,从此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进一步加强和升级。其实在这之前,1966年4月10日,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即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国,并且指出《纪要》对部队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纪要》尤其是对俄苏文学作出了令人惊讶的、无以复加的歪曲,并颠倒黑白地声称:中国1930年代的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斯坦尼斯拉弗斯基的思想”,对他们的“迷信”必须“破除”。又说,“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等等。《纪要》对俄苏文学的大力挞伐,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坛对待俄苏文学的纲领性指南,此后的大批判,基本上就是以此展开的。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一个人的遭遇》是“为社会帝国主义效力的黑标本”等等。《纪要》不仅如此讨伐俄苏文学中的精华,而且在它的推动下,整个外国文学界都被说成是“崇洋媚外”,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还炮制了《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文章,不但否定西方现代派文艺,而且否定我们以前曾经肯定的资产阶级进步文艺,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还胡说它们“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蒙蔽劳动人民”、“维护剥削制度”。总之,在“四人帮”看来,外国文学界贩卖的是“封、资、修”。这足见那时文艺领域的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是何等之猖狂!幸好,这一页很快翻了过去,但是它的教训却极其深刻,而且在今日全球文艺领域内,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并没有销声敛迹,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人们对它们不应等闲视之。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苏联文学及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复杂过程:从全面学习、全面接受到全面否定、全面批判。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写作者十分为难,实际上呈现出的多是一些应景性的或大批判的文章,真正有分量有见解的著述,可谓凤毛麟角,甚至有些苏联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还没有达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的领域,虽然研究成果同样不多,虽然也写了一些大批判的文章,但毕竟留下了一些好的与比较好的著述,如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1964年)、杨周翰等三人的《欧洲文学史》(上册,1964年)等,就具有开拓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
1978年后作为学科建设的外国文学研究
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外国文学介绍和研究同共和国的其他领域一样,迎来了百废俱兴、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春天。
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在北京召开外国文学工作座谈会,并于同年11月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来自全国各地外国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和出版界70多个单位的140余名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并通过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这是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举行的第一次盛会,也是一次学术的动员会和进军会,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社团组织,标志着中国外国文学工作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全新时期。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外国文学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的阶段,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克服了1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和影响、清算了林彪和“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重新把握了文学与政治的正确关系、坚持了文学研究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观点及方法多样化的主张,从而有效地突破了外国文学的一系列禁区,扩展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加强了同外国文学同行的交流与对话,使外国文学研究得以朝着全方位全领域的方向大踏步前行,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它们不仅包括流派和思潮的研究,也包括丰富的作家作品和多样化题材的研究、文学类型和文体史的研究、作家传记和评传的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欣欣向荣,不仅有为数不少的大部头的通史,也有各种各样的各国断代史的问世。比较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外国文学研究中那些向来薄弱的学科,诸如南美文学、北欧文学、意大利文学、非洲文学、西葡文学等等,均进入了成果的丰收季节。
对于学科发展,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这是外国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表现之一。一是梁坤主编的《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20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分别阐述了20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二是陈众议于2004年开始组织的大型系列丛书《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第1批2014年版)。二者的阐述重点不同,前者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后者以作家诗人为对象;两者不仅具有互补性,而且相得益彰,标志着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发展和开拓前进的新阶段,可喜可贺。
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次转型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学新时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和发展,是又一次人的觉醒和解放。正是改革开放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事件,使中国文学得以摆脱封闭和偏狭、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危机,走向复兴和发展。
文学新时期伊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转型像第一次文学转型一样,是从翻译介绍和引进外国文学的新状况起步的。文学“拿来主义”再次成了文学界的共同诉求。从外国拿来的,同“五四”时期相似,首先是三大思潮或流派,相同的如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同的是“五四”时期并未产生的后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五光十色的国外的新思潮和新理论。同时应该看到,20世纪的新理论新思潮并不限于20世纪之内,例如,在20世纪发生重要影响的诸如现象学和实证主义的思潮和理论等,在20世纪前就已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从恢复真实性、“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步的。毫无疑问,这是对“四人帮”反动文艺观的直接反驳。
恢复现实主义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20世纪的现实主义之形式和内容,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较,已无法同日而语。传统上老是把现实主义定义为“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其实,是不准确的,这只能导致削足适履,因为20世纪的生活和艺术都在飞快发展。即便是19世纪现实主义,虽然主要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但也存在不同的形态和类型,例如幻想的或象征的等等,果戈理的某些小说就是如此。卢卡奇在1930年代提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样板和模式,这一观点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20世纪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文艺的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甚至包括20世纪之前以为同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神话在内,都用了,例如20世纪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艾特玛托夫的现实主义小说等,都大量运用神话。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异化,也不是现实主义的毁灭,而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归根结底,这是20世纪生活的使然。可见,那种以细节真实和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定义20世纪的现实主义,已越来越不可能。即便对于卢卡奇,他的晚期著作也对1930年代的观点作了修正。本文作者在80年代曾多次介绍国外有关的新动态,并提出“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之新命题。
现在,究竟应该如何定义现实主义,的确是个难题,需要人们进行认真探讨。我以为,必须另辟蹊径,首先考虑作品关于人的观念、关于世界的观念,同时不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绝对化,这是现实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之处。很遗憾,在这里我没有时间加以专门讨论。
关于后现代及后现代主义。在今日世界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按哈贝马斯的看法,启蒙主义并没有成为过去,现代化仍然是未竟之业。后现代并没有到来。对于西方理论界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必匆忙作出结论,急于分清谁是谁非,而是应该客观地冷静地观察一段时间。
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其实正确地说,它是一种实验小说。我在多年前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序言”里,就表达了这个观点。从艺术角度看,20世纪文艺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荒诞、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许多有益成分,从而丰富和开拓了20世纪的艺术视野,促进了20世纪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世界文学及其理论思潮和流派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也影响了和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次转型期文学多样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这就是我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之百年历史变迁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2015年春于北京
注释
[1]吴元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吴元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3]参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4]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5]转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