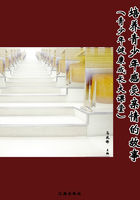“你少臭美了,潘安哪是你这样的?即便大哥有断袖之癖那找的也是你二哥这种的,哪能轮得到你?”弓子曜白了陆离一眼,他们都是在说顽话,自然也不会在意那样多。
“你们少拉我下水,我可没这癖好。”南浔更是喜欢玩笑,见陆离也放开了,便无所顾忌。
三人便这样哈哈大笑了起来,南浔瞬间领悟,其实自己大可不必这般怀疑陆离,陆离这样的身段,眼中又是这般清澈,有些情谊是可从眼神之中看出来的,陆离对弓子曜的尊敬与在意,是假装不出来的,更何况弓子曜平常是有些不着调,但也不傻,不至于被一个看起来年仅十六七的小孩骗了。
“二哥还未与月公主完婚吗?”兴致到了深处,陆离随口一问,却忘记其实知晓凤寒月与南浔成婚之人甚少。
而且先前陆离又问过弓子曜了,现在问,她自己也不知是为何。
闻言,南浔有些奇怪,若说陆离是乡下来的,又参军不多日,为何这些事知晓的这样清楚,虽是这般怀疑,南浔还是微笑着回答,“公主金枝玉叶的,我这自由惯了的,自然不会被驸马这个头衔而桎梏,也自知配她不上,便婉言拒绝了,倒是公主,也并不满意这门亲事,我与公主虽未曾见过,倒有这般默契,实数不易,今生看来无缘分,只等来生再续前缘了。”
听南浔说得头头是道的,错过了让身份再次高贵的机会,又能说得这般冠冕堂皇的,弓子曜才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摆摆手,不耐烦道:“你们这般文绉绉的我不喜,还是说些有趣的事吧,二弟你周游了四海这般时间,也该多与我二人讲讲奇闻趣事,要整些文的就赶快回你的巢穴,我可不爱听。”
在这形桑之中,再找不出能够让南浔称之为“家”的住处,弓子曜便将他所住之处称之为“巢穴”,也是在比喻南浔的四海为家,又如鸟那般无拘无束,其实世间少有人不羡慕南浔的,他既可不用心中有所担当为国效忠,又不用发愁未来将来面对的事情,贵在活在当下,既豁达,又洒脱。
“我还能遇到些何事,大哥你也是知道的,我呢,从不停留在一处很久的,除无聊之时去听听戏曲与评书,其余时间都是飘忽不定的,大哥又不爱听文绉绉的东西,那么那些个评书啊戏曲啊什么的,都是些无趣的了。”南浔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说辞,陆离听罢忍俊不禁,既有这般人物将自己的懒惰说得清新脱俗,也实属有趣了。
“你这张嘴啊,平日里我已然说陆离不过,遇到你本还想沾些便宜的,看来又是一场空,你们两个家伙,也不知让着大哥这个莽夫。”弓子曜虽每次话语强势,可无疑不是一种谦卑,总说自己没有文化,可说出的话,打的比喻,都比较有意思,陆离与南浔也不过是卖弄而已,比起弓子曜来,自然还是差了不少。
夜色似乎有些泛白了,南浔酒足饭饱,打了个哈欠,看了一眼陆离道:“你且劝劝大哥赶快就寝吧,看他愈发的精神,我这把老骨头可是经不起他折腾了。”
清早还有事情要做,若南浔不说,弓子曜差些就忘了,与他二人聊得实在忘我,才忘了时间,弓子曜一脸歉意道:“我这就去睡,你们俩也赶紧的吧。”说罢一溜烟儿跑了。
“二哥是要离军营而去吗?”看南浔的样子是不打算走了,可弓子曜跑得那样急,南浔是不可能与他同住了,看样子南浔是要与陆离同住,陆离也是担忧,这才问出口确认一下。
“这会子驿站还未曾有营业的地方,眼瞧着天气转凉,我也没法在外面睡,若是三弟不嫌弃,我就在你营帐之中对付对付,我睡地上也无妨。”南浔都这般说了,陆离实在不忍拒绝,她除了女儿身不能让南浔接近外,实在找不到拒绝南浔的理由,可唯一的理由又不能说出口。
“二哥哪儿的话,这样说便是见外了,二哥若是不嫌弃,便现住在三弟的营帐之中,若有什么不便,二哥担当着,三弟就先谢过了。”不得不说陆离这个乖巧与谦逊还是甚讨南浔喜欢的,其实南浔不喜欢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人,南浔不喜欢自己的这种桀骜与目中无人,而陆离恰恰一点都没有,所以南浔喜欢。
“瞧你说的,分明是我来借宿,你倒客气起来,你不必把我当外人,我可是你的二哥,有何难处尽管说便是,那么就叨扰了。”说着陆离起身带着南浔去了自己的营帐之中了。
还以为军营之中的营帐之内都是又脏又乱的,陆离的营帐却超乎南浔的想象,虽简陋,却是整洁,还泛着淡淡的香味,比一般的驿站都要好得多,甚是合南浔的心意,“可又毯子?铺在地上我将就将就。”
“哪有客睡在地上的道理?二哥尽管上榻上去睡,剩下的我来便可。”说着陆离前去寻毯子,准备自己睡在地上,南浔看了看,深深叹口气。
“真是不想恭维你这奴才样,都说了往后只把我当二哥便可,看你身上好像不大好,那么若是你嫌弃的话与我同榻可好?”南浔精通一些医术的,而陆离脸色泛白,自然是不好的颜色,他方才提起自己睡地上并不是客套,而是不想让陆离受罪。
自从在东离换皮之后,陆离的身子一直不大好,不过这点小事,她早已习惯,难得南浔看得出又真心的替陆离着想,现在她已经乏到眼睛都睁不开了,也懒得因为这等小事而与南浔推三阻四,连连点头,“那么就谢二哥体恤了。”
若是这时拒绝南浔,那么便是要承认自己有问题,反正床榻够大,若是没有肌肤之亲,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二人躺下,南浔其实毫无睡意,他平躺着问道:“你可知你这个名讳,与姑苏陆离相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