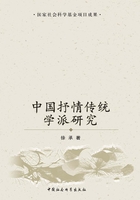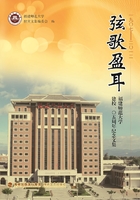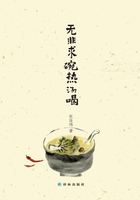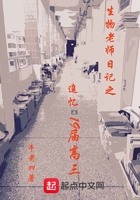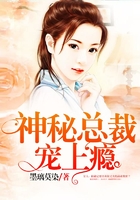南京有个文化圈儿。这圈儿,不是什么组织,也不是什么流派,只是一些兴味相投的文化人,以文会友,谈人说事,自娱自乐。文化,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机关发个号令要它繁荣就能繁荣的;也不是贴点钱,弄几个项目,就能成就千秋伟业的。文化需要滋养。滋养,需要环境。文化人之间无拘无束,尽兴交流,常常就是最有趣也最能催发创造力的环境。不信你关注一下,凡是几位趣味相投的文化人自发地凑在一起,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虽只有清茶一杯,却常常妙语迭出,奇思屡见。但若正襟危坐,领导致辞,依序发言,照本宣科,例行鼓掌,虽有车马费分发,还可共进午餐或晚餐,大抵,会散了,事也就过了,留不下一丝痕迹。尽管主办单位会说如何成功,有关报刊会说如何重要,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拆穿,为主办者保留一份面子罢了。
文化圈儿虽不是也不能靠指令成立,但也要有热心人从中联络。这热心人既要懂得文化,喜爱文化,又要有不惮烦劳、不辞辛苦的精神。董宁文君就是这样的热心人。他对文化有极浓厚的素养,又有极广泛的兴趣。他很懂得文化人的闲散和趣味,从不勉强什么人,从不指令什么人,大凡琐碎的事情,大都由他承担,只是努力为大家的交流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
他知道文化人的交流,能聚首交谈自是乐趣,但毕竟天各一方,聚少离多,更多的机会是得见其文,如见其人。所以他又联络同好,争取资助,办起了一个小小刊物,名曰《开卷》。这不是公开发行的刊物,也没有堂皇的封面、精美的印刷,只是一本三十二开三十来页黑白两色的小薄本子。封面《开卷》二字,是集鲁迅的字。装帧与版式虽不华丽,却极为精致,煞是可人。更为有趣的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都渐渐聚集到这本小小的非正式的刊物上来,足见人气颇旺。我想,这同编者能容的气度、广阔的交往大有关系。渐渐地,因着董宁文,就有了《开卷》,又因着《开卷》,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但又不间断的文化圈。书来信往,人来人往,便每期有了记载这些文人文事的《开卷闲话》,捉刀的子聪便是董宁文君。这些《闲话》,日积月累,编辑成书,至今已是第八编了。
文化人自有文化人的趣味。文化人当了官,不免官趣压倒了文趣,便同文化人有了隔膜。当官而无官气的文化人不是没有,只是稀有罢了。至于本无文化或文化无多的文化官,同文化人就更难沟通了。所以,当官的大抵很少知道文化人所思所想,而痴迷于文化的文化人,也大抵很少去理会官员们的指令。
董宁文君的“闲话”,所记皆是与文人、书人、编辑、教授的种种交往,或书信、或交谈,谈书、谈人、谈文事、谈书事,大多实录。看似琐碎,但却真实,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词语,叫做“原生态”吧。这就为研究当代文学、当代出版,留下了一份当代文人、书人真实心态、观感、趣味、追求的珍贵史料。时间愈久,其价值愈显。
开卷有益,“闲话”不闲。希望《开卷》长存,《闲话》长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