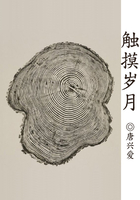前厅里,程舒志和展云隐隐僵持着,书房中,安歌闲来无事,便在程舒志堆积在书案上,那些杂乱的书册子里翻来翻去。
程舒志是个十分仔细却小心的人,他的书房中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安歌把他书案上的东西粗略瞧了一遍,没有一样是和政务有关的。
找了一会儿,安歌才找到程舒志翻译的《迷魂之法》。
老旧的羊皮卷上,记载的密密麻麻的字,被程舒志一字不差地用正楷写在空白的册子上,他一笔一划都写的极为仔细、端正,他的字像他这个人一样俊秀。
羊皮卷上记载的功法描述像极了安歌读书时,学的文言文,晦涩难懂,许是怕安歌琢磨不透,程舒志甚至在后面写了标注。
对迷魂术,程舒志一窍不通,他写标注的时候,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写,每句话都是经过再三琢磨推敲,直到他觉得意思确切、贴切了,才敢落笔。
安歌看了一遍羊皮卷上记载的迷魂术的详细,又看了一遍程舒志的标注,便觉得难懂的部分霎时间豁然开朗。
羊皮卷上的字不多也不少,不多不少的字,却把迷魂术的来历、修炼方法等记载的清清楚楚。
在这个大家信鬼神,鬼神也确实有的时代空间里,便有许多的奇人异士,亦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其中迷魂术便算是其中一样。
在羊皮卷的记载上,迷魂术是一种血脉相承的幻术,这种幻术最后出现于永康十三年。永康十三年后,修习之法虽然存留下来,亦有无数的人使劲浑身解数,想要勘破其中的奥秘,但没有一人成功。
“血脉相承。”安歌不停地重复这四个字,她可以断定,自己的迷魂术绝对不是血脉相承,她那位从未谋过面的母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而自己拥有这项能力,也是在原主的灵魂消失之后。
她甚是怀疑,自己之所以会拥有这项神奇而又看起来没什么乱用的能力,是死去的原主送给自己的“最后的好处”。
但究竟是也不是,原主已经离开了,安歌无从考证。
前文里已经说过,迷魂术是一种奇异的天赋,要修炼它,其实没什么特殊技巧,羊皮卷上记载的内容,关于迷魂术的描述便占去了一大半,修炼方法只有短短几句。
短短几句总结下来,便是磨练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力,自身意志越强,越容易控制人的心神。迷魂术作为一种天赋,来之容易,却有个弊端。
每次施展迷魂术,都需要耗费一定的精神力,之前安歌只是无意间成功两次,问的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故而没有什么感觉。
但倘若她要追究人心底的秘密,操控人的心智,使其短暂地成为自己的傀儡,那么便需要一定的精神力了。
精神力如果不够,每次施展后,安歌便会陷入一段时间的虚弱。
该如何修炼精神力,羊皮卷上也记载了两个简单且有效的方法,安歌捧着程舒志的译本,看得入神,不知不觉,半个时辰便过去了。
半个时辰的时间,如何修习精神力,安歌还是一头雾水,但简单地运用自己的这项“天赋”,安歌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上手了。
适时程舒志送走了展云,从前厅里回来。他的动静并不小,但因为安歌全心投入到迷魂术中,故而在程舒志走到她背后,盯了她半天,终于忍不住轻打了她一下后,安歌冷不丁被吓一跳,才回过神来。
回神之后,安歌拍着胸口舒口气,嗔道:“你走路怎么跟个猫似的,一点儿声都没有,吓死我了。”
“不是我走路没声,是你看得太入神了。”程舒志瞥她手里的译本一眼,问:“看得怎么样?”
“还好。”安歌合上译本,“叔、叔父走了?”
这句“叔父”,安歌喊的格外拗口,程舒志没在意,他拉了张椅子坐到安歌对面,点头道:
“我方才已经和叔父商量过了,平安镖局自此便关门了。镖局里的镖师们有许多好手,我打算挑一部分人留在京都里。”
安歌点头,赞许道:“眼下你中了状元,京都局势又不安宁,留下一些人在你身边保护也好。”
“不是保护我。”程舒志笑一声,捏捏安歌的脸蛋:“我身手好,寻常人不是我的对手,倒是你,搬出状元府后,身边没有几个人,所以我打算等到宅子修缮好之后,让大壮带着他们,跟你一起搬到新宅去。”
“跟我搬过去?”安歌连忙摆手拒绝道:“我一个女流之辈,谁没事想着去害我。我不要,你把他们留在状元府里保护你!”
“我府上自然也有人保护,这个你不必担心,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到时候我让他们过去。”
“不行!我不要!”
“乖~”
“不乖!”
“乖,你身边有人保护,我才能放心。”
“我不要!”安歌撅起嘴来。
“那你坚持不要的话,没什么办法,我只能把你留在我府上了。”
闻此言,安歌一瞪程舒志,她的软肋被程舒志捏的死死的,没办法,只好让一步,道:“那些镖师我可以留着,但是大壮我不要。我看得出来,大壮是你的心腹,你把他留下来!”
还未等程舒志说话,安歌赶紧强调道:“这还是我最后的妥协了!不然的话,我就趁你上早朝的时候,偷偷溜回我爹现在住的那个小宅子里去!”
程舒志拍了拍安歌的脑袋,宠溺地笑着应下了。
他的动作十分麻利,宅子看中了,展云一走,便立刻让忠叔揣着大把银票,不过一个时辰,地契和房契便送到了安歌手中。
看到房契和地契,安歌愣住片刻。
之前程舒志说的是,在京都给她赁一处宅子,她去看宅子的时候,满想的也是赁这处宅子不便宜,左右也就是一年光景,一年之后,她便嫁入状元府,程舒志要赁上一年,便赁上一年。
至多二三十两银子而已。
当房契地契送到她手中,她才发现自己错了。
安歌急忙拿着房契和地契冲到书房里去问程舒志,程舒志瞧见她一副炸毛公鸡的样子,愣了些许,便笑起来。
“哪有赁房子给你住的道理,我还未给过你聘礼,这处宅子,你便当是我给你的聘礼了。”
安歌心里虽然有些急,也有些气,但没有受了别人东西还要朝人发脾气的道理,她只能埋怨道:
“在京都,这样大的宅子,千两银子能够买下吗?饶是聘礼,也没有这样贵重的聘礼啊。你这样,我哪有嫁妆哪来还你。”
“你就是最好的嫁妆。”
程舒志认真地一句话,霎时间撩的安歌心里小鹿乱跳,嗔骂一句“花言巧语”,房地契收入怀中,算是收下了“聘礼”。
“明儿我便派人去把宅子给收拾出来,里面的家具咱们一应全部换成新的,近些日我不得空,你若是想亲自挑家具,便让大壮或者忠叔陪你去,看中什么只管要,不用在乎银子,这也是聘礼。”
程舒志笑眯眯地一番话,让安歌顿时有一种自己被包养的感觉。
但细想来,她可不是呗包养了吗,在这儿,无论是吃穿住行,都是程舒志管着,她要做的,就是瘫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这样颓废的米虫生活,安歌过得还算是安谧。
安歌不是矫情的人,宅子程舒志既然给她买下来,她便收着,她两袖清风,程舒志送什么,她也不拒绝。
她心里计较着,程舒志待她是由里向外的好,他的好,她无以为报,唯有不负程舒志的一颗真心。
除了修缮房屋,翻新家具外,宅子里的丫鬟下人也需要添置。
宅子买下之后,程舒志果然开始忙碌起来,从前他晌午时会从宫中赶到家中来,可眼下,往往日落西山,程舒志才会从宫里赶回来。
朝政上的事,安歌身为一个女子,不便多问,她也拿捏得准分寸,亦不去打听自己不该去打听的事。
状元府里,只有家务事。
因马上就要搬出状元府的缘故,安歌格外珍惜这几日的时光,程舒志下朝回家后,俩人一同用过早膳,安歌便会拉着程舒志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坐下,嗅着桂花香,笑嘻嘻地拣这一天的开心事向程舒志说上一说。
因自幼时,程舒志便孤僻的缘故,他为人冷淡,话也不多,唯有在面对安歌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笑,耐着性子听她喋喋不休着。
哪怕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夜色下,拉住他的手,头枕在他的肩头上,一坐就坐到她昏昏欲睡,程舒志也不厌烦。
比起朝野上的风波暗涌,勾心斗角外,程舒志显然更加喜欢在这个四四方方的,小小的院子里,和安歌单独相处的时光。
这样静谧安详的生活,对于程舒志来说,是短暂且美好的,也是他现在该珍惜的,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风浪会突然席卷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