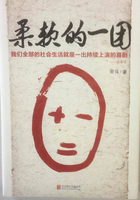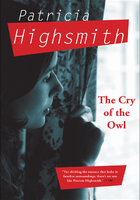北大的欧阳哲生教授要我写一篇有关我自己多年来治学经历的长文,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要求,我竟然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后来才发现,这一类文章十分难写,其难度与写自传不相上下。当然若从篇幅的长短来看,写一篇有关自己的治学经验的文章和写一部庞大的自传有很大的不同,但对我来说,其必须严肃地检视自己过去的过程却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我一向把求学的经验视为生命的主要内容。今日在回头检阅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时,我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感触,那就是,离开了“学”便无所谓人生的乐趣。
19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在他题为《一条没走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的诗中写道:“在黄叶林中我看见有两条分岔的路。”这首诗通常被解释成为人生的隐喻——在人生的旅途中,人们或许会偶然停下脚步问道:“如果当初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不知今日会是如何?”佛洛斯特自己说,他所选择的是那条偏僻而比较少人走过的路,而那个选择也就决定了他来日的人生方向。遗憾的是,一个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但我认为我一直只有一条路。而那条假想中的“没走过的路”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只要是没走过的,没经历过的,那就不算是一条路。
我的那条路就是读书求知的路,就是一条永远走不完的遥远的路。也许因为年幼就遭受到苦难的缘故,我从很小的年纪起就学会独自一人埋头于书中——在那个书本的世界里,我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记得我九岁那年住在林园乡下,每天下了课之后几乎都在阅读从大人那儿借来的世界名著中译本——我读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我也读赛万提斯[2]的《堂吉诃德》、薄伽丘的《十日谈》、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3]、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当时读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一书深受感动。全书以一个意大利学生的日记形式串联起来,尤其是《寻母三千里》那段故事特别感人。后来,我十二岁那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开始阅读《圣经》,那本书决定了我往后的人生观和对人性思考的兴趣。
以上只是关于我幼年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习惯的一个简介,还说不上是什么治学经验。真正的治学要到大学时代才开始。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向运气不错,初中保送高中,高中保送大学,所以从来不觉得有准备升学考试的压力,这样我暑假期间也就能随心所欲地阅读课外书了。我之所以选择进东海大学外文系,主要是想向美国教授学习如何阅读西方经典作品(当时东海大学外文系里的教师全是美国人,其中有些是传教士)。不知怎么,我自幼就特别喜欢英文,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篇长文竟然是用英文写的——记得当时上初一,我特别欣赏我的英文老师,她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她不但在课堂上鼓励大家说英语,而且下了课还单独教我写英语作文。而且,当时我上的中学正巧在一座修女院的对面,每天放学回家之前,我总是过街去找修女们用英语聊天。同时,在修女院我还学会了初级法文。这种种因素都使我后来决定上东海大学外文系。
1965年,二十一岁那年,我开始埋头努力撰写毕业论文。我选的题目是《美国19世纪的作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完全是一种巧合:一个好学的青年在开学的前夕送我一本麦尔维尔的小说Moby Dick(《白鲸》)。那本书的设计十分引人注目,蓝底封面配着白色的“Moby Dick”两个大字,封底还印着出版社极力推荐的一句话:“这是顶尖的世界名著。”(“The best of the world's best books.”)我读了书的开头一段,就立刻被它深刻的语言给抓住了,所以第二天就决定拿这本小说作为我毕业论文的题目。然而问题是,该书一向以其阅读的难度出名,尤其是整本书中大量使用了《圣经》的典故。我的指导教师Anne Cochran怕我无法应付,所以当初没有立即批准我的论文题目。几天之后,她决定给我一个有关《圣经》内容的考试,看我是否有资格研究这部充满了《圣经》典故的小说《白鲸》。没想到那个《圣经》测验第一次带领我入了研究的门。那天Anne Cochran教授阅完试卷,看我每题都答对了,高兴地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接着就开门见山地问道:“我看你真是做学问的材料,以后就走这条路吧……”她完全没想到,我从年幼就开始阅读《圣经》了。但她再一次向我强调,若想精通西方文学,首先非要熟读《圣经》不可,而且必须反复地读,因为那是所有西方人公认的一本最伟大的经典,也是最重要的典故出处。
果然,小说《白鲸》的一句话“Call me Ishmael”就把我拉回到了《圣经》的世界里。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以实马里[4](Ishmael)为希伯来人祖先亚伯拉罕和女奴夏甲所生,后来以实马里和母亲一起被亚伯拉罕的正妻撒拉所逐,被迫离开迦南,所以他后来就成为西方文化里典型的流浪者之象征。在某种程度上,麦尔维尔是借着他的小说《白鲸》来描写他身为一个流浪者的心灵自传。当书中的主人公开门见山地说,“就喊我作以实马里吧”,读者很自然地就会想起《圣经》里的那个令人难忘的流浪故事。唯一不同的是,《白鲸》里的以实马里是自我放逐而非被迫放逐——他说:“这陆地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乐趣,那么就让我出去航海,看看那片海洋的世界吧。”诚然,小说家麦尔维尔的一生正代表着苦闷的近代人那种选择自我放逐(下海)的悲剧。麦尔维尔于1819年生于纽约,自幼有一段坎坷的命运。他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之后被迫退学,到纽约一家银行里去做小工,十八岁以后开始当水手,到世界各处流浪,几年之内又多次上了捕鲸船,一直到二十五岁才回到故乡,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白鲸》主要写的是叙述者以实马里登上捕鲸船“斐奎特号”[5]之后,目睹船长亚哈不断追捕白鲸莫比·迪克的经历。我当初阅读这部小说,最喜欢该书的百科全书式的叙事章节。虽然整个故事看来颇为简单——说穿了就是一连串的巡捕、追逐、冒险加上最后全船沉没的大灾难——但每节内容之丰富、语言之生动及该书象征意义之感人,令我在阅读之中不得不全神贯注。这样,我就把大四那年仅有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全投入在论文写作上了。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广泛地阅读,我发现,大部分有关《白鲸》的二手资料都专注于船长亚哈如何疯狂地追捕白鲸莫比·迪克的问题上——那就是,讨论亚哈为何把一个捕鲸之旅转为个人的复仇之旅的心理因素和前后因果。然而我却把解读该小说的重点放在流浪者以实马里的个人救赎上——以实马里是书中唯一的生还者。在小说的末尾,以实马里眼看着亚哈和“斐奎特”号沉没在南太平洋里;在大船下沉的时候,以实马里差一点就被卷入了那个致命的轴心。但后来以实马里靠着海上漂来的一只棺材(即船上好友魁魁格的那只棺材)而得救。他趴在棺材上,在海上漂来漂去,整整过去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条船(即先前恳求亚哈放弃追逐白鲸莫比·迪克的“拉吉号”)偶然驶了过去,把漂流在海上的以实马里捞了起来。初读《白鲸》,我就觉得故事结尾的场景特别感人,特别富有联想的视觉效果。因此,三十多年以后,当我看到电影《铁达尼克》[6]的结尾时,我就不知不觉地想起了《白鲸》——虽然两部作品的故事题材并不相同。
回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新批评”盛行的年代,我的指导老师Anne Cochran特别教给我凡事细读(close-reading)的治学原则。她说:“你要养成细读的习惯,就会终身受用不尽。只有通过细读,你才可能在一本书中找出从前人没看出来的意义。细读是一种纯属个人的阅读经验,是你自己找寻思考人生意义的好机会。凡是通过细读而获得的灵感是属于你自己的财产,是别人偷不去的……”比方说,她很喜欢我用细读的方法读出了《白鲸》里的救赎之意。她说,她很高兴我能以《圣经》的典故为基础,加上自己的想象和分析,对麦尔维尔的作品产生了独到的见解。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用严谨的做学问的方法写出的第一篇论文。
20世纪60年代末我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我继续努力研究英美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我广泛涉猎了弥尔顿的《失乐园》、浪漫诗人布莱克的诗与画、王尔德的戏剧、哈代的诗与小说《苔丝姑娘》[7]、弗吉尼·伍尔夫[8]的《灯塔行》[9]等小说、叶芝和艾米莉·狄金森等诗人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美国写的硕士论文乃是有关19世纪英国散文大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英雄主义论,同时也对卡莱尔的名著《法国革命史》等书作了较为彻底的研究。我当时的指导教授Jerry Yardbrough的想法特别先进,他一方面要我注意德国作家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的重要性,一方面也鼓励我进一步把文学和文化现象结合起来研究。他说:“凡是长久以来的经典名著,必有其永恒而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你只管朝那个方向走,绝对没错。”他介绍我看著名学者Erich Auerbach的《模仿》一书,使我大开眼界。在那本书中,我学到了一个研究文学经典的秘诀:那就是,如何从文本的段落中看到整体文化意义的秘诀,是一种由小见大的阅读方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中,这种批评的方式一向被称为stylistics(文体研究)。据我看,Auerbach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文学经典中所用的语言——哪怕只有几句话——落实到了广义的文化层面上。Auerbach这种分析文本的方法后来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文学和文化批评。例如,著名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学者Stephen Greenblatt就在他的有关文艺复兴的许多著作中用类似的方法来阐明文学与文化的新意义,但不同的是,Auerbach以阅读文学经典为出发点,但新历史主义家们则较偏重对边缘文化的重新阐释。[10]
回忆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自己也很受Auerbach的研究方法的启发。我尝试用他的文体论的分析方法来广泛地阅读世界文学。奇妙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正当我较深入地学习西洋文学和文化时(当时我已在美国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心中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寻根欲望所笼罩着,久久无法平静。我很后悔自己从前只全身心努力研究西洋文学史,整个脑子只有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等人的影子,却完全忽略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中国古代的伟大作家。我突然恍然大悟:若不能深切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将来是无法严肃地从事比较文学的。所以,当时我一有机会就到普林斯顿的东方图书馆里去埋头苦读中国文学,几个月下来很粗略地涉猎了自《诗经》以来的不少经典著作。(多年之后我竟然当上了该东方图书馆的馆长之职,命运真不可思议,此为后话。)但我发现,中国的古籍浩瀚如海,愈往里头钻就愈感到自己的不足;愈不足就更有求知的欲望,也愈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肃然起敬。有些作品是从前在中学里就熟读过的,但现在重新阅读却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领会,这使我大为惊奇。例如,看到《诗经》里的诗歌和充满了儒家气息的《毛诗注》,就立刻会想到《圣经》里的《雅歌》,在脑海里对两种文化的不同产生了有趣的比较。但这种比较的角度是从前小时候所没有的。我发现,愈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所认识,就愈可能有举一反三的阅读乐趣。后来读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对他那种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态度,感到既佩服又向往。尤其是,钱著十分精彩,精辟的见解俯拾即是。记得我当时正在赶写一篇有关法国美学家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2)的报告,正在寻求新的灵感,突然读到钱锺书先生所写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讨论,一时感到欣喜若狂。钱先生把戈蒂埃的文体和唐代诗人李贺相比。他说:
戈蒂埃(Gautier)作诗文,好镂金刻玉。其谈艺篇(L' Art)亦谓诗如宝石精妙,坚不受刃(le bloc résistant)乃佳,故当时人有宝丹之讥(le matérialisme du style)……近人论赫贝尔(F. Hebbel)之歌词、爱伦坡(E. A. Poe)之文、波德莱尔(Baudelaire)之诗,各谓三子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窃以为求之吾国古作者,则长吉或其伦乎。如《李凭箜篌引》之“昆山玉碎凤凰叫”,“石破天惊逗秋雨”……[11]
这对我真是“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心灵经验。我把钱锺书先生看成是一种难得的文学现象,是把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的新现象。他对文学的热情和他对中西文化了如指掌的修养,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因而也看到自己从小所受西洋文学教育的盲点:我一味地追求那个文化上的“他者”,多年来简直把英文法文当成了母语(至少是写作上的母语),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对自己真正母语的逐渐遗忘。于是,我痛定思痛,毅然决定从头开始专攻中国文学,终于在1973年秋季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研究系的博士班。
在普林斯顿求学的期间,我主修中国古典文学,当时我的指导教授就是以研究唐诗著称的高友工教授。在研究汉学方面,我也深受 Andrew Plaks(蒲安迪)[12]和Frederick Mote(牟复礼)两位师长的启迪。另一方面,我也攻读比较文学,当时我在比较文学系的两位指导教授是 Ralph Freedman和Earl Miner(厄尔·迈纳)。前者以《抒情小说》(The Lyrical Novel)一书著称;后者以《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一书著名。[13]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有关文类(genre)的问题;我选的题目是《词的演进》,主旨在分析词体发展与词人风格的密切关系。我在论文中强调:一个伟大词人的个人风格经常会发展为后来的词体成规(即词之所以为一独特的genre之成规);反之,次等的词人则只能萧规曹随,跟着词体的成规随波逐流了。我到今天还很感激我的老师Earl Miner教授,因为他在我刚完成论文初稿之时(也就是尚未毕业拿博士学位时),就把它推荐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他的极力推荐和鼓励才催生了《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一书的早日出版与问世。[14]后来我转到耶鲁大学工作,有一次和我的同事布鲁姆(Harold Bloom)教授聊天,才发现我所谓的“伟大词人”与他的“强者诗人”有极相通之处。[15]不过,从本质上看来,拙作更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美文学研究所流行的“文类研究”的诠释方法;那种由小见大的阅读方法也间接地受了Auerbach等人的文体研究的影响。
我的第二本专著《六朝诗研究》(Six Dynasties Poetry)写的是有关诗中的“表现”(expression)和“描写”(description)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一种“文体研究”。我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文体作为检验个别诗人风格的参照点,主要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美国文学批评界中,“描写”正是许多批评家所探讨的重点。在逐渐走向后现代的趋势中,人们开始对视觉经验的诸多含义产生了新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也就直接促成了文学研究者对“描写”这一概念的兴趣。但从某一程度看来,这种对“描写”的热衷乃是人们对此前的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间太偏重情感“表现”的文化思潮的一种反动。然而,在我的《六朝诗研究》一书中,我是把“表现”和“描写”当成两个互补的概念来讨论的。这样,我一方面既能配合现代美国文化思潮的研究思潮,另一方面也能借着研究六朝诗的机会,把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介绍给西方读者。现代西方人所谓的“表现”,其实就是中国古代诗人常说的“抒情”,而“描写”即六朝人所谓的“状物”和“形似”。
这些年来,我开始关注文学里各种不同的“声音”(voices)。“声音”是非常难以捕捉的——有时近在眼前,有时远在天边;有时是作者本人真实的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解构主义告诉我们,作者本人想要发出的声音很难具体化,而且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十分错综复杂,不能一一解读,因而其意义是永远无法固定的。而且,语言是不确定的,所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mis-reading)。另外,巴特的符号学认为,作者已经“死亡”,读者的解读才能算数,在知识网络逐渐多元的世界里,读者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主体,因此作者的真正声音已经很难找到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Stanley Fish所主导的文学接受理论虽然主要在提高读者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却不断向经典大家招魂,使得作者又以较复杂的方式重新和读者见面。同时,新历史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努力寻找文学以外的“声音”,企图把边缘文化引入主流文化。此外,最近以来逐渐发展出来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研究,其实就是这种企图把边缘和主流、“不同”和“相同”逐渐会合一处的进一步努力。
自从1982年我到耶鲁大学任教以来,由于面临现代文学批评的前沿阵地(耶鲁大学一直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发源地),一方面我感到十分幸运,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警告——千万不要被新理论、新术语轰炸得昏头昏脑,乃至失去了自己的走向。我喜欢文学,喜欢听作者的声音,就让我继续寻找那个震撼心灵的声音吧。回忆这些年来,我基本上是跟着文学批评界的潮流走过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符号学理论、文学接受理论、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批评、阐释学等诸阶段。但不管自己对这些批评风尚多么投入,我都一直抱着“游”的心情来尝试它们的。因为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风潮也像服装的流行一样,一旦人们厌倦了一种形式,就自然会有更新的欲望和要求。然而,我并不轻视这些时过境迁的潮流,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文化。对于不断变化着的文学理论潮流,我只希望永远抱着能“入”也能“出”的态度——换言之,那就是一种自由的学习心态。记得多年前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自由就是自由地退出已进入的地方,以免它成为自己的陷阱。”我一直把这句话当成了座右铭。
于是,我就持这种自由自在的态度陆续编写了不少学术专著,希望能捕捉文学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在《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一书中,[16]我讨论情爱与中国的隐喻和实际关系,我曾借用Erich Auerbach的“譬喻”(figura)的概念来阐释明末诗人陈子龙的特殊美学。后来,与Ellen Widmer(魏爱莲)合编的《明清女作家》(Writing Women of Late Imperial China)[17]——共收录了美国十三位学者的作品——则侧重于妇女写作的诸种问题。与Haun Saussy 合编的一部庞大的选集《中国传统女性诗歌和评论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共收录了六十三位美国汉学家的翻译——则又注重中国古代妇女的各种角色与声音。我总是希望通过翻译与不断阐释文本的过程,让读者重新找到中国古代女性的声音。同时,我也盼望能借此走进世界性的女性作品“经典化”(canonization)行列,从而把中国女性文学从边缘的位置提升到主流的地位。
此外,在研究各种文学声音的过程中,我自己也逐渐发现了中国古典作家的许多意味深长的“面具”(mask)美学。这种面具观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作者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也同时促使读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阐释作者那隐藏在面具背后的声音。所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解读一个经典诗人总是意味着十分复杂的阅读过程——那就是,读者们不断为作者带上面具、揭开面具、甚至再蒙上面具的过程。
从捕鲸船上一路走来,我发现自己在经历过千山万水的颠沛经历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方向。诚然,做学问犹如捕鲸,那是一种显出生命的努力,也是不断从事自我教育的过程。《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就说过:“我的捕鲸船就是我的耶鲁与哈佛。”(“A whale ship is my Yale college and Harvard.”)
但与伟大的麦尔维尔相比,我只是一个渺小的读者,一个喜欢不断阅读经典作品的读者。
注释
[1]本文摘录自《文学经典的挑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一书的自序。
[2]中国内地译为“塞万提斯”。
[3]中国内地译为“基督山伯爵”。
[4]中国内地译为“以实玛利”。
[5]中国内地译为“裴廊德号”。
[6]中国内地译为《泰坦尼克号》。
[7]中国内地译为《德伯家的苔丝》。
[8]中国内地译为“弗吉尼亚·伍尔夫”。
[9]中国内地译为《到灯塔去》。
[10]参见Frank Kermode, “Art Among the Ruin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uly 5,2001), p.60
[11]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48页。
[12]中国内地译为“浦安迪”。
[13]参见Ralph Freedman, The Lyrical Novel: Studies in Hermann Hesse, Andre Gide, and Virginia Woolf(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后者中译本见《比较诗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王宇根、宋伟杰等译。
[14]此书中译版《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首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后来该书的简体修正版(题为《词与文类研究》)于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孙康宜补注,2014年12月)。
[15]参见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中译本见《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徐文博译。
[16]此书的中译本《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首先由台湾的允晨文化公司于1992年出版。其简体修订版(题为《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于201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孙康宜补注,2014年12月)。
[17]参见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