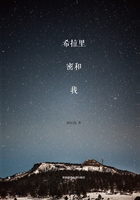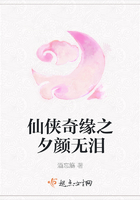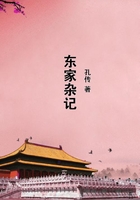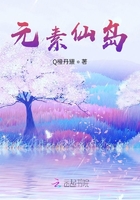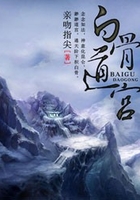客人一早就坐马车来了,各式各样的车子都有:有一匹马拉的小篷车、加长车身两条排座的双轮车、轻便的老式敞篷车、挂皮帘子的运货车。附近村子的年轻人在大马车旁站成排,用手扶住两边的栏杆,免得马跑车颠把人摔倒。有人从十古里以外的戈德镇、诺曼镇、卡尼镇赶来。两家的亲戚全邀请了,曾有过节的朋友都忘了旧事,多年不见的熟人也都收到了请帖。
篱笆外时不时传来鞭子的响声;接着,栅栏门打开了:来的是一辆小篷车。车子径直跑到台阶前,猛地停住,上面的人四散着下车后,有的揉膝盖,有的伸胳膊。女客戴着无边软帽,穿着城里款式的长袍,露出金表的链子,披着两边对叠的短披肩,下摆掖在腰带底下,或者披着花哨的小围巾,用别针在背后扣住,露出后颈窝。男孩子的穿着打扮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们的新衣服似乎有点碍手碍脚。这一天,许多孩子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穿新靴子。在他们旁边,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姑娘,穿着初领圣体时穿的白袍子,为了这趟做客又放长了一些,这八成不是他们的姊姊,就是他们的堂妹,红扑扑的脸蛋,神情呆呆的,头发上抹了一层厚厚的玫瑰油,一句话也不说,总怕弄脏了手套。马夫人手不够,来不及给马卸套,客人就挽起袖子,自己动手。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穿全套礼服,有的穿长外套,有的穿短外套,有的穿两用外套。全套礼服代表一家的敬意,不是参加隆重的仪式,不会从衣橱里拿出来;长外衣的宽下摆随风飘荡,有高高的竖领,衣袋大得像布包;短外套是粗呢料的,一般配上一顶加帽檐滚铜边的鸭舌帽;两用外套很短,背后有两个靠得很近的纽扣,活像两只眼睛,下摆似乎是木匠从一整块衣料上一斧子劈下来的。还有一些该坐末席的人,领子翻到肩头,背后有许多小褶裥,腰身低低地系着一条手缝的腰带。
衬衣的硬衬像护胸甲一样鼓在胸前。人人都理了发,露出了耳朵,胡子也剃得光光的;有几个人甚至天不亮就起了床,刮胡子也看不清楚,不是鼻子底下划了几道斜斜的口子,就是在下巴上剃掉三法郎金币那么大的一块皮,路上一冻红里发亮,让这些喜气洋洋的大胖脸上像加了一块玫瑰红的斑纹。
村公所离田庄只有半古里,大家步行前去,待教堂仪式一完,大家又步行回来。一行人起初挺整齐,看起来好像一条彩带,顺着绿油油的麦地中间的蜿蜒曲折的小路逶迤前行。不久行列就拉长了,三五成群地放慢了脚步,闲谈起来。乡村琴师走在前头边走边拉琴,他的小提琴上还扎了彩带;后面跟着的是新人,亲戚朋友们随意地结伴行走;走在最后的是孩子们,时不时地掐下燕麦秆子上的小花,要不就是躲着大人,自个儿玩耍。艾玛的袍子太长,下摆有点拖地,走不了一会儿,就得停下把袍子往上提一提,一边还要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拔掉野草的芒刺,而夏尔则只是在旁边等着,也不动手帮忙。卢奥老爹戴了一顶新的绸帽,黑礼服袖子上的花边直盖到指尖,他的亲家母挽着他的胳膊。而他的亲家公包法利先生,从心里瞧不起这些乡巴佬,来的时候只随便穿了件单排纽扣军装式样的礼服,一路上都在对一个金黄头发的乡下姑娘献殷勤,好像在小咖啡馆里一样。姑娘涨红了脸,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点着头。其他宾客各聊各的,或者在别人背后恶作剧,仿佛要先把气氛活跃起来;用心听的话,能听见琴师在田野里边走边嘎吱嘎吱地拉着提琴。琴师见大家都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便也就站住换口气,给琴弓擦上松香,好让琴弦的嘎吱声不那么刺耳,然后又继续往前走,琴的把手一上一下地晃动着给他打着拍子。琴声惊起了小鸟。
酒席摆在车棚底下。桌上有四大盘牛里脊,六大盘烩鸡块,还有炖小牛肉,三只羊腿,当中摆着一只烤得金黄透亮的烤乳猪,四边是香肠加酸模菜。桌子四角摆着装了烧酒的长颈大肚玻璃瓶。甜苹果酒则装在细颈瓶里,瓶塞四周浮起了厚厚的泡沫;所有杯子都早已斟满了酒,还有几大盘黄奶酪,只要桌子稍微一动就晃荡起来,平滑的表面上用细长的花体字写下了新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他们还从伊夫托请了一位糕点师傅来做夹心圆面包和杏仁饼。因为他在当地才初露头角,所以格外卖力。上餐后点心时,他亲自端出的一个塔式奶油大蛋糕让大家惊喜不已。蛋糕底层是用一块四方的蓝色硬纸板剪成的一座庙宇,有门廊、圆柱,神龛的四周撒满了烫金的星星,白色的小神像清晰可见;第二层是个堆成一座城堡模样的萨瓦式大蛋糕,周围用白芷、杏仁、葡萄干、橘瓣制成要塞;最上面一层是一片绿茵地,有果酱做的山石和湖泊,有榛子壳做的小船,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爱神在打秋千,巧克力做的秋千柱子顶上有两朵真的玫瑰花蕾,那便是蛋糕顶部的饰物了。
大家一直吃到天黑。坐得太累了,就到院子里去溜达溜达,或者去仓库玩一局打瓶塞的游戏,看谁能把瓶塞上的钱打下来,然后又重新入座。快散席的时候,有些人已经睡着,打起了鼾。但是一喝咖啡,大家又来了兴致,有唱歌的,举重的,攀拇指的,扛大车的,说粗话的,甚至有的搂着女客亲起来。马吃燕麦吃得从喉咙里满到鼻子眼里,连套车都成了难事,尥蹶子,使性子,皮带都挣断了;主人们有的大骂,有的大笑;彻夜都有载满归客的车子疾驶在月光下的乡间大路上,颠簸着越过水沟,蹦跳着翻过鹅卵石堆,摇晃着爬上斜坡,女客们把身子探出车门拼命地抓住缰绳。留在贝尔托过夜的则通宵在厨房里喝酒。孩子们早在长凳上睡着了。
新娘事先恳求过父亲免掉闹新房的俗套。但是表亲中有个做水产批发生意的(他特别带了一对比目鱼作新婚的贺礼),准备用嘴把水从钥匙孔里喷进新房去。幸好卢奥老爹走过,把他拦住,对他解释说,女婿是有地位的人,这样闹房未免举止失当。这位表亲只得悻悻住手。但在心里,他怪卢奥老爹摆臭架子,就向角落的另外四五个客人发牢骚,这几个人碰巧在酒席桌上一连吃了几块劣质肉,也都觉得主人刻薄,于是都叽叽咕咕地咒这一家子没有好下场。
包法利老太太一整天都没有开过口。媳妇的打扮,酒席的安排,全都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她早早就离了席。可她的丈夫非但不跟她走,反而要人去圣维克托买雪茄烟来,一直抽到天亮,一边还喝着掺樱桃酒的烈酒——乡下人还没有把这两种酒掺在一起喝过,因此对他格外佩服。
夏尔生来不善谈笑,因此在酒席上表现并不出色。从上汤起,客人少不得对他说些俏皮打趣的话,有的是双关语,有的是恭维话,还有粗俗的下流话,说得他无力还嘴。第二天,说来也奇怪,他却判若两人。人家简直会以为他是昨天的新娘,而真正的新娘却若无其事,令人看不透。那些捣蛋鬼也觉得她莫测高深,见到她走过他们身边时,只好一言不语地看着。可是夏尔却掩饰不住他的高兴。他亲亲热热地叫她“太太”,碰到人就问有没有看到她,到各处去找她,还时常把她拉到院子里去,老远就可以看见他们在树木中间并肩走着,他搂住她的腰,脑袋几乎俯在她身子上,把她的胸衣都蹭皱了。
婚礼过后两天,新夫妇要离开了,夏尔要看病人,不能耽搁太久。卢奥老爹套上他的小篷车,亲自把他们送到瓦松镇。他最后一次吻了女儿,便下车返程。大约走了百来步,他又站住回头看,只见小篷车越走越远,扬起一片尘土,他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他随即想起了他自己的婚礼和往昔,想起他妻子第一次怀孕,他从岳父家把她接回去,那一天,他自己也曾是那么快活。因为那是圣诞节前后,田野白茫茫一片,他们一前一后骑在马上,在雪地里跑着,她一只胳膊抱着他,另外一只挎着篮子;她的帽子是本地传统款式,长长的花边帽带随风舞动,有时拂到他嘴上;他一回头,看见她金黄色的帽沿下那红扑扑的小脸蛋挂着静静的微笑,紧紧依偎着他的肩膀,她时不时把冻僵的手指伸进他怀里取暖。这一切都是陈年往事了!他们的儿子要活到今天,也该三十岁了。他不由得回头看看,路上什么也没有。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所人去楼空的旧宅一般,酒醉饭饱后发晕的脑子里温情的回忆和凄凉的思绪交织在一起,他一时真想转到教堂那里去看看妻子的墓地。不过他怕去了会更伤心,还是直接回家了。
大约有六点钟,夏尔夫妇回到了托特。左邻右舍都从窗口探出来看他们这位大夫的新夫人。
老女佣出来见过了新的女主人,抱歉地说晚餐还没有准备好,请夫人稍候片刻,先熟悉熟悉她的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