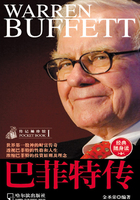虽说杜月笙已有“教父”之称,在上海滩上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是至高无上,但有一件事却让他一直气不顺,那便是他的大老婆沈素娥。
且说杜月笙与沈素娥结婚后,整日忙里忙外,新鲜劲很快过去了。沈氏一个人独守空房,难免生出些寂寞。她是苏州人,小时候是在表哥家度过的,因而,她常常想起那竹林、茅舍和月光下的小河及河上弯弯的小桥。表哥时常拿着一只洞萧在河边吹奏,少年的沈素娥时常静静地双手托腮听着那动听的乐曲。而杜月笙呢,偏偏在忙碌中又看上了别的女人,这女人叫陈帼英,是个舞女。
杜月笙平日喜欢嫖赌,对抱着女人的细腰嘭嚓嚓地跳华尔兹,他并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抱着女人上床,所以不大高兴去跳舞。
有一次,张啸林硬拉他到丽都舞厅去跳舞,正好碰上走红的陈帼英。
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的美称。每当夜幕降临,舞厅的霓虹灯此亮彼暗地闪烁起来,人口处极其性感的红舞星巨幅照片特别醒目。衣饰华美的众多舞客,兴致勃勃地步入舞厅。随着优美的舞曲奏响,舞客和舞女成双成对步入舞池。
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方的交谊舞厅开始传入,但当时只是洋人的自身娱乐活动。上海最早出现交谊舞是在外白渡桥的礼查饭店,稍后又有与国际饭店相邻的卡尔登戏院。每逢周末和星期天晚上,这两个饭店就举办不对外售票的“交际茶舞”,这是上海公开开设交谊舞场所的开始。从此,交谊舞在上海盛行起来。
上海最早开业的营业性舞厅是“黑猫舞厅”“月宫舞厅”等。到了三十年代,舞厅蜂拥而起,独领上海滩风骚。头等舞厅有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南京西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米高梅,等等。这些舞厅装潢华丽,设备高档,舞女年轻貌美,技艺娴熟。延安东路的新大华,黄陂路的维纳斯,南京西路的大沪,位列二等。大世界和永安等游乐场附设的舞厅,各居下等。还有些像大华饭店、华懋饭店和卡尔登的舞厅,则是西洋风味的外国舞厅,其规模设施,豪华奢侈,只有显赫的社会名流才能光顾得起。此外,一些小型舞厅也应运而生,如“夜总会舞厅”、“惠令登舞厅”、“逍遥舞厅”等等。这些小舞厅收费低廉、舞女伴舞五至八次才收费一元,光顾者都是商贩、中小工厂的老板及职员等。
舞厅是靠舞女唱“主角”的,所谓舞女,是以伴舞为职业的女性,人称为“龙头”,舞客则被称为“拖车”。舞客邀舞女伴舞,行话称“拖车配龙头”。按规定,舞女必须领取从业执照,方能在各家舞厅中伴舞。上海领有执照的舞女最多时达一千多人。舞女的来源有小职员、公务员、逃妾和侍女等等,他们多为生活所迫而沦为舞女。有一个叫李菁的少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看着老母亲和嗷嗷待哺的一双儿女,她忧心如焚,整日以泪洗面。最后,她画了眉毛,涂了口红,到维也纳舞厅当了舞女。美国水兵都喜欢让她陪着到处兜风,三天两头开吉普车来接她。人们称她为“吉普女郎”。由于过分劳累,她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卧床不起,终于命归西天。
舞女中也有些竟是十几岁的中学生。父母虽然贫困,却省吃俭用,积攒点钱送她们上学堂,她们为了减轻父母负担,白天到学校读书,晚上则借口有事出去,实际上是偷偷地到舞厅伴舞。有一个中学生姚梅碰到的顾客竟是隔壁邻居;第二大晚上,父母问她上哪儿去。她起初支支吾吾,看父母问得紧了,不由得放声大哭,父母也陪着落泪。
舞女的收入一般以舞票为主,每次以舞票多少与舞厅老板拆账。最走红的舞女可得约十分之七,次一等的约十分之六,末等的不到十分之五。舞女并不能全部拿到拆账后的钞票,还要遭受“舞女大班”的“提成”。舞女大班是一种“抬脚大班”,实际上是地方上的恶霸流氓。另一种大班是介绍舞女陪客、伴舞的“望台子”的舞女大班,实在像工厂里的女包工头。他们负责向舞厅推荐舞女和介绍生意。“舞女大班”每天要拿去舞女收入的十分之一二。经过舞厅老板和舞女大班的“提成”,舞女能拿到手的钞票只有一点点了。还有的舞女居然“吃汤团”,也就是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舞女都希望舞客的施舍。舞厅则规定,舞客每去买一瓶十几元昂贵的香摈,舞女可得一元二角。一曲终了,舞客喜欢请舞女一起喝香槟。如果舞客不买的话,舞女常常要明指暗示,这时舞客往往很有派头地掏钱买香摈。有时,乐曲声中,舞客将一条藏有钞票的花手绢悄悄塞到舞女手中,舞女则报以甜甜的一笑,伴舞更尽心尽力了。舞客送钱给舞女,不能让侍役转递,又不能到舞厅外送,于是就采用这个办法。
少数红舞女,像大华舞厅的陈雪莉、爵禄舞厅的李丽娜,凭着过人的色艺,倒也收入颇丰。但她们只是上流社会的玩物。大多数舞女,步入舞厅犹如跌进火炕,人前强颜欢笑,人后以泪洗面,还有的舞女沦落为娼。
所以,很多舞女都是趁着年轻貌美走红时,嫁一富庶的男人,以便终身有靠。
陈帼英就是这样做的,她先是一个中学生,初二那年15岁,因家里太穷,便在晚上悄悄地出去扮舞。扮到18岁,扮成一个亭亭玉立、丰乳细腰肥臀的大姑娘,舞客们人见人爱,很多人都想把手往她那肥嫩的屁股上搭。但陈帼英都婉言相劝,请舞客尊重些。
当杜月笙来到丽都舞厅时,老板请过陈帼英,杜月笙立刻被她的美艳与气质给震住了,半天说不出话。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先生。”
陈帼英在上海滩,当然知道杜月笙的大名,立刻高度投入地跳了起来。对跳舞无大兴趣的杜月笙,竟如魂牵梦绕一般,随着那动听的乐曲,飘飘欲仙。临走时,杜月笙就有些依依不舍了。后来,因忙于贩鸦片开赌场,没有时间再相会,但有时想起,心里总是油然而生出一种向往和怀念之情。
此段因缘,不知怎么被谢葆生知道了。
谢葆生原是沈杏山的手下,被杜月笙拉过来后,依然在沈那里卧了几年底。后来,沈杏山被杜月笙彻底打败,他才正式打了杜月笙徒弟的旗号,兴高采烈地倒戈过来。只是因为这小子爱财如命,马屁拍得山响,杜月笙心里并不喜欢他。
谢葆生过来后,就用昔日积攒的钱,开办了仙乐斯舞厅。开舞厅须对付三教九流的人,必须得有个靠山、背景,以镇住捣乱寻隙生事的人。杜月笙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由于杜心里讨厌谢,所以接到发来请求剪彩的大红喜帖,就来了个婉言谢绝。
谢葆生当然也不是寻常之徒,等闲之辈,他擅长揣摩人意,对症下药。他懂得怎样才能请得动对他有戒心的师父,在这紧急关头,无可奈何之时,他甩出了一张“黑桃皇后”,舞厅开张的那天下午,他找到杜月笙,说:
“师父,您即使不看在小徒的面子上,也得看在陈小姐的情分上,去走一道吧!”
“这关陈小姐屁事?”
“师父有所不知,仙乐斯舞厅特地聘请陈小姐挂头牌伴舞。陈小姐起初不肯,后来听说我是您的徒弟,今晚师父光临剪彩,她才点点头同意。如今她已在舞厅的幽会室里翘首以待哩!”
“你也真会找由头,把她骗来干什么呢?”
“师父,您去剪个彩,同她见个面,那我不就不是骗了吗?”
“咳,真拿你没有办法。”杜月笙摇头。他又想起陈小姐的细腰和那对在眼前晃动着的丰满的乳房。整日穷忙,这块肥肉为什么不吃一吃呢?想到这,他钻进了自己的汽车,吩咐司机说:“随着谢先生,去仙乐斯舞厅。”
汽车沿外滩向北行驶,过了海关大楼,向西一拐,进了南京路。两边高耸人云的摩天大楼把千百辆汽车夹在当中。在车水马龙中游戈了一段时间,车子在“仙乐斯”门前霓虹灯下“嘎吱”一声刹住了。几个制服笔挺的仆役上来开车门迎接。
进大门后,一大堆来宾见杜月笙到场,便噼噼啪啪地来了一阵热烈掌声。
掌声中走出陈小姐来。她穿了件无袖印度绸旗袍,奶白色底子上缀着一朵朵嫩黄的小菊花,滚边是嵌金线黑丝绒。她脚上穿着一双蛋黄色高跟皮鞋,长筒丝袜套到大腿弯儿上,高叉旗袍正好露出整条丰腴的大腿。蓬松的卷发披散下来。一对丰满的乳房高耸着,摆动着雪白的手臂,扭着细腰肢走来,吊着杜月笙的膀子发嗲:
“喔唷,杜老板架子真大,要我们谢老板三请诸葛,才出山呢!”
“让陈小姐、让各位久等,实在对不起!因为有些小事情绊住,迟来一步,请大家原谅!”杜月笙向大家拱拱手,然后文质彬彬地拉起陈帼英的手,厚嘴唇贴上去亲一下,陈嫣然一笑,依傍着杜走下舞厅内。
舞池四周的小圆桌子上,摆着鲜花与汽水、果子露、香槟等各种饮料,供客人们随便取用。乐池里着白西装黑领带的乐队成员,个个抱着乐器专等指挥的小棍一动。溜光滴滑的舞池,像面镜子,可以照得出人影。四壁柔和的灯光,混着微香,洒向人群。两对十五六岁的童男童女,拉着一幅大红绸子,横过舞池,在红绸子当中打了两只斗大的彩球。当杜月笙一踏进舞厅,乐队奏起迎宾曲,陈小姐挽着杜月笙的膀子,走向舞池中央。一个女孩端着一只红漆盘子随在后边,盘内有把镀克罗米的大剪刀。杜月笙站了片刻,让来宾们都进厅了,他才拿起剪刀,在人们噼噼啪啪的掌声中,剪了彩。
这时,四壁灯光慢慢转暗,镶在地角旮旯的脚灯放出淡淡的微光。几盏宇宙灯开始旋转了。乐队奏起一支中四步的舞曲,来宾们翩翩起舞,杜月笙斯斯文文地向陈帼英一鞠躬,随后抱着她的细腰,双脚踩着节拍移来移去,沉醉在嘭嚓声中。慢慢地陈帼英的身子越来越紧贴着杜月笙,她的脸蛋先在他肩上轻轻地摩擦,而后移过来依偎在他的腮旁,她微微惦起脚尖仰起头亲着他的脸,喃喃地动着嘴唇,可又听不清她说什么。
杜月笙漾起一片热潮,把陈帼英搂紧了,在原地扭动着。此时此刻,他才生出一种感触:舞厅,是一杯美酒,香醇而甜蜜。大丈夫在世,这醇美至醉的酒,是不可不饮的。她知道,杜老板这会儿被征服了,可以进一步提出自己想好的要求,可惜,乐曲终了,人们纷纷归座。
开张剪彩仪式到此算是结束,一些熟人都过来向这位大亨打招呼请安问好致敬。在嗡嗡扬扬的寒暄声中,乐声又起,那是支快速旋转的华尔兹曲子。嘭嚓嚓的节拍惹得人脚底痒兮兮的,杜月笙却觉得头晕,不想再加入这疯狂的旋转的队伍。他向一直陪在身边的陈帼英说:
“陈小姐,我得走了,下次再和你跳!”
“那到后头小间休息一下吧!”陈帼英说。
“师父怎么要走了?这可不行。”一直躲在一边,让陈小姐出面笼络着自己师父的谢葆生,不知从哪儿跳出来,“还有几桌酒席,要请先生赏光,要不,现在就开宴。”
“不用了,我还有点事情,你去忙吧,不用送我了。”
“那请陈小姐你送一下吧!”谢葆生向陈帼英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
陈帼英会意,挽起杜月笙的胳膊,依傍着下楼。一出门,杜月笙的汽车就开过来。陈帼英嘟起红红的小嘴嘟哝着说:
“杜先生,你真无情无义。”
“怎么讲?”
“我等了一个下半天,想等你来陪我喝杯酒,可现在又丢下我要走了!”陈帼英说着扬起手,向什么地方打了个响指。
另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陈帼英拉着他走了过去,到车子边,她拉开车门,先是自己钻进去,趁着杜月笙与她俯身吻别的当儿,勾住杜月笙的脖子,将他拽进车里,吩咐司机:
“汇中饭店。”
杜月笙本来也没什么大事急着要走,只是给谢葆生这小子一点教训,同时也为了给自己的身价加点码子,搭一下架子。现在既然有美人主动送上来,当然也就来个顺水推舟。杜月笙这一夜便在谢葆生为陈帼英包的汇中饭店一个房间里度过。
那陈帼英虽是舞女出身,但只是陪舞,从不陪身子,一些急得口水直淌的男人想找她便宜时,也只能隔着那紧身的衣服从外面摸摸捏捏。所以,陈帼英的身子如同是一嘟噜十分成熟的葡萄,肥、嫩、甜、香,色泽诱人,挂在枝头上,摇曳不己,只要轻轻一碰,就会从枝头跌落,甜美的汁水会随之四处飞溅。
当杜月笙和陈帼英一起来到包房时,久经风月场的杜月笙依旧像开始一样,坐在沙发上,不紧不慢地吸着纸烟,摆出了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
陈帼英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她进了房间之后,就背对着杜月笙,自己轻轻地解开了旗袍的纽扣……
杜月笙惊住了,眼前这美妙绝伦的场景使他五脏六腑都空了。
杜月笙不由地狠狠地拧灭了烟头,急步走上前来,恨不能一口吞了陈帼英。陈帼英见杜月笙来到身边,马上莲步轻移,晃到一旁,杜月笙的手按到了墙上。
此时杜月笙早已乱了方寸,大亨的派头消失了……
当夜,两人就在那间房子里住下了。
陈帼英虽说以前从未与男人睡过,但心有灵犀,一点就通……
时间近午时,杜月笙和陈帼英才依依不舍地从被窝里爬起来。
“帼英,我要娶你,做二房,做二房,你答应吗?”
“我身子都给你了,还有什么不答应的?只要你常常陪我,我才不在乎什么二房三房的。”
“好!”于是,杜月笙立刻给管账的杨渔笙打电话,要他马上收拾好后进二楼的房子,把四壁都贴上金纸,他要来个金屋藏娇。
当天下午,杜月笙就派人用一辆彩车把陈帼英接到了杜公馆后进二楼的洋房。从此,二楼全部给了陈帼英居住。
自从得了这个迷人的娘们,杜月笙吃喝拉撒全改在后进的二楼,不是十分重要的事,他就是不出二楼。接连好几个月,他也没有进原配夫人沈素娥的房门,这可砸破了醋坛子,沈素娥股股酸劲直往上冒:“哼,这狐狸精迷得他不知天日,连林宝的生日也忘了。”
这天夜里,沈素娥想起明天就是儿子维藩(系抱养的,小名林宝)的生日,丈夫没有一点表示,更加愤怒,“我去找他,看他怎么办!”
噔噔噔,沈素娥气急败坏地跑到后进楼房里,跑上二楼,摸到陈帼英的房门,正要用拳头擂几下,却从开着的窗户里传出了女人清晰的喘息声,这声音里含有一种欢快、满足的情调。
此时,沈素娥五内俱的玻璃舞池焚,股股酸水潮水般地直往上涌,她不由地想到当初自己才嫁杜月笙时的动人情景,浑身上下如火烧一般,禁不住大吼道:“不要脸的东西!”
房内听见突然的骂声,静了几秒钟,接着便是哗啦一声,像是一只开水瓶从窗口掷出来,几点开水溅到沈素娥脸上,烫得有些疼。沈素娥气得发抖,捂住鼻子咬住嘴唇往楼下跑,背后传来了半句话:“黄脸婆!”
沈素娥回到自己房内,哭了一夜。第二天红肿着眼皮儿,坐车到钧培里桂生姐跟前哭诉。桂生姐听完后,同病相怜,唏嘘着告诉她自己的丈夫黄金荣同样也喜新厌旧,如今抱着戏子露兰春这小娘们儿不放,“也冲着我叫黄脸婆哩!”说着,抽泣起来,随后是两人抱头痛哭了一阵子,共同得出结论:男人都是没良心的色鬼,都是吃着碗里看锅里的馋猫子。如今生米已煮成了老熟饭,闹也无用,还不如自行其乐,自己尽情地玩耍玩耍,许他州官放火,就不许咱百姓点点灯?
从钧培里回来后,沈素娥像是变了一个人。她把孩子的事,全部掼给佣人去管,自己跑戏院,上公园,看跑狗,赌赛马,还拉上一帮小姊妹,轮流做东搓麻将。她在杜公馆来去自由,没有人去管她的闲事,而杜月笙呢,也就落得耳根清净,与陈帼英一心一意做好事,再也不必有人败兴了。
俗话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春去秋来,时间早过了半年。原来亭亭玉立的陈帼英,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全变了模样,也有了一张蜡黄皮,腆着个大肚子,整天想着吃杨梅。
杜月笙觉得没劲了。
且说自清朝康熙年间“弛海禁”以后,放宽了对海上运输的禁令,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得以迅速发展了以后,大批洋人来到上海滩,把上海变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旧上海的娼妓发展也随之登峰造极。
最早进入上海开业的妓女有两种,一种是苏州妓女,她们是善于弹唱说书的艺妓;还有一种是民间戏班中的坤伶,她们是由原来的卖唱艺人逐渐转化成公开或半公开的妓女的。但上海在清朝道光以前,妓女往往标榜“卖艺不卖淫”,妓院称为“书寓”。鸦片战争前后,因增加兵防,妓院迁进租界,由于租界完全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市面“繁华”,加之租界基本上不制约妓院活动,只要妓院向租界工部局领取执照,按时交纳营业税,即可公开挂牌营业。这时,上海妓女的卖淫开始公开化。
旧上海的娼妓主要来源于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其中江苏约占90%,浙江约占6%,广东约占4%,另外还有少数其他地区来沪的妓女和外国妓女。妓院开设较集中的场所,最早在东门一带,清道光后,迁入西门附近,到清末,主要在宝善街一带。民国时期,妓院或妓女集中的地区有好几处,如闸北的天道庵路一带,十六铺的横马路一带,以及虹口、八仙桥、北四川路等地。
这些娼妓原本多是些良家女子,她们之所以堕落风尘,沦为妓女,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卖身还债以及被拐骗引诱。一旦落入陷阱,就一辈子受流氓、老鸨、龟奴的钳制,无法跳出火炕。
1911年的一天,在上海南京路大广里生生美术公司楼上一间破旧的小亭子间里,一个老妇缩身病榻,凄凉而死。死后,竟没有人来替她收尸。谁会知道,这个枯瘦如柴的老妇,就是1897年被上海的《游戏报》评为沪上四大姿色超群的妓女之一“林黛玉”。
从“林黛玉”之死,足见旧上海娼妓的命运多么悲惨!
旧上海的妓院和娼妓也有等级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书寓
妓女被称为“先生”,她们以陪酒弹唱为主,用艳色招徕客人,一般不卖身。
(二)长三
低“书寓”一等。妓女被称为“倌人”,也有称“先生”的,这里的妓女卖唱也卖身。
(三)幺二
妓女大都是老鸨的“讨人”或“押账”,失去身体自由。陪客留宿一般收费二元。
(四)烟花间
在销售鸦片的烟店里,雇用一些女人,名为给客人装烟,实则秘密卖淫。
(五)钉棚
开在棚户区里的妓院。妓女多老丑不堪,故都在晚上暗中接客。
(六)野鸡
这类妓女没有固定妓院,也没有营业执照,一般在马路上“游击”拉客。其中有些是临时妓女,待还债赎身后从良。
杜月笙是个闲不住的人,陈帼英肚子大了,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妓院,他常常找那些姿色艳丽的妓女,一睡就是一夜,但这些妓女都是与许多男人对阵的,杜月笙与她们一起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这一日,杜月笙来到一家书寓,想找两位漂亮的“先生”开心,看能否弄到外面一睡。
忽然,一阵悦耳的琵琶声传来,他寻声看去,只见一身材小巧的少女,杏眼含春,正在专注地弹奏。
大概是发觉到有人驻足,少女马上停止了弹奏,提起琵琶进里屋去了。杜月笙这才发现这少女生得小巧玲珑,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当即,他找来书寓的老板,问:
“刚才弹琵琶的‘先生’是谁?”
“她呀,叫孙佩豪,是唱苏滩的筱桂的外甥女,怎么样,杜老板,愿意不愿意指点一曲啊?”
“哪里,哪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愿意洗耳恭听,不知孙先生可愿以雅和俗。”
说着,挥了一下手,后面的随从递上了五百块钱。
老板见了五百块钱,眼睛亮了许多,兴奋了许久,说:“杜先生实在太抬举敝馆了,能为杜先生操琴,这可是佩豪的福气呀。”
说着,老板将杜月笙领进一间洁静的雅舍,坐定后,孙佩豪款款而至,对着杜月笙鞠了一躬,启动朱唇说:
“请问杜先生赐教哪首曲子?”
“孙先生太客气!只要是你弹的,我都洗耳恭听。”
“那我就见笑了。先来一曲《凤还巢》吧。”
孙佩豪说完,就开始运动十指,在琵琶弦上操鼓起来。虽说她是纤纤细手,但弹拨起琴弦来却十分有力,琵琶声如同疾风吹雨,响彻屋宇。
杜月笙原来并无听琴的雅兴,他的两只眼睛不住地盯住孙佩豪的小脸蛋。那小脸蛋白乎乎的,恬静而秀美,眼睛和鼻子都透着一种天真无邪的气息。
一曲终了后,杜月笙找到书寓的老板,问:
“刚才这位孙先生年方几何?”
“正值二八年纪。”
“身子还完好吗?”
“完好,这点请杜先生放心,我们这里的姑娘是只卖唱,不卖身。”
“那好,这位孙先生由我包了,不准她再见任何客人。”
杜月笙挥挥手,有人送上来一张支票。
“啊,两万块呀?杜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我是要为孙先生赎身。”
“这,杜先生?”
“好,再加一万,这总该行了吧?”
老板赚了两万多块钱,二来他不敢得罪杜月笙。
“去汇中饭店包一套房,这几天先让孙先生在那里住。”事情讲妥后,杜月笙吩咐手下人。
当天晚上,孙佩豪告别了书寓,住进了汇中饭店。她知道杜月笙赎了她,他要娶她,但她不知道他怎么娶。
从杜公馆来的女佣人侍候着孙佩豪洗过澡后,杜月笙来了。孙佩豪急忙起身。
“杜先生,晚上好。”
“孙小姐,你好。”
女佣人此时知趣地离开了。
“佩豪,”见房里没有其他人,杜月笙把孙佩豪揽进了怀中,“晚上一个人在这里怕不怕?”
孙佩豪脸涨得通红,说:“怕。”
“我在这陪你,不用怕。”
说着,杜月笙就动手解她胸前的纽扣。孙佩豪虽不情愿,但也不敢怎么反抗。
几天后,杜月笙把孙佩豪也迎进了杜公馆,住进洋房的三楼,他富丽堂皇地装饰了一番,全部留给孙佩豪居住。
沈素娥更加绝望了,她原想自己冷落一阵子以后,丈夫会看在结发夫妻的情分上,改变态度,重温旧好,起码也可以与二姨太平分秋色,自己还不失内当家婆的身份。可是,杜月笙又娶进来了一个二八年纪的三姨太,竟把二房太太也丢在一边了,何况我这个三十开外的黄脸婆呢!
幻想彻底破灭了。她在心里恨恨地说:“许你沾花惹草,就不许我在外面接露水?要我为你守活寡,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