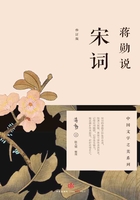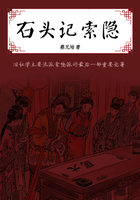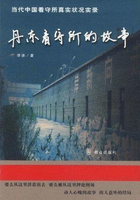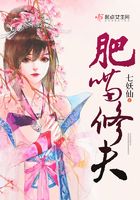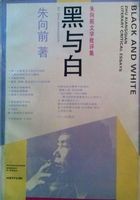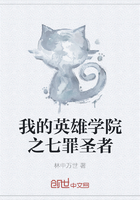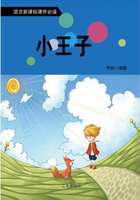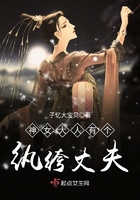进一步,放宽视野,从时人荐举书信、征召令中,我们也能看到,西晋时所高看的道德品行在渐次让位于文学才华。如果说,因文学才华而拔擢,在西晋尚不多见;东晋以后就较为普遍了。建武元年(317)征明僧绍,“标志高栖,耽情坟素”;永明十年(492)孔稚珪荐杜京产,“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沉吟道奥”;次年《斩王奂诏》“拔其文笔之用,擢以显任”;萧绎荐鲍几,“博涉文史,颇闲刀笔”;任昉荐王暕,“居无杂尘,家有赐书,辞赋清新,属言玄远”;刘孝仪荐贺玚,“幼能斧藻,长则琢磨”;又荐江兴,“颇涉书记,弥闲刀笔”;甚至到了后来,行文的风格也为之一变,如萧绎为东宫荐石门侯,“文传梦鸟,学重灵蛇,点漆凝脂,事愈卫玠”,就愈加绚其文采,烂漫无边了。更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选择储君萧纲,首先推重的却是“文义生知”,而不论其理国的才干——这不能不说明文史在武帝心中重要的位置。据此可以断定,其因文学才华而被举荐的比例无疑在日趋增大。这正印证了《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论》以及李谔《上书正文体》中的判断:
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姚察的意思很明确,所谓的“文史”,以其举的例子“二子之作,辞藻壮丽”来看,显然是侧重于辞藻,任昉、江淹也正擅长于此。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恪传》中所载:“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子恪少亦涉学,颇属文,随弃其本,故不传文集。”此处显然是以“文史”、“文学”互称。正是感于文史的重要,高门子弟王僧虔宋世就曾劝诫其子:“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说白了,只有读书,才能策试、辟举、文化传家,维持或增进家族的地位。进一步,这种“文史”转向,应当始于宋代:
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
宋武帝以一武夫爱尚文史,实开先河,这也是那一时代的整体氛围;只不过,其所爱仍多限于经史。太祖赐萧思话弓琴,手敕曰:“丈人顷何所作?事务之暇,故以琴书为娱耳”,则事务之暇以琴书自娱,即重视书籍、文化修养;重要的是,“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宗)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这也说明从上到下,甚至底层乡曲也都以文义为高,可见社会浸润之深、之广。一句话,“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辩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词,文实忤主。文词之为累,一至此乎”。沈约批评的文辞之累,大约是指没用对地方。承其流风遗韵,到了大明(457—464)时代,才有了质的改变,“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敏”,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从《宋书》卷七《前废帝纪》、《宋书》卷八《明帝纪》的《求贤才诏》中,更能看出对文史才能的明确要求:
其有孝性忠节,幽居遁栖,信诚义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识,干事治民,务加旌举,随才引擢,庶官克顺,彝伦咸叙。
若乃林泽贞栖,丘园耿洁,博洽古今,敦崇孝让,四方在任,可明书搜扬,具即以闻,随就褒立。
虽然“文敏博识”、“博洽古今”几乎淹没在“信诚义行”、“敦崇孝让”的道德海洋,但与先前相比,至少国家诏令中已明显突出了文史标准,文史跨入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这里的“文史”只是宽泛意义上的概念,本身的内涵随时代而略有变动,即以《陈书》卷六《后主纪论》“皆以文学相处”来论,就明显偏于文学方面,其史的方面,则不甚重视,或有意忽略。宋明帝泰始三年(467),议秀才考格时谢超宗认为:
非患对不尽问,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宁劣五通而常;与其俱奇,必使一亦宜采。
谢超宗的建议没被采纳;但“患以恒文弗奇”却无疑是当日社会主流思潮所追求的一个方向,这也实际上显示策文的评价标准业已发生了转移。汉魏时,策试要求直言极谏,于事有补;这一点,宋齐以来,确实发生了转移、变更: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
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
“辞不贵奇”,批评的话语中正看出时人是“贵奇”的;《诗品》评任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是以诗不得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人自藻饰”的氛围下,自需“新奇”才能脱颖而出;王僧孺为时人所重,就在于“新事”;而“新事”,不正是“奇”嘛。元嘉时,王微就坦言:“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南齐时张融自称“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又说:“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张融不无自得的话语中,正看出时人对“奇”不懈的追求。不妨说,就是在这普遍求“奇”的氛围中,谢超宗才对察举制度提出了这一求“奇”的观点。“承平”之际,自可以文学来点缀升平。妇人韩兰英有文辞,宋孝武帝时“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独有偶,齐明帝建武初,琅邪王寂“欲献中兴颂,兄志谓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显然,以文学来邀功,祈求腾达,一时间大有人在。
既然文学才华在举秀才中日益凸显其重要作用,甚至大有取代举孝廉之势;那么,文学对整个社会的辐射,自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次展开。这种氛围下,甚至权力高层,也不得不如此。《梁书》卷三十七《何敬容传》中“自晋宋以来,宰相皆以文义自逸”,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为此,“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嗤鄙”的背后,正看出时人对“庶务”不屑一顾,对“文义”情有独钟。或许正因为此,这一时节有治世才干的人颇为缺乏,刘宋时刘湛就曾不无狂言:“今世宰相何难,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其敢狂言,正因时无其人。文史日渐兴盛,甚至让先前受重视的儒学、隐逸孤高之士也相形见绌、黯然无光。萧齐皇室后裔萧子显也感慨儒风不纯:“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间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萧氏的感慨正显示出宋齐以来文史对儒学的强力冲击,也即裴子野所说的“大明之代,实好斯文”。
不过,不管后人如何诟议,秀、孝策试毕竟使一些人脱颖而出,在当日具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王融、陆厥、陆倕、张率、丘迟、何逊等都成了研究这一时期文学所不可绕开的人物,他们以一己才华,为南朝文学的繁盛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固然其间发展的方向不无偏离、旁逸斜出。梁、陈时日益重视的秀、孝察举,其意义也就在于此吧?但是,也毋庸讳言,这种以文史才华作为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东晋南朝文学的繁盛,固然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但文学真正的繁兴并未到来。究其实,恐怕有三点原因:一,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体——高门子弟,以一家利益为转移,甚至在朝代鼎革之际,也只是将“一家物与一家物”,一己门第岿然不动,自然不去关心、关注社会民生。“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看似通达的语调,却饱寓感伤、痛楚,萧子显虽有可能感于一家的变迁,但他正道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晋以来普遍的现实。南朝的史籍中是绝不见《忠义传》的,赵翼在遍检南朝诸史时指出:“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二,士人多以“事功”为耻。上所言“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以及张岱拒绝齐武帝封赏时说的话,都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说,家贫尚可接受,一旦因事功赐禄,则万万不可。三,东晋南朝,尽管一再下诏求“谠言”;然一旦对时政严词批评,又多不为时主所容,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梁武帝对贺琛“陈事”的极端态度,“大怒,召至书于前,口授敕责”;这就让本不愿意直面时政的人更噤若寒蝉,不留意时政了。这些都不能不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也只能在形式、遣词造句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而不可能洞达社会、关心民漠。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梁末侯景之乱,一些文人播迁北上,如徐陵、庾信、沈炯等激于时变,才在荒寒的异域吟唱出动人肺腑的时代之歌。
$第三节 来自主流的声音:从孙绰到傅亮、
谢灵运、颜延之
显然,因评价标准、视野的差异,当下文学史评价较高、看好的作家,当日不一定处于主流地位,甚至还处在边缘,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诗品》列陶渊明为中品,《文心雕龙》也基本上没有评价。《宋书》、《南史》、《晋书》中陶渊明只是作为一介隐士列入《隐逸传》,而不列入《文苑传》,这是史臣的观念。当日与之深交的颜延之,在其死后作诔文,也是直称“陶征士”,“南岳之幽居者”,文中凸显的也是隐居不仕的高洁,对其诗文,仅称“学非称师,文取直达”。八、九十年后,梁萧统第一个整理陶渊明文集时,其所作序,评价才略微高一些:“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因此,在历史的存在中,钩沉当日来自主流的声音,无疑更能较为真切地探求骈文迁变的轨迹。
这种主流的声音,可先追溯到东晋中期的孙绰。孙绰在当日的官职并不很显赫,只是作过扬州刺史、建威将军殷浩长史、右军将军王羲之长史、永嘉太守、散骑常侍等;就是后来的散骑常侍,也不过是第三品。但孙绰的文学名气甚隆,“于时文士,绰为其冠”,东晋前期位望最高的大臣“温(峤)、王(导)、郗(鉴)、庾(冰)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可见孙绰在当日声名卓著。历史上盛名一时的永和九年(353)兰亭聚会,尽地主之谊的王羲之作序,孙绰则写《兰亭集后序》,这不能不说孙绰的文名时望之高。孙绰也一度以此自负,曾以其作《天台山赋》示友人范荣期:“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也。”
咸安元年(371),孙绰卒后,一时间文采出众、声高位尊的当推傅亮。东晋中期,孙、许并称;许询擅长玄谈,其文学名声却不免逊色许多,孙绰本人就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至于傅亮,则“博涉经史,尤善文词”, 据《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桓玄篡位时,就已初显名声:“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大约在义熙九年(413),“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为朝廷撰写表策文诰,自然看出傅亮在刘裕心中的地位。之后,傅亮又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少帝——这种贵显的地位,当然更易影响当日文坛的风向。但好景不长,傅亮于元嘉三年(426)被杀。那么,此后谁执掌文坛的牛耳呢?
至于今人所推崇的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与鲍照,当日的实际地位是不一样的。《宋书》中,鲍照不仅没有专传,仅附于《刘义庆传》后;而且,尽管鲍照当日宋孝武帝刘骏又“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其有意夤缘攀附,元嘉时写《清河颂》,甚至曲意逢迎,也终究不为所用。重要的是,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评价鲍照类“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甚至定性为时人鄙夷的“郑卫之音”,《诗品》列鲍照中品,且评“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都看出时人对鲍照的评价委实不高。这种文风,自然不会进入主流,更不会为时主采纳。当然,作为一体,较为风靡、盛行,又是另一回事。至于谢、颜,则明显不一样。作为一流高门出身的谢灵运不仅“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且颇受文帝器重,“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又曾让谢灵运撰写《晋书》,文帝待之如此,民间更是认可,“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一时间洛阳纸贵。当然,谢灵运袭封康乐郡公,是被谢家寄予振兴家族重任的核心人物,也强化了这种声誉。谢灵运死于元嘉十年(433),之后,文坛的当轴人物就是颜延之了。颜延之,据《宋书?颜延之传》,早在义熙十二年(416)年,就已崭露头角:“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这之后的一件事,颇能显示当日的文坛风向:
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
揆之常理,傅亮时已身居尚书令的高位,又一度受武帝的器重,自不会与一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的颜延之斤斤计较,但实际上却“甚疾焉”。之所以如此,只能是颜延之声名鹊起,已严重威胁到傅亮在文坛上的话语地位,在一个极端推重文才的时代——无疑让傅亮不堪忍受。也许正是有意展示才华,“负其才辞,不为之下”,颜延之在隶事、偶对、藻饰方面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得到鲍照“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以及汤惠休“颜诗如错彩镂金”的评价。此后,颜延之虽“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辞甚激扬,每犯权要”;但也因时无其人,仍在主流的位置。孝武帝刘骏时,因其子颜竣贵重、权倾一时,颜延之也跟着沾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孝建三年(456)卒时。这一年,鲍照四十三岁,已经开始了诗坛的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