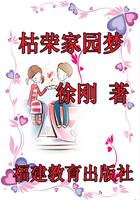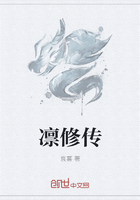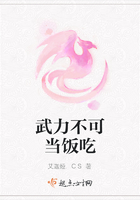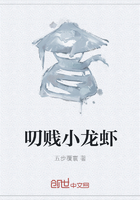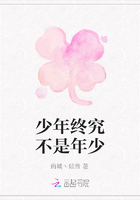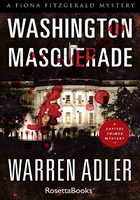这些赋作都比较短小,最长的应玚《正情赋》,也不过二百五十字;短的,曹植《静思赋》仅七十四字。在这短小的篇幅内,能更清楚地说明一些问题。这些同题共作之文,在内容、语言上多有雷同、类似之处;但其语言却颇为华丽,一则对句较多,一则藻饰烂漫。在上举曹丕《与吴质书》中曾详细、生动地描绘出当日侍游的场面,即“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往日可堪追忆;但是,没有真情实感,或切肤之痛,只是侍从、应命作文,恐怕大多只能就常情立意,而在辞采上下工夫。对此,刘勰曾认为昔人是“为情而造文”,而今赋颂却是“为文而造情”,根本原因就是心中没有感触,“心非郁陶”,只能“苟驰夸饰”了。徐公持也说:魏晋时大多数赋作“篇幅短小,寄托或有或无,即使有所寄托,往往寓意不深,主要以描写精细巧妙见长,逞词使才的色彩很浓,甚至令人感到文士们撰写这些作品是在互相比赛技巧和辞采。”只不过,可能限于篇幅、体制,刘勰没有具体指明“为文而造情”的途径。这一点却可由第二例中寻求答案。“为文造情”,除了藻饰、偶对外,就是隶事了。“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建安诸子所隶之典,多是经书,偶尔出自史书,或子书。对此,《文心雕龙?事类》有一个清晰的概述:
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张班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护,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刘勰所说的“捃摭经史”的情况,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之所以如此重视经书,按刘勰“宗经”的观点,即是“夫经典沈深,载籍浩汗,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为此,“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但深层次上,却是汉武帝以来以经学察举、重视经学的遗习。不过,由刘勰所说隶事的两种情况,即“略举人事”和“全引成辞”来看,此处更多的只是引用经书成辞,偶有涉及史书、子书的。如《文选》所选蔡邕《郭林宗碑文》,据李善注,就有《黄石公记序》、《韩诗外传》、扬雄《覈灵赋》、《西京赋》、《神仙传》、《典引》、《法言》、范晔《后汉书》、《易通卦验》、《汉书》、《孝敬援神契》等,《陈仲弓碑文》的情形也大致类似。至于“略举人事”,却不甚突出。也显然,这只能是一种低层次的用典,还远未达到六朝人化用、泯然无痕的境界。这正可说明在曹魏初期,虽有隶事较多,但其运用的技巧实在不甚高明——大多只停留在“全引成辞”、直接套用,或略作变更的层次,如上所举的“虽企予而欲往,非一苇之可航”,一看即知出自《诗经》,还远不能灵活点化、浑融一体,一如梁陈时呈现一种轻灵摇曳、动荡生姿的境地,这也正是初期不甚成熟的必然表现。如同样描写丽人,沈约《丽人赋》是:“响罗帷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薄暮延伫,宵分乃至。”格调明丽,一派轻盈、娇羞之态,顿现眼前。这与建安诸子《闲邪赋》之类的丽人描写,明显地不一样。与此相对应,是这一时期的对偶,也多为“正对”、“言对”,而少难度高一些的“事对”、“反对”;而且,即便是“正对”、“言对”,其工稳也颇欠缺。上所举例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初期的状态。
诗赋在整个魏晋南朝都占据主流地位,这从《文心雕龙》首先论述诗赋创作以及《文选》选文首选赋、诗中都能清楚地看出。而汉末以来,时人的文体辨析已日益明晰、细致和深入。《后汉书》记载当日著名文人的作品时,所列文体仅十来种,多为赋、诗、颂、诔、吊、书、赞、七言、祝文、连珠、笺、奏、论、碑、策等;曹丕《典论?论文》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据《全晋文》所录残片,已论及的有颂、赋、诗、七、箴、铭、哀辞、诔、碑、图谶、哀策十一种;陆机《文赋》论及的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据此,能看出除诗赋以外,多为铭箴碑诔等有韵之“文”。这或许就是时人最为看重的文体。为此,考虑到全面和代表性,这里选择碑诔、诏策、檄移、章表、连珠和书信等加以讨论。
碑诔:诔,据《文心雕龙?诔碑》,最早可追溯到周朝,《周礼?春官宗伯》载大祝掌六祝之辞,其六曰诔。《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表达对亡者的伤逝之感。诔,重在“累其德行,旌之不朽”。 至于碑,虽上古时帝王封禅树石纪碑,但直到后汉才较为兴盛,“碑碣云起”,蔡邕则为一代碑诔高手。其文体特征,曹丕认为“铭诔尚实”,挚虞则认为“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 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陆机《文赋》也说“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李善注为“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惨。”就是说,碑文强调征实、典正,诔文则又强调缠绵凄惨,能感人泣下。东汉到西晋,善为碑文的是蔡邕,至于诔文,则首推潘岳,作为精选多有定评的《文选》“诔、碑文”类,共选蔡邕二首、潘岳诔文四首,就看出其在时人心目的地位。但因受人所托,难免有“谀墓”的存在,蔡邕对此就颇多感慨。其碑文的骈俪特色,可见上文所论。就是说,碑诔文已向华丽的方向发展。
诏策:据《文心雕龙?诏策》,刘勰推崇三个时期的诏策,即武帝时期,“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明帝时期“崇学,雅诏间出”,及建安末潘勖《九锡文》,“典雅逸群”。这里,刘勰把诏策渊雅的表现推至汉武帝时期;那么,他推崇的“策封三王”的策文又是怎样的面目呢?《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载有元狩六年(前117)策封三王的诏书,为说明问题,仅选其一: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于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国。
显而易见,“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是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领域,其言辞倾向渊雅、深厚,自不待言。公孙弘为学官时曾上疏:“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 司马贞《索隐》曰:谓诏书文章雅正,训辞深厚也。就是说,诏书自需“文章雅正”,“训辞深厚”;关键是怎样才是“渊雅”,即“雅”呢?从上面“策封三王”的诏书中能看出,其不折不扣地是对《尚书》语辞、语调的袭用和仿作,或者说翻版,即本于经书立意。无独有偶,北周时,苏绰适应宇文泰政治改革的需要而仿《尚书》作《大诰》,以改革丽靡的梁陈文风,也是出于这种“典雅”的心理。这种以经书为典雅的观念,一直到曹魏时还是如此。曹丕《与吴质书》:“(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而《中论》,据《四库提要》,正是“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徐干《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矣。”徐干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得力于他饱读经书,“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弄清了“雅”的观念,再来看潘勖的《九锡文》。据《文选》卷三十五李善注,《九锡文》确实是多引经书之文,尤其是第一段,基本上完全引用、化用《左氏传》、《公羊传》、《尚书》、《论语》、《毛诗传》等。这也正吻合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的:“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总之,魏晋时,甚至到南朝,所认为的典雅,均是与引用经书密切相连,即本于经书立意,以训辞深厚、渊雅。或者说,皇帝制诏追求语言美化,以示训辞渊厚,更是西汉以来的一个传统。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议不举孝廉者罪诏》:“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就显示了由整齐对句而彰显的蹈厉奋发、铿锵有力文风。重要的是,因汉武帝尊奉儒家以后而形成的“引经据典”之风,该是这种“典雅”观念的远源。汉代经学自是极度繁荣,皮锡瑞《经学历史》就称之为“经学昌明时代”与“经学极盛时代”,进而辐射、影响到整个社会。为此,出于对经学的极端推崇,汉人在行文中多引经书之言,以增强说服力。
这里亦可以辞赋为例,“其高者颇引古训风喻之言”。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四章《经学极盛时代》。
然自(司马长)卿、渊(王褒)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扬)雄、(刘)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也。
刘勰考察文风的转折而断以扬雄、刘向为界,实可商榷。实际上,董仲舒已发其端绪。他的《举贤良对策》已经屡次征引《诗》、《书》、《春秋》,甚至直接化用《礼记?乐记》中的成句。也正是这种心理,形成了汉大赋颇遭后人指责的一味模拟、陈陈相因的创作模式。
檄移:檄移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主要用于军事,“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边有警,辄露檄插羽。”刘勰也说:“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但是,后来檄移也用于教令,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就是鉴于蜀地人心骚动,汉武帝特意派司马相如到蜀地安抚并发布的檄文;正在这一点上,李兆洛认为:“教令所颁,亦谓之檄,非止用之军旅也。”因与兵革征战相连,檄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明白畅达,不迂回婉曲,“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以直达为上。也正因临阵对敌,宣示声威,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出师先乎声威,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檄移特别强调行文声势。《文选》卷四十四共选四篇檄文,《喻巴蜀檄》可能含有追溯源流之意,其余三篇都是魏晋时的作品,即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钟会《檄蜀文》。这也是三国激烈征战下的产物。这中间气势最壮的就是《为袁绍檄豫州》。文章写于官渡之战前夕临阵对敌之际,为壮大袁军声势,陈琳以如椽之笔,处处以夸饰、奇丽之语,将袁、曹对比,尽力渲染袁军的威力无比及曹军的不堪一击,“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焚飞蓬,覆沧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灭者哉?”为此,有时还不惜夸大、歪曲,甚至编造一些骇人听闻、人神共愤之事。对此,刘勰也不免略有微词:“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但不管怎样,层层烘托、铺叙,一气呵成,奔泻千里,效果自然非同凡响。《三国志?记载》了这样一仲故实,“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这一事情就充分说明了其力量所在。不过,这种夸饰还是要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不能一味地无端生有,《檄吴将校部曲》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一篇文章,据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即伐吴前夕。这时,赤壁之战的失败虽已过了八年;但在魏国再一次攻打吴国时,又不可回避;这样,自难措辞,陈琳也不得不引以他辞,而曲为解释了:“是后大军所以临江而不济者,以韩约、马超捕逸迸脱,走还凉州,复欲鸣吠。逆贼宋建,僭号河首,同恶相救,并为唇齿。又镇南将军张鲁,负固不恭。”不管怎样,檄移是以声威、气势为重,这也是檄移的生命力所在,“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追求声威凌厉,张扬骋辞之风。阮、陈二人也可能正因辞采飞扬而得以任命为掌书记;这是因为,一旦遇到国家大事,或涉外事宜,曹操往往让人捉刀代笔,而绝不会以《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语气、行文来写作军国书檄。《三国志》卷二十一《陈琳传》所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裴注引《典略》说:“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都说明了这种情况。在此也不妨考察一下这四篇文章对偶、隶事的比率。整个来说,檄文中偶对并不很多,整齐、工稳的偶对又少之又少。不过,中间出现的一个情形却不可忽略,语句虽不偶对,但确实在以骈偶之辞来运思成文,如上面的“以韩约、马超捕逸迸脱,走还凉州,复欲鸣吠。逆贼宋建,僭号河首,同恶相救,并为唇齿”,虽不对偶;但连续三个四字句并列,语气连贯而下,又是何等的整齐。对此,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曾有精到的论述,他说:“由汉至魏,文章变迁,约有四端。”其中之一即是:
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专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
这一点相当重要,一定意义上比单纯的对偶更重要,因为它足以代表时人思想的重要转变,即从无意为文、不甚重视到以文章为不朽、为勋绩的观念,再到以骋辞为手段达到这一目的。这种观念相当有力地促使文章骈俪化的发展。
章表:《文心雕龙?章表》载:“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曹公称为表不止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这里,有两个问题:一、被称为“台阁为式”、“天下第一”的左雄、胡广章表是怎样的情形?二、既然魏初表章“求其靡丽,则未足美”,则为何曹魏时的章表迅速地向骈俪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