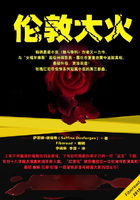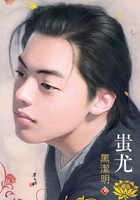来源:《中华传奇》2010年第09期
栏目:传奇人生
也许我的肉体只能蜗居在大别山的一隅,但我的灵魂会跟随我的学生走向四方;我是荒原上的一支电线杆,也许只能永远地矗立在那儿,但我能把希望和光明送向远方;我可能永远是一座桥,能让学生踏着我的身躯走向希望的彼岸,我就心满意足了……
——汪金权
2010年7月14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国务委员刘延东、教育部长袁贵仁等领导亲切接见了参会的全国教师代表,代表们合影留念时,无数的闪光灯聚焦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一位白发老者身上。人们不禁要问,这位满面沧桑、和霭慈祥的老者究竟是谁?怎会被刘延东和袁贵仁簇拥在正中间?仔细看过之后,人们这才发现,他不就是中央电视台等全国二十多家权威媒体集中报道过的扎根大别山区二十二年,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十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的全国优秀教师汪金权吗?
汪金权于1963年出生于蕲春县狮子镇郝子堡村枫树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母为其取名“金权”,蕴涵着身处底层的贫穷农家对子女前途最美好的愿望。他母亲陈细花万万没有料到,日后这个儿子的人生选择恰恰与“金”、“权”背道而驰。
1983年,汪金权以全县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汪金权以华师“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被分配至蜚声全国的黄冈中学任教,没想到一年后,为了献身山区教育事业,扛起日渐倒伏的山区教育大旗,他毅然回到了蕲春县最贫困、教学环境最差的蕲春四中。
作出这个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决定,汪金权说,当时的黄冈中学,锦旗纷至,让人陶醉,名师云集,令人向往。但是,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汪金权说,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激励和鼓舞了他,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做一滴呕心沥血的甘露!
蕲水年年东流去,群山岁岁送英才。二十二年的执著坚守,青丝已成白发;二十二年的苦心育人,汪金权给无数贫寒学子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迄今,汪金权已经亲手将2000多名淳朴的蕲北学子送进了全国各地的近百所大学。
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许多代表私下与他交谈时都以前辈相称,谁曾想到,这位两鬓斑白的“老前辈”现龄仅仅四十七岁!
“那我调回来!”
教师是一项需要献身的事业,在我看来,教师更是一项充满激情的事业,让我的智慧得到发挥,让我的个性得到张扬。
——汪金权
淋着盛夏的雨水,25岁的汪金权扛着满满一编织袋的“家当”快步走在家乡泥泞的山路上。此刻,他的思绪一如那飘渺的雨幕,轻盈漫散开来,他不知道母亲知道自己回到四中教书会是喜还是忧,但想到自己即将面对面地教育家乡的孩子,手把手地把他们引向人生的远途,能够将自己的多年所学直接回报乡土,想着孩子们脸上露出的笑容,想着能早日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他的步伐就更坚定了。此刻,他不觉得这大雨是老天对他的考验,反而觉得入眼皆是纯然美景,心间无限畅快淋漓。他小跑起来,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回到那生他养他的深山小村,那里曾是他大学梦的起点,如今,为了另一个更神圣的梦想,那个已经长大的孩子,他又回来了!
当汪金权顶着编织袋,湿得像只刚从水塘里跳出来的山猫一样嗖的一声蹿进家门时,把正在堂屋收拾碗筷的母亲吓了一大跳。汪金权放下喝饱了雨水的一袋衣物,一边抖着身上的雨水,一边喊了一声“娘!”母亲看清他时立刻由惊转喜,连忙拿出一条干毛巾帮他擦头上的水。看着浑身湿透的儿子,面容是那般憔悴,身体也似乎又瘦削了不少,母亲差点掉下泪来,强忍住,扭过头去说:“儿啊,我给你热饭去。”
母亲已经从四叔那知道了汪金权要离开黄冈中学回蕲春四中教书的消息,早早就把东厢房收拾好了,四叔说要到收高粱的日子才回的,没想到儿子会提前在这么一个雨夜赶回家来。汪金权辞了市里学校的工作回到邻镇的高中来教书,从大都市回到这连路都没有的山村,从众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山村老师。母亲本来是不同意的,但她也知道儿子的脾气,已经做下决定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也是作为母亲的她从小就灌输给儿子的思想,汪金权年仅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从小到大母亲都是激励儿子凡事要自立自强,想好的事,就要拼尽全力的做出个样来。母亲虽然没文化,但头脑不固执,从小到大,她尊重儿子的决定,时时处处维护儿子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尊严,这一次也不例外,她坚信,儿子决定的事,一定错不了。
母亲热好饭时,汪金权已经把湿衣服从袋子中拿出来在屋里扯了根绳子晾好了,他又从袋子中提出一捆书来,书用塑料袋包得里三层外三层,而且裹在衣服中间,拿出来时竟一点也没湿。
那一夜,东厢房的灯光一直亮到了后半夜。
国家级贫困县蕲春,当时共有四所高中,除一中在蕲春城关外,其他三所都在乡镇。蕲春四中就坐落在地处鄂皖交界处的闭塞落后的张榜镇,离蕲春县城有一百多里路,是县里出了名的末位高中,教学设施老旧落后,连老师的办公桌都无法做到一人一张。来这里的学生都是中考分数上不了重点高中的末批次学生,最关键的是教师编制不足,三百多个学生,才十几名老师,教学任务之重可想而知。校长办公室里韩鼎朝校长正在望着窗外犯愁,今天是老师们报到的日子,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今天刚刚放晴,老师们正在忙着清理淤塞的下水沟。看着晴天扬沙场雨天淤泥塘的操场,韩鼎朝校长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
韩校长走到办公桌边,看着桌上摆着的两份辞职信,心里又是一阵莫名的烦躁,眼看就要开学了,本来教师人数就不足,现在又有人要辞职,这哪是辞职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分明是嫌四中条件差,托人找关系调往条件好的学校去了,可是又能怎样,谁叫咱这儿穷呢。忽然电话响起,韩校长迟疑了片刻,接起来,面无表情地听着电话,连说了三声“好的”之后,缓缓挂断。电话是县教育局打来的,电话里说,有两名教师已决定调离四中,但已安排了一位年轻教师调过来,教育局那位负责人事调动的科长还特别强调:“这回调来四中的汪金权老师是华师的高材生,绝对比调走的那俩师范生强得多!”韩校长除了连声说好,已经没有别的说词了,这样的调令每学期都有,调来调去,学校的老师眼看着越来越少了,这意味着他当校长的工作难度也将越来越大,走的老师越多,留下的老师肩上的担子就会越重,连他这个当校长的都不得不兼两个班的数学课,今天说是走两个来一个,来的还是华中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听着那利禄味十足的名字就知道这绝不是一个能踏踏实实在这穷乡僻壤呆得下去的人,谁知道他哪天能来,来了又能在咱们这呆几天?唉……这学期的课还要不要开了?韩校长正生着闷气,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抬头看时,见到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办公室门口,逆着光,看不清模样:“你是……”那人近前几步,把随身带的一个行李包放在一旁的凳子上自我介绍起来:“校长您好,我叫汪金权,从这学期起就成为贵校的一员了。”一字一句字正腔圆,韩鼎朝校长连忙换上一副热情的笑脸离座相迎,握手倒茶深表欢迎。
这一天是1988年8月25日。
下午,开学工作筹备会议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召开,汪金权扫视了一下全场,看到的情况让人心惊,到场的教师连校长在内也不过十二三人,从大家的外表来看,年龄过五十岁的差不多有十人,这种年龄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仅此一点,汪金权便深深感到了作为年轻教师,自己身上的担子之沉之重,这里才是真正需要自己“掏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地方啊!
校长向大家介绍了汪金权,他把电话中教育局领导向他介绍汪金权的话一字不漏地向大家复述了一遍,大家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因为大家知道,华中师范大学可是全国知名的重点师范大学,县里的重点高中蕲春一中都没有几个老师出自华师,蕲春四中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华师毕业生来校任教。
会上,汪金权作了简短发言,他谈了自己作为一名四中新人的“肤浅认识”,他说,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为人师表是教师的本分;终身学习、追求卓越是教师的根本;尽心尽责、服务学生是教师的使命。他说,他将与全体同仁一道为山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鞠躬尽瘁;为学生健康成长实现梦想修桥铺路,甘当人梯!
汪金权的简短发言慷慨激昂,在场的教师都对这位朴实无华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会后,韩鼎朝校长和总务主任田铭生将汪金权带到学校给新老师安排的宿舍前,那是一排红砖青瓦小平房,大概是学校建校时就建好的元老级建筑物了,青色的屋檐上长满了翠绿的青苔。总务主任田铭生推开一间宿舍的门,室内的地上已撒上了一层白石灰,地面看上去才不至于太“湿润”,因为刚下过几天雨,墙壁上漏雨的渍痕清晰可见,一张单人板床,一张学生用的旧课桌,就是宿舍里的全部了。韩校长满怀歉意地说:“实在对不住,学校条件太差,不知汪老师是否住得惯,真的是委屈你了。”
汪金权看了,爽朗地笑着说:“不差不差,比我家的房子还要好些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住得惯,请校长放心。”
让韩鼎朝校长没想到的是,眼前的年轻人竟会如此淳朴平实,跟以前调来的年轻人真的很不一样。临走时他照例还是对汪金权说:“以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能满足的我们尽量克服困难予以支持。”这句话,韩校长说得底气不足,汪金权也并未把它当成“尚方宝剑”。事实可以证明的是,直到若干年后,学校把这排小平房当危房拆除,汪金权都没向学校提过任何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住得惯”这话并不是汪金权的虚言客套,而是出自真心,他当然知道,跟黄冈市的教学首府黄冈中学相比,四中的差距不只一点半点。敏感的汪金权能猜出韩鼎朝校长临走时看他的那种意味深长的眼神背后隐藏的深意,他决定给韩校长写一封信,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那一夜,小平房的灯光一直亮到了深夜。
第二天一早,韩校长的办公桌上就出现了一份洋洋洒洒数千言的信,他把信从头至尾,看了三遍,最后将视线定格在落款上,那是笔力遒劲的三个浓黑大字——汪金权。
谈学生的成长、谈学校的发展、谈教学方式的改革,已经多久没有人向他这个校长上书言事了,或者是从来没有过,不然,为什么这个年轻人的建言书会给他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和共鸣?
这所暮气沉沉的乡镇高中是要有点新气象了。
晚饭后,韩鼎朝校长来到的汪金权的宿舍,他抽出了汪金权的备课薄,仔细翻阅起来,他想看看汪金权的业务能力究竟如何,他想给这个年轻人一些精神上的支持。那一夜,韩鼎朝校长与汪金权促膝谈心,直到深夜才离去。
窗外月朗星稀,夜已深沉,汪金权刚才与韩校长谈话激起的兴奋情绪依然没有片刻消减,他已经知道,校长是完全信任他,完全支持他的,还有什么比这种信任更让人欢欣鼓舞呢!
9月1日,学生报名完毕,学校正式开课了。
九月的蕲北,依然暑气未消,蝉声在耳,热气蒸腾。急促的上课铃声,宣告着暑假的结束,也绷紧了每一位教师的神经。
初来四中的汪金权,一人独挑两个班语文教学的重担,还是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重任在肩,汪金权知道自己半点也马虎不得。
他一头扑进教材研究、备课、作业批改中。为了上好每一堂课,他因陋就简,翻阅几乎所有能接触到的资料;为了让课堂效果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他的教案总是几易其稿,直至自己满意为止。
除了精心备课,他还阅读大量中外教育家的专著,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他默默给自己定下了向“名师”进发的目标。
当时的四中面临的难题太多,学校的教学设施老旧落后自不必说,条件太差必然导致留不住好老师,成绩好点的学生也不愿来。连续几年四中的升学情况都不理想,这一年的高考更是零升学。镇上成绩好点的孩子都舍近求远,想方设法到别的学校上学去了,在校的学生厌学的情绪也很浓。汪金权当时很清楚地认识到学校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即升学、辍学和乐学。乐学是最根本的,只要学生都能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就一定能减少学生的辍学率,乐学也能极大提高学习效率,学习效率高了学习成绩也就能很快提高,升学就不会是学校无法逾越的坎了。
在华师求学的四年,是汪金权教育思想逐步成型的四年,也是他沉浸书山的四年,加上他在黄冈高中一年的教学实践积累下的经验,在知识储备方面,汪金权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上课的第一天,一位年龄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陈老师特意走过来拍着汪金权的肩说:“汪老师,咱们学校可不比黄冈中学,学生比较调皮,你第一天上课,一定要抖出点威风来,那帮小子们都调皮得很,一开始不把他们镇住,以后的班级管理工作可就难得开展了。”
汪金权满脸真诚地感谢他的善意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