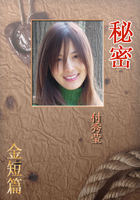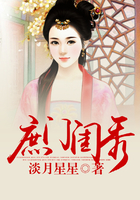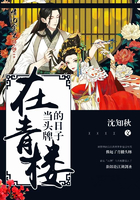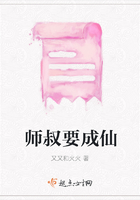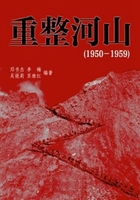那天的晚餐喝的是大酒,牡丹江当地酿造的小烧锅。先是三杯干,人人有份,谁也不能落下,这是第一轮,有礼有节;第二轮开始“提酒”,有理有据,诸如:久未见面呀,上次没喝好呀一类,你得喝,不喝不够哥们儿;当然还有三轮:老丛(深)是主席,老蒋(巍)也是主席,主席遇上主席,也得喝吧?喝!你们是作家,我们工会的小青年爱文学,他们得敬老师酒吧?得搞好关系嘛,不喝不行啊,得喝!几轮儿过去,厨师端上来一盘小鱼,说是镜泊湖的,掌长,头尾一顺儿,码得整齐。
工会主席说:“头三尾四。”我不懂,只能接着往下看。原来这哥们儿说的“头三尾四”是指鱼头冲着谁,谁三杯;鱼尾冲着谁,谁四杯。你想,这盘鱼尾能冲着谁呢!
韩作荣笑笑说:“行!就四杯,我喝。”
“慢,等我数数。”工会主席拿筷子扒拉盘里的鱼:“每条四杯。”哦——我惊讶了,目瞪口呆,那是九条鱼啊!四九三十六杯啊!
韩作荣稍作停顿,一挥他那香烟熏黄的手:“他娘的,拿杯子来!”把所有的杯子拿来,共十二个,一字儿排开,杯子不大,三钱的。待得斟满,这老兄便一口一个地往喉咙里倒。说实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疯狂的一次喝酒。工会主席倒安然无恙,韩作荣就显出了醉态:他破例地拿了几个易拉罐饮料回住处。在夜幕下,迎着小楼里透出的灯光,只见他将那易拉罐笨拙地夹在左右两边的腋下,还激情不减地挥着手说话,那易拉罐便落在地上,滚地的影子模糊可鉴。他捡起,复又夹,复又掉,如此反复,高大的剪影很忙很生动,令我悠然想起少儿时看过的电影加片——狗熊掰棒子的情景。这一幕,印在我脑际多年,要形成文字时就犹豫了,怕伤着哥们儿朋友。春节期间,聚在韩作荣家喝酒,说起这个故事,徐刚说:写!干吗不写?写出来,作荣才是个完整的人,真实的人!作荣的夫人郭大姐也作鼓动:怕什么?写他,他的故事多了。
作荣憨憨地说:喝多了的“洋相”何止这些,我还被人家绑在树上过呢。说的是一次喝得回不了家了,醒的少是女的,醉的多是男的,送不过来,就把他先绑在树干上,脸朝外,耷拉着脑袋等着。
我调侃说:听说是用裤带?
他说:哪呢!是用围巾,娘们儿干的。怕我走丢了,还把扣系在后头,真损啊!
我想:人的一生,谁没有年轻过?年轻时谁又没有造几件糗事?哈哈,年纪大了、老了,有几件笑话能供老哥们儿相互调侃,且也是又一件乐事。
作荣这几年身体小恙,不喝白酒了,我有些遗憾。
他说:“少给大夫找麻烦,少给家人添担忧而已。”
但他改喝红酒了,喝得很入味,很地道。去年我看到了他关于红酒的文章《有生命的液体》,他可堪为品评红酒的专家了。于是我就把朋友送的红酒留着,每年春节和老婆拎着,一道去他家,换得一瓶老酒喝。他给我喝的都是十年以上的老酒,几十年的友情就着陈年的老酒,还有郭大姐的酸菜馅儿饺子,这个年过得愈来愈有味道了,酒也喝得越来越有味道了。
今年是和徐刚兄相约一起到作荣家的,徐刚见了我就调侃,专门在我老婆面前揭发我的糗事。我老婆是黑龙江人,痛快豪爽,没心没肺,能和徐刚这厮调侃到一块儿。
老婆说:山西人就是会过,有几百瓶好酒舍不得喝,一箱一箱地买红星“二锅头”。
徐刚问为什么?
她说:怕以后老了没人送了,存着呗。
徐刚和作荣异口同声地问我:你准备活几年?我俩的就够你喝几十年的,别担心,老西子。虽是调侃,让我心里有些热乎。
郭大姐也是黑龙江人,说得更实在:我家还有两瓶三十年的汾酒哪,明年来喝。
老婆说:三十年的汾酒很值钱哪!郭大姐慢条斯理:多值钱也不能卖啊,留着干啥,喝喽。
作荣笑得苦不堪言;我却得意地笑着,期待着来年的春节。
酒渗透在我生活中是我的愿意,成为我工作的伙伴却是我的意外。我曾经有幸欣赏到了一幅不可复制的风景,并历史般地留驻心中,使我走上了对酒近乎迷恋的快行道。
1988年3月,贵州作家何士光来京开政协会议,建议《人民文学》组织一个有关茅台的征文奖项,他愿意负责联络促成。四川作家周克芹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也表示赞成。这个奖项定名为“茅台文学奖”,由茅台厂委托杂志社承办,文类为散文。七月评选揭晓,定于十五日在茅台酒厂举行颁奖仪式。主编刘心武因受邀出国讲学不能出席,委托副主编周明带队,我当时代理总编室主任,王扶代理一编室主任,听从周明调遣,一同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作家陆文夫、从维熙、谌容、叶楠、何士光、周克芹、乔迈、梁上泉、李宽定、顾汶光等,崔道怡作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评委也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