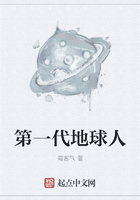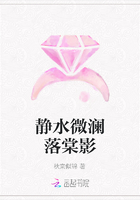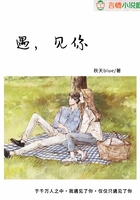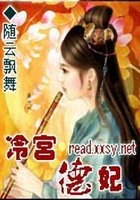我们经过仔细比对后发现,实际上“红军史”上的十一个暴动点,基本也包括了廖家同的十四个点在内,两者之所以形成统计学上的误差,是由于认定的方法不同而造成。譬如“红军史”记载的“沙河暴动”,是徐其虚、郑延青率领隐藏在太平山上的三十多名农民武装人员,经柏树冲至午夜后赶到沙河,与杨珂领导的二十多名农民自卫军会合,将驻有卢银冰民团二十多人的佛缘庵包围。战斗胜利结束后,在当地部分农会会员的配合下,又移兵前往攻打漆继堂(廖执言为漆霁堂)的庄园……因为置换了战斗现场,且增添了当地农会人员的参与,廖家同把“漆继(霁)堂庄园”列为又一个暴动地点。如此等等。哪一种方法论更科学、更严谨姑且不论,至少,他那种修复历史记忆求真存疑的个人执念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最先就是从廖家同口中,听到集中在这么一个姓氏身上的红色冲动的。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漆”字大概只能算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姓,但是不管谁走到了金寨县斑竹园一带,无论如何都不敢小视漆氏家族,不管是现在、民国还是前清。
其实历史遭遇到细节末枝时,常会有那么一缕的捉摸不透。漆先航,字袖海、号任之——当初漆家“先”字辈里一名德高望重的人物,但在不同的文字或口述表达中,漆先航的名字基本上为“漆树人”所取代,而有时亦作“漆树仁”。历史在相当大的余地里转圜腾挪游移不定……当然这里我们不敢完全排除另一种小概率的可能,说不定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下,恰是他自己改名由“人”而求“仁”的。
我们理解,由漆先航而漆树人或漆树仁,这种看似无意的改变,正是那位清光绪庚子年举人在历史链条上作为一个构成环节的隐喻。为了不至于造成新的混乱,我们权且还是将漆先航称为漆树人吧。
漆树人出身贫苦,后来读书求学有成,在外履职多年,历任河南巡抚参议员、省咨议局议员、河南省长葛县知县,陆军18师执法处处长,湖北省荆州府镇守使书记官,四川省夔州府书记官、征收局局长。在漆氏后人一篇缅怀其曾祖父漆树人的文字材料中,这是位被百姓称为“漆青天”的老先生,是忧国忧民,正值英年“不愿与狼共舞,毅然辞官还乡,以满腔热血投身到大别山革命事业中来”的传奇性人物。
关于辞官,最贴切地反映漆树人思想状况的可能莫过于他的《思归》:
半雅亭边雁阵斜,入来蜀道向天涯。
春前怕树忘忧草,雾里仍看解语花。
生事艰难疲战乏,冷官最易老年华。
司农最是翁常熟,归去与农话桑麻。
看透世事心灰意懒的漆树人返还家乡时,可能不会想到今后他将必然地走进斑竹园红色风暴的台风眼。《金寨红军史》中的漆树人是位着墨不多的开明乡绅,在有限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斑竹园、果子园农民协会开会时,大绅士漆树仁、徐朗山都在会上发言,支持农民协会活动,带头减租减息。”还有一段:“1928年冬,首先由周维炯、漆德玮做漆树仁的工作,动员他将他们带领的三个班农民武装参加到杨晋阶民团中去……漆树仁也认为这是发展他个人势力的上策,更相信周维炯和漆德玮的才干,所以同意了。”
漆树人的曾孙漆重诚告诉我们,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曾祖父漆树人把漆德玮、周维炯等族内子侄都唤了去。后者则借此机会建议漆树人想办法搞枪,建立自卫队。于是漆树人找商城县县长李鹤鸣借了十几条枪……这件事在《金寨红军史》里有相应的记载,区别在于史料上写的不是“李鹤鸣”,而是“柯干甫、柯寿恒”,此外漆树人还将在武汉买的六支枪也一并交给了漆德玮和周维炯。漆树人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想干什么事,我不反对,但是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你们就不要给我增加麻烦了。其实漆树人知道他们在搞共产党,也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漆德玙和漆德珷都加入了共产党,不过佯装不知而已。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爷不反对红色运动,但也不希望把事情惹到家里。
有价值的历史在于历史的真实,对漆树人以及当年那些与他类似的有财产、有地位的乡绅进行读解,离不开对总体历史境况和个体文化视角的考量。实际上漆重诚和我们都无法还原当年漆树人面对革命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是政权体制(虽然有些失望)的“旧臣”,且在体制笼罩下续延尊荣的一名体面的乡绅;另一方面,他的骨肉血亲的儿子们,偏偏又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要彻底砸烂这个体制的不归之路。
我们相信,在树影葱茏的斑竹园小河村,在多少个阴晴圆缺的月夜里,漆树人有过许许多多辗转难眠的时刻。老先生的文化、阅历和见识使他对“革命”及其代价的了解多于常人,他清楚革命是危险的,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走出家门很可能再也回不来。同时他还明白,包括他两个儿子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者踏上了这条道,就算十头老牛也拉不回头了。也就是说,事关这双重“不归”的现实思考,或许还需要确认他精神基因里中国传统人文的家国情怀,最终决定了漆树人在1920年代对待革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