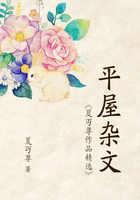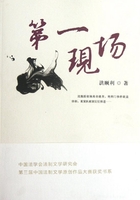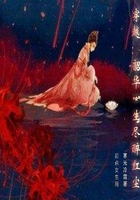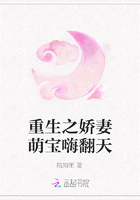史沫特莱被安排在延安城临街的一所房子里,同翻译吴光伟住在一起。吴光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留着长长的卷发,漂亮、活泼,来延安前在上海当过演员,现在被安排做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史沫特莱此后过上了普通红军战士的生活,穿一身灰布制服,简单、朴素。她不习惯睡炕,便把一张窄窄的帆布行军床支在炕上。炕前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架打字机和几本白纸簿,就是写作的地方。外间屋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毛泽东、朱德等人来访,就坐在那里同她谈话。
二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同志吃过晚饭来看望史沫特莱。
毛泽东进屋后,史沫特莱给他搬过一把木椅,请他在桌旁坐下。不一会儿,又给他端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毛泽东道着谢,接过咖啡,忽然问她:“‘谢谢’用英语咋个说法?”史沫特莱和翻译告诉他:“‘谢谢’用英语是Thankyou!”毛泽东听了,认真地学道:“三克油——”由于乡音太重,发音不准。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逗得哈哈大笑,毛泽东自己也给引得笑了。史沫特莱又教了他几遍,总算读得差不多了,但由于口音太重,读起来仍不是味。“以后你们就教我学英语!怎么样?”毛泽东恳切地说。“好啊!”二人一齐答应道。史沫特莱想不到毛泽东这样虚心好学,很受感动。毛泽东呷了一口咖啡,史沫特莱问他味道如何,他点头连连称赞:“好,好!比茶叶好喝!你们美国人很懂得享受嘛!”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再加上俏皮的话语,令史沫特莱忍俊不禁,咯咯笑了。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的乡音太重,便问吴光伟北京官话应怎样说,又向她学起来。但由于他的乡音已养成多年,很难改过来,所以收效甚微。他自嘲地笑了笑,说道:“这北京官话像英语一样难学吗?我就不信学不会,以后再跟你学。”接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漫谈,毛泽东询问起她在美国的生活情况,她给毛泽东讲述了她的早年经历。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北部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她幼年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母亲在别人家里洗衣服、做杂工,父亲则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贫困潦倒的一家人,靠她的一个当妓女的姨妈的帮助,才免于陷入绝境。她十六岁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过早去世,这使她十分伤心。为了摆脱与母亲同样的命运,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之路,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小的时候,她仅断断续续受过小学教育;但她依靠自学,在十九岁那年考入坦佩师范学校,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受教育机会。后来她又曾进入圣地亚哥师范学校进一步学习。在学校,她当过校刊编辑,磨练了自己的文笔。在坦佩,她曾与厄内斯特·布伦丁结婚,度过一段难忘的共同生活之后离了婚。1914年下半年,她谋得一个讲授打字的教员工作;两年之后,因为与社会党以及参加过1912年言论自由运动的人们有联系,还因为和印度民族主义人士的接触,又失去了这一职位。1917年,她迁往纽约。纽约的几年里,她在担任一份秘书工作的同时,还为社会党的报纸《召唤》和女权主义者领袖玛格丽特·桑额夫人的刊物《节育评论》撰稿,同时日渐卷入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当时,英国和美国当局把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看作一种颠覆性运动,这个运动的支持者在美国至少被视为叛徒。史沫特莱的活动,引起了英国和美国情报人员的注意。1918年3月,她和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分子萨里安德拉·纳什·戈斯一同被捕。根据“反间谍法案”,她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英的印度判乱。在“坟墓”拘留所里关押了六个月之后,她被交保释放。其中部分保释金是玛格丽特·桑额筹措的,因为史沫特莱还被指控犯了当地的一项反节制生育法。牢狱之灾使她的思想更为激进,出狱之后,在指控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她便在《召唤》上发表了几篇有关她同监的四位女囚的特写,揭露狱中的黑暗,题目为《铁窗难友》。此后她更积极投身于印度民族革命的行列。她编辑了新闻通讯《印度新闻》,担任“自由印度联谊会”的执行书记;并为该组织筹款、撰稿。由于连连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她不得不决定离开美国,于1919年前往柏林。在德国期间,她除了继续支持印度的民族革命外,还继续参加争取男女平等权力的活动,仍然和玛格丽特·桑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7年她把桑额请到德国去作巡回演讲,并帮助桑额在柏林开办了第一个节制生育所。她在柏林大学讲授英语和美国研究课程,还设法使大学当局接受自己成为了一名攻读印度历史的博士学位研究生。她用德语写了许多文章,有些发表在学术性刊物上,主要问题是印度史和妇女问题。她与当时德国左翼激进的知识分子都有联系,德国女版画家凯绥·柯勒惠支是她的朋友,两人曾为出版一本有关节制生育的小册子在翻译和插图方面进行合作。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在上海又积极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
毛泽东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史沫特莱讲述她的曲折经历,不时发出惊叹声,他手上的烟竟忘了吸,直到快要烧着手指才将烟蒂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