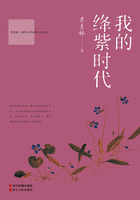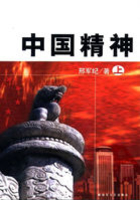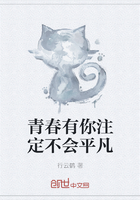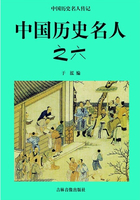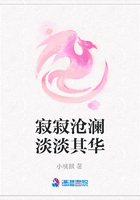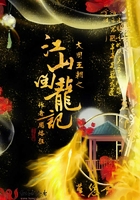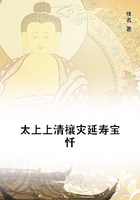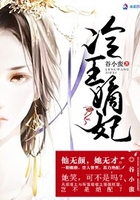横穿美国,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又依然茫然地原路返回,一连数月,一群茫然而带着偏见的欧洲演说家、学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作家、这样那样的理论家甚至美国问题专家鱼贯而行,欢呼雀跃地享受美国这道饕餮大餐。在飞机上、火车上、宾馆卧室滚开的炉灶上,在演讲会和招待会的间歇,他们许多人急不可耐地企图写日志,写日记。
起初,震惊于这道大餐之丰盛,又有些惭愧于东道主之慷慨,不习惯所受的重要客人之礼遇,他们克服了尽管是共同语言的障碍,不知疲倦地写将起来,把美国性格、文化和美国政治制度一一匆匆加以归纳。但是,就在这群中年人匆匆忙忙在中西部的俱乐部和大学走马观花的中途,他们疯狂写作的劲头减退了,他们的兴奋劲儿降低了,一是由于他们在各地受到盛情款待的烧酒,一是他们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没劲。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声望——他们经常发现,一周前关于土耳其现代小说的讲座受到了观众热情洋溢的反响,而现在对一场关于瓷器的幻灯片讲座,听众们的反响同样强烈。他们的日记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如下的记述:“我无路可逃!”“水牛!”“我算服了。”等等等等,到后来,他们一个字也写不出了。说话也口齿不清,未老先衰,眼睛就像裹了沙子的肉串,到后来被人搀扶着上了回国的轮船的舷梯,送他们的是肺腑之交的朋友(当然肺腑也各不相同),这帮朋友扶着他们的背,搂抱一番,把酒瓶、十四行诗、雪茄、讲稿塞进他们的衣兜,在船舱里举行告别聚会,又搂抱一番,然后嘻嘻哈哈地走了:他们要在码头上等待欧洲来的另一班船,要接待另一批初出茅庐的欧洲演讲者。
每年春天,这些人从纽约去洛杉矶:办展览的人、爱辩论的人、研究戏剧的人、鼓吹神学的人、货真价实的蠢人、痴迷芭蕾舞的人、美化未来的人、吹牛皮的人、大有来头的人、讲空话的人、热爱邮票的人、热爱牛排的人、追逐百万富翁遗孀的人、名声长了象皮病的人(象牙长而心眼小)、研究汽油的专家、主教、写畅销书的人、找作家的编辑、找出版商的作家、找美元的出版商、存在主义者、肩负核计划的严肃物理学家、说话就像嘴里含了埃尔金大理石球的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人、风风火火的哲学家、职业爱尔兰人(最卑劣的那种),恐怕还有出了几本薄薄诗集的肥头大耳的诗人。
在这一溜耍嘴皮子的人中,瞧瞧那些高个子戴单片眼镜的男人,他们一身皮革皂和俱乐部圈椅的气味,口气混杂着威士忌和狐狸血的味道,他们满口上流社会的龅牙,蓄着乡下人的胡子,英国制造出这些人,大抵是为了把他们派到国外,让他们在妇女俱乐部演讲,亏他们想得出诸如“谢德兰群岛蚀刻画史”这样的主题。这些人中,还有些专横霸道的男人婆,她们满头电烫发卷,脸皮河马般厚实,她们自称是“普通英国家庭主妇”,来美国的目的是要给美国有钱的、肥硕的、穿貂皮大衣的主妇们演讲,演讲的主题包括:医疗保障的不公、矿工的懒惰、安奈林·贝文先生的根根底底,英国人晚上不敢出门,因为街上的有组织棍棒党,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因为当权派拒绝让警察佩带左轮手枪,拒绝将各种名目的少年犯绳之以法。
还有那些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唯唯诺诺的英国作家,在平平淡淡为人遗忘多年之后,他们终于很不幸地写出了一本在大西洋两岸大红大紫的烂小说。在英国,刚刚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们倒也有节制地开心;一两次文学聚餐会后,他们就像聚餐会前上的廉价雪利酒上了头一样飘飘然起来。也许,随着可爱的钞票滚滚而来,他们开始做起作家的浪漫梦来,梦想退休到县里去养马蜂(也可能是蜜蜂),再也不写一个破字儿。但是,文学掮客的枪手来了,出版商雇的杀手来了:“你们必须去美国露露脸。你们的小说在那边红透了,我们也不奇怪。你们必须去合众国给妇女演讲。”这些腼腆的作家,他们从来不敢做演讲,更别提给妇女演讲——他们怕女人,不了解女人,他们笔下的女人就像不存在的东西一样,而女人也接受了——这些害羞的可怜虫叫道:“我们讲什么呀?”
“英国小说。”
“我不读小说。”
“小说中的女伟人。”
“我不喜欢小说,也不喜欢女人。”
不过,他们还是飘去了,坐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号豪华的包房,随身带着就像纽约的菜单一样长的约会单,或者查尔斯·摩根的书,不久之后,他们就将被女主人们紧紧地围起来,他们金鱼一样冷冰冰的小手也将忙得不亦乐乎,握住一只只热情慷慨滑腻的手。
我突然想到,欧内斯特·雷蒙德,《告诉英格兰》的作者,曾对美国妇女俱乐部做过一次巡回访问,每到一个镇子,他都受到当地最富有、最高大、最狂热的女士的留宿和款待。有一次,他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来接他的照例又是一辆牛高马大的车,里面塞了一个巨大的戴角质边框眼镜的商人——跟电影里巨大的戴角质边框眼镜的商人一模一样——还有他圆滚滚珠光宝气的太太。雷蒙德先生和这位太太坐进后座,车开了,是那位丈夫开的车。她立刻就讲起来,说她本人、她丈夫是多么开心,能有幸请他到妇女文学和社会之家,还恭维他,说他的书是如何如何好。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读过《索瑞尔父子》这么好的书,”她说,“人性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索瑞尔是刻画得最好的人物之一。”
欧内斯特·雷蒙德听她讲着,自己尴尬地看着前面。他看到的是那位丈夫脖子上的肉褶子。她一个劲儿地夸奖《索瑞尔父子》,到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
“我同意您的看法,”他说,“那的确是本好书。不过,《索瑞尔父子》不是我写的,是我的老朋友沃里克·迪平写的。”
头也不回,那开车的牛高马大戴角质边框眼镜肉褶子脖子丈夫说:“艾米莉,又露馅了吧。”
还有一些人,他们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游走于一个又一个文化活动社团:兜售英国文化的人,在美国一路混吃混喝又诋毁美国文化的人;在边远地区向女性听众鼓吹要复活超现实主义,其实这些妇女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在波士顿拿一堆珍贵的坛坛罐罐谈意大利伊特鲁斯坎坛坛罐罐。在这一帮横穿美洲大陆乐此不疲奔走于一个个俱乐部的演说者中,还有外国诗人、弱不禁风的吟游诗人、寻找一夜情的情种、想钱想疯了的演说者,还有从外国跑过来靠自己的存款过着日子的流浪诗人,我就属于混得最差的这帮人。
一个人踌躇满志、带着诚心和干干净净的讲稿,轻松愉快地奔向西部,要在那伟大的公立大学工厂里找到一份有报酬的归宿;另一个人却衣衫褴褛、灰溜溜地带着自己的诗和精心打印的讲稿踏上归途,我很纳闷,这两个人在途中会相遇吗?我为这两个人而痛心。一个人依然清纯,坐在火车包厢里得意地啜着一杯硕大的波旁威士忌,叼着粗大的雪茄,奔向那广阔的空间和那一张张期待的面孔。除了装文稿的行头,他带了一把新动力剃刀,刚在纽约的商店买的,这玩意儿大拇指一掰就启动,却割破了大拇指,伤口深达骨头;一罐剃须泡沫,只好用另一个没有流血的大拇指来开启了,喷出的泡沫不仅盖住了脸,也铺满了整个卫生间,这东西一下子就凝结了,把这地方搞成了一个北极的冰窟窿,两个暗自好笑的男招待才把他拽出来。当然,他还带了一件尼龙衬衣。看了广告,所以他坚信,这衬衣在宾馆里自己就可以洗,晾一晚上就干了,不用熨烫,早上就可以穿了。(我倒是用不着熨斗,有人毫无人性地写文章骂我,说我一身皱巴巴的,就像没理过的床。)
在火车站,他受到一大群牛高马大的剃平头诚挚的大学生的热情欢迎,所有人都像捕捉蝴蝶的爱好者,拿着捕虫网、笔记本、毒药瓶、别针和标签,每个人都有至少三十六颗白森森的牙齿。他们小心翼翼地簇拥着他,就像他是一个残废有钱不久于人世的姑妈一样,搀着他上了一辆汽车,一连五十多英里,车子以拆散诗人骨头的速度奔驰,一路上,学生们亲切地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眼下斯蒂芬·斯彭德在开哪个国际会议,英国诗人对一个他不认识的美国名人的作品有何反应,等等。对这些问题,他结结巴巴、模棱两可、夸张的英国口音,这一切证实了学生们的猜测:他是个迟钝的家伙。接着,他被带往只有几百人的小小的聚会,大家都相信,一位来访的学者走向讲台之前最需要的是足够的马提尼酒,这样他才能从讲台顺当地走下来。抓着快要胀破的酒杯,没过多久,在一阵阵无知的涌动下,他口若悬河而又傲慢地批评起那些文艺妇女的诗作来,这些女汉子个个出身高贵,她们玩文字,就像招待拿通心粉装盘一样熟练。他到头来才知道,这些有钱女人都是凶残的女猎手,专门收拾弱小狮子(就像他那样的诗人),她们竖着耳朵、张开扳机埋伏在西部的丛林里,而其中最凶残的一位就是当天晚上招待他食宿的女房东。至于演讲嘛,他只记得有鼓掌,兴许还有两个问题:“有人说英国青年知识分子都注重精神需求,这是真的吗?”还有:“我的包里通常都带一本克尔凯郭尔的书。你带什么呀?”
当晚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写下了一整页日记,混乱而尖刻地记述了第一次演讲的经历。其中一段概括了美国高等教育,到第二天,这段文字他自己都看不懂了。他睡着了,睡梦中,他在漫长黑暗的灌木丛间逃窜,后面紧追不舍的是一位梅布尔·弗兰肯森斯·梅哈菲女士,她手里端着一托盘马提尼酒,还有抒情诗。
又一位幸福而汗津津的诗人打道回纽约了,这个城市给他最初的印象无非是一堆可怜的房子,而此刻,经历了这伤痕累累的演讲季之后,这城市像吐司一样温馨,像冰箱一样凉爽,像摩天大楼一样安全。
(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