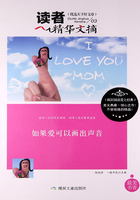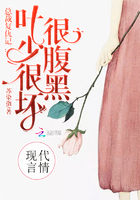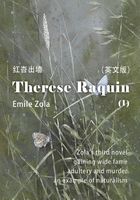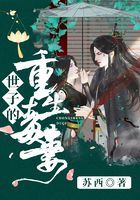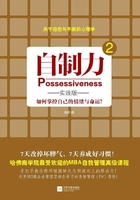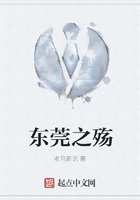“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对若干历史现象的回顾和再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在我国历史上空前深刻而彻底的文化革新运动,作为这个运动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即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也是一场空前深刻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和先驱者们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时候,对传统文化和文学曾经采取过一种偏激态度,通常对这种偏激态度的解释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向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发起猛烈冲击,并且大喊大叫地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而这种偏激是难以避免的。还有一种解释是当时文化革命的先驱者使用的是坏就是一坏皆坏,好就是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方法。这样的解释诚然都是对的。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深刻的历史原因,这在陈独秀的文学发难文章中已经涉及,他说当时“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他认为“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的“垢污深积”。正是这种旧文化的“垢污深积”在很大程度上使近代开始的种种文化改革的倡导和实践不能顺利进行,乃至半途而废,更谈不上彻底变革。这个历史教训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们在批判旧文化时的勇猛精神和偏激态度。习惯于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托古改制”现象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以“复古”为“通变”现象的人,曾为“五四”文学革命对文学传统的无情攻击而感到惊讶或困惑,甚至目瞪口呆,迂腐的守旧派更是痛心疾首,起而反对。“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守旧派又往往以保存、接受传统文学为借口来反对新文学,革新派又往往为了保卫新文学而忽略对传统文学的继承,这种现象也是为中国的具体历史状况所规定,而且有着种种复杂的情况,因此,作为一种历史经验来做再认识,或许也是必要和有益的。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在此之前,文学革命已由积渐酝酿到正式发难。1916年8月,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号召兴起一个像19世纪30年代“青年德意志”运动那样的文学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从之矣”。
1916年10月初,陈独秀致函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信中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同年10月,胡适致函陈独秀,认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稍后胡适又撰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提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重申他致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和“不避俗字俗语”等“八事”,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三大主义”。陈独秀尊胡适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之急先锋,他自己“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上,《晨钟之使命》《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都是文学革命发难的重要文章。如果说《文学革命论》较《文学改良刍议》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前者把文学革命看做是政治革新和思想启蒙的必要条件,而《晨钟之使命》更是着重说明新政治、新文明之产生与新文学之兴起之间的关系。《文学革命论》较《晨钟之使命》的明显不同则在于前者更多更具体地对中国传统文学作了审视和批判,这种审视和批判表现出作者反对旧文学的勇猛、激烈的革命精神,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了一种片面态度。那种勇猛、激烈的革命精神却又正是《文学改良刍议》所缺乏的。50多年前,郑振铎就认为《文学革命论》较之《文学改良刍议》更为激进,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陈独秀继之而作《文学革命论》,主张便鲜明确定得多了。他以“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辈”,而断然加以排斥……他高张着“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答胡适的信道:“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他是这样的具着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
从《文学革命论》全文看,陈独秀批判旧文学的激进态度表现为既反对传统文学的内容,也反对传统文学的文体,但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白话文学正宗”说,他在斥“十八妖魔辈”的作品“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的同时,却尊马致远、施耐庵和曹雪芹都是“盖代文豪”[4],也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虽认为韩愈文章“起八代之衰”之说并非“确论”,却又认为“然变八代之法,开宗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5]按当时的历史事实,李大钊、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汇合在一起,实际上就确定了文学革命的作用和内容:为了革新政治,势必革新文学,而为了革新文学,就要倡导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就要反对旧文学。事实上,要求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际上不仅涉及文学的创作,而且牵及社会文化的很多方面,《文学革命论》在批评“文学之文,概不足观”之外,还攻击到碑铭墓志、寻常启事、匾额题言和俗套春联等应用文,斥之为“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正因为文言、白话之争事实上不可能只限于文学创作方面,所以反对文言文在当时所引起的社会震动较之一般地提倡新文学所引起的震动为大。自那时开始不断出现的“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很多来自并非关心文学之人。不仅是遗老遗少,也不仅是道学迂儒,还有留洋教授,都视胡、陈为洪水猛兽。胡适、陈独秀遭到大量攻击并且由此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同这种情况也很有关系。但文学界的人攻击文学革命也是从攻击白话文开始的,或者是以白话文为主要对象的。为大家所熟悉的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当废》和《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就是极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发表于《文艺丛报》,这个刊物出版于1919年初,在“五四”运动前几个月,创办人陈拾遗是提倡保存“国粹”的守旧派,这个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不仅反对白话文,而且也反对所谓“与国粹为大敌”的“欧糟”“美粕”。也是在这一年3月间,北京出现“国故社”及其主办的《国故》杂志,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提出要重振“颓纲”。“国故社”以挽救“国学”来和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势必要遭到提倡和拥护文学革命者的回击。当时也在北京成立的“新潮社”及其主办的《新潮》杂志登载了毛子水(“新潮社”成员)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批评“近来研究国故的人”,既不知“国故”的性质,也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于是双方往来辩驳。同时,在南京高等师范执教的胡先骕发表了《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反对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责备提倡新文学者是“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这篇文章实际上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和北京“国故社”的研究和昌明国故的主张遥相呼应的作用,于是又引出新潮社另一成员罗家伦的驳斥之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胡先骕后来是“学衡派”中人。“学衡派”以1921年创办的《学衡》杂志而得名,《学衡》和1925年在北京复刊的《甲寅》杂志一样,它们的矛头都是直指“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它们的种种言论也遭到了文学革命先行者们的驳斥。以上这些事实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常被记载,被概括地称作“对复古派的斗争”或是“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
正当“国故社”和“新潮社”就研究“国故”问题相互驳难的时候,提倡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胡适在《新潮》上发表了《论国故学》,这篇文章发表时附在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之后,原是胡适致毛子水的信。毛子水文中怀疑当时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胡适在文中却说,“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并说要用“自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他还说:“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云云,说明胡适当时把研究国故限于纯学术范围内,有别于当时整理国故中出现的挽救“颓纲”的迂腐见解。1922年,胡适脱离“新青年”阵营后另办《努力》周报,后又附出《读书杂志》,他在《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中说,创办这个新杂志是沿用清代著名朴学家王念孙父子《读书杂志》的名称,《缘起》的末尾,他希望“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由于他在此之前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不止一次攻击宣传社会革命理论是“空谈好听的主义”“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人们自然地就把它们联系起来。而他在创办的《读书杂志》上又提倡研究国故,加之他后来又把从1920年开始的章回小说考证工作所体现的“科学方法”说成是可以“教我的少年朋友学一点防身的本领”,还说,“我这里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就是说,他把自己提倡的“整理国故”的方法之一的考据学,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整理国故”当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段,赋予“整理国故”以政治、思想斗争的色彩,实际上违背了他的纯学术宣传。
胡适在20年代提倡整理国故,曾招致卫护“五四”文学革命业绩的人的抨击,视之为复古逆流,或者助长了复古气焰,因而有害或者不利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提倡“整理国故”,胡适在《发刊宣言》中疾呼“古学要沦亡了”,感叹“无限的悲观”后,各地纷纷开办国学馆,一时成风。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中说,有的国学研究家“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大锣大鼓四处去宣传”。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也说:“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势力仍很猖獗, 1924年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孙宝琦下令教育部核办取缔“新学说”,还发生查禁陈独秀文集和禁演易卜生的《娜拉》等事件,看来并非偶然。在1924年发表《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恢复科举吧》和《康圣人修孔庙》等抨击复古潮流文章的沈雁冰于同年连续撰写了针对“整理国故”之风的《文学界的反动运动》和《进一步退两步》两篇文章。前者主要锋芒针对“学衡派”及其他复古派,认为他们掀起一股“凶恶的反动潮流”,文章说:“我们要站在凶恶的反动潮流前面尽力抵抗。”后者主要批评新文学营垒中提倡研究国故的人,他说,虽然新文学运动“不是单纯的白话运动”,但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一定要是白话运动”,他认为当时“白话的势力尚未十分巩固”,“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和“建立不拔的根基”,由此他以为“做白话文的朋友们”的整理国故是一种“退让”,“遂引起了复古运动”。沈雁冰是赞成新文学运动中应有估价、整理旧文学任务的主张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也申明了这种态度,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反对“做白话文的朋友们”在此时此际提倡和研究国故。他批评的“朋友们”中当有胡适,但又不仅是胡适。沈雁冰的这种看法和当时鲁迅、郭沫若等人的看法大致相同,是有代表性的。现在的文学史著作大抵把20年代胡适提倡(其实郑振铎也提倡)整理国故看做是有害或者不利于当时新文学发展的举动,也就把它概括在“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或“与右翼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内容中加以叙述和评论。但这种看法或许并不全面,或许值得怀疑,或许会有争论。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发生的围绕着提倡“国故学”和“整理国故”的争论有着复杂性,当这种提倡是为了反对新文学的时候,当这种提倡表现为以“读书”以“考据”来对抗社会革命宣传的时候,它们的历史命运是可悲的,但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审视,从继承文学传统这个命题来考察,却又需要作另一方面的观照。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人们谈论的所谓国故,泛指我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并不专指我国古代文学,但包含着古代文学,有时甚至成为文学传统的同义语。因此,当时围绕着“国故学”的争论,也就必然涉及文学革命和文学传统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较早用比较明确的语言来表达和争论的是上文提到过的胡先骕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和罗家伦的《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据罗家伦说,胡文是受到“烧料国粹家”们热烈欢迎并拍手称快之作。从反对以白话文取代文言以及嘲讽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这点上说,胡先骕之文确是表达了守旧的国粹家的心声,但胡文中关于文学的革故鼎新关系的论述却超过了那班只以保存“国粹”为能事的“国粹家”,从而表现出他的高远识见,文中说:
盖人之异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历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如厮始可望其成功。
罗家伦文中则说:
“用已有的材料方可从事创造”一句话我们是承认的。我们同胡君主张不同的地方只是胡君所注重的仅是这句上半句“已有的材料”,而攻击我们“创造”;我们则注重下半句“从事创造”,当然以已有的材料为用……有人以为我们创造新文学不用文言,就是不用已有的材料。这话真不值一驳。
从罗家伦与胡先骕的论战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彼此都认为从事创造要利用“已有之材料”,实际就涉及文学的革新需要继承文学的传统这一命题。胡先骕文章中的可取之处也表现在这里。胡文又曾嘲讽文学革命运动的“盲从者”为文学革命发难者的“外国毕业及哲学博士等头衔所震”,他于是自诩“亦曾留学外国,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文学之源流”,但他在说“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和说“故居今日而言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之时,却没有强调创造新文学也要借鉴外国文学。他只是似是而非地说到“故俄国之文学,其始脱胎于英、法,而今远驾其上,即善用其古产,而能发扬张大之耳”。罗家伦却擒住胡先骕的这句话,生发开去,论说文学革命正是中西文学接触和撞击的结果:
胡君以“俄国之文学出于英、法而今远驾其上”,诚然诚然……人类文化是大公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原是不足为耻的事。从前法国文学影响英国,后来英国文学影响法国;从前英国文学影响德国,后来德国文学影响英国。一看欧美文学进化史,则展转影响,不可胜数。而且进步也都是由互相接触得来的。中国这次文学革命,乃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文学进化史上不能免的阶段,请大家不要少见多怪罢!
从“纯文化”的观照角度来看,这样一些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注意,罗、胡论战是在1919年,这年胡适发表《论国故学》,次年胡适开始写作一系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文章,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再过一年,即1921年,在北京成立的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简章》中提出了“整理中国的旧文学”的任务,几乎和《国学季刊》提倡整理国故同时,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增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栏,就研究与整理中国传统文学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展开讨论,参与讨论的不少文章大抵阐说了整理国故的必要性。当时的主编郑振铎发表了《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郑振铎所说的“国故新研究”,是为了区别于国粹派的国故研究,所以他认为这种新研究有助于打破国粹派的旧观念,他说:“正如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旧教中人藉托《圣经》以愚蒙世人,路德便抉《圣经》的真义,以攻击他们。路德之成功,即在于此。我们现在的整理国故,也是这种意思。”这种论述倒是带上了西方文艺复兴的色彩。他又说:“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郑振铎这篇文章发表于1923年1月,同年5月,他在《文学旬刊》第七十三期的《给读者》中说:“本刊对于盲目的复古运动与投机的‘反文学’运动,虽曾叠次加以热烈的攻击,却没有发生什么效果,到现在,盲目的复古派还自若的在进行着”,“我们仍旧继续的对一切愚顽的敌人,下热烈的攻击”。由此看来,郑振铎提倡的“国故的新研究”既有着与国粹派、“盲目的复古派”划清界限的目的,同时也确认国故之研究是新文学建设中应有之举。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23年后开始掀起的关于整理国故的论战中,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已经不完全采取1917年之际像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提倡文学革命时所使用的“绝对之是”的“过悍”态度,当时成仿吾所写的《国学运动的吾见》中所表现的反对态度虽十分激烈,但他同时也说:“国学,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然而研究的人一要有十分的素养,二要取适当的方法。反观现在许多热心国学运动的人,却不仅没有十分的素养,也还未取适当的方法。”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中除了同意成仿吾说的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精神外,还说:“但如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所以凡事只能各行其是,不必强人于同。只能先求人有自我的觉悟,并求有益于社会,则百川殊途而归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以见出大同。不必兢兢焉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异”。这时文学研究会的另一重要人物沈雁冰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说,“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在这点上他和郑振铎所持的新文学运动中“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的观点相同,不同的是他认为不是当务之急。与沈雁冰所持观点相近似的成仿吾也说“然而现在便高谈研究”,“未免为时过早”。
但“为时过早”说并没能阻挡住新文学营垒内发生的研究国故、研究传统文学的主张和实践,到了1927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刊有60多篇研究论文,内容从先秦汉魏文学到明清小说,其间包括唐诗、宋词和元曲等的研究文章,以至后来被人认为这个专号实际是一部学术论文集。郑振铎为这个专号撰写的《卷头语》中以两个武士各自只看到盾的一面而发生争论的故事,比喻传统文学成分的复杂,因而需要研究和鉴别,他说:
近来为中国文学而争论的先生们,不有类于这两个武士么?有的说,中国文学是如何的美好高超,哪一国的作品有我们的这么精莹。有的说,我们的都是有毒的东西,会阻碍进步的,哪里比得上人家,最好是一束束的把他们倒在垃圾堆中。他们真的还没有见到这面盾的真相。这面盾原是比之武士们所见的金银盾,构成的成份更复杂,而且更具有迷人的色彩与图案的。这是我们区区愿望,要在这里就力之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这面盾的真相显示给大家。
是否可以这么来认识,20年代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和郑振铎提倡“国故之新研究”,以及他们的种种实践,就文化“本位”的意义上说,他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也是适应了一种需要,在文学革命初期对传统文学做出异常激烈的批判和攻击之后,需要对传统文学认真而从容地进行分析、思考和反省,以助于新文学的创造和新文化的建设。或许可以说,从这一角度考察,也还是历史的审视,是历史现象的另一种观照。
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也是有变化的,在整理国故问题上也是如此。1919年他在说明整理国故的必要性时只强调要“懂得”它,后来又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不过如此’。”(《整理国故与打鬼》)他在这方面最有价值的说法倒是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把整理国故和新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终于表示了与只强调借助西方文化的主张的不同。
在新文学的建设中,既要借助外国文化,又要继承传统,即一手伸向外国,一手伸向传统,这种“两手信号”在1921年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表现得最为鲜明,它在“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的同时,逐渐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在出现“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和“现代世界文学研究”等专号外,又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并且号召人们从事研究清理传统文学这个“艰难”而“伟大”的工作。1923年后任《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在另一篇题为《研究中国文学之新途径》中,又以一种宏大的气魄,要求扬弃古人文学研究中的种种弊端,提倡对传统文学的开创性研究,“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一个时代之研究的著作”,“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每一种文体之研究的著作”,“我们还应该有不少部综叙全部中国文学之发展的文学史,或详的,或略的,或为学者的研究结果,具有不少独特之创见的,或为极详明的集合前人各种特殊研究之结果,而以大力量融合为一的、或为极精细的搜辑不少粗制的材料而成为浩大的工程的,或疏疏朗朗的以流丽可爱的技术而写作出来的”,他还说:“我们还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辞书、类书、百科全书,还应该有不少关于它的参考书目、研究指导,等等。”郑振铎这里表现的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气魄,他在文章的“结论与希望”部分又把研究传统文学的工作置放在中西文学“接触”会产生一个“大时代”这种战略宏图中来予以认识:
中国的文学曾因与印度的文学的接触而产生了一个大时代。现在却是与西方文学相接触了,这个伟大的接触,一定会产生更伟大的时代出现的。文艺复兴的预示,已隐隐的现于桃红色天空的云端了。在这个将来的大时代,将来的文艺复兴期中,每个努力于文艺者,都会有他的一份贡献……而研究中国文学者,也自应努力去研究,去建造许多古未所有的专门的功绩……大时代不是一日一夜所能造成,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造成,我们有我们的一分工作,我们不能放弃了我们应做的工作!
是的,“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先行者们并没有“放弃”这项工作,他们还做出过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他们能够作出的贡献,自发难文学革命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文学阵营中人在传统文学的研究上做出巨大和重要成绩的有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胡适的章回小说研究,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还有沈雁冰的神话研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等。他们的著作至今还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那时的成就又是有限的,郑振铎所倡导的种种著作,远没有完成或很好地完成。胡适在50年代曾经说过他不赞成“五四”文学革命之说,他说那是一个文艺“更生”和“再生”运动,但他又说在这个“再生”运动中和运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有“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现象。他所说的“创造”指文艺作品。但借用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后一段时间内缺少能与这场革命相称的、对传统文学再估价的巨著力作,也还是合适的。
为什么说“创造无力”呢?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看,却又同“五四”文学革命激烈攻击传统文学的特点有关,简单化地论说这种特点为优为劣固然是不恰当的,但这种特点确实带来了轻视文学传统的偏向,这种偏向的影响是深远的。1950年周扬在《怎样批判旧文学》中说这种偏向也被3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艺运动继承下来,他说:左翼文学运动中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但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当时我们是坚决摒弃一切旧东西,反对旧戏,就连《水浒传》也不主张叫人看的”。周扬在这篇讲演稿中还把在对旧文化问题上发生过的偏向视作关于共产党“不要文化”的谣言的一种“客观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倡和强调重视文艺遗产的研究和整理的重要原因。
同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审视,“五四”文学革命后一段时间内缺少对传统文学再估价的巨著力作,还同当时人们没有能够把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学“接触”的宏观视点真正融化于具体的实践,或者在实践中过于匆促有关。作为这种“接触”的一种具体表现(远不是全部),当时人们自觉地认识到重新估价和研究传统文学也需要借用西方文化作武器,在新文学阵营中发生的整理国故的争论中,无论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还是郑振铎倡导的“国故之新研究”,都主张要用科学的方法,批评者或者认为国故研究非当务之急的人也主张应有科学的方法。所不同的是批评者往往不具体描绘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提倡者倒是十分明确地亮出他们的具体主张。胡适1920年披露的《水浒传考证》中说他要借这篇文章贡献给大家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后来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又宣扬“历史的方法”,他说:
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它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它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它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它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它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它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份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是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它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它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在一个时期内,对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和“历史的方法”的批评常常偏于论说它的非科学性。这种批评招来了异议。这种批评和异议目前依然存在,估计今后还会出现。我们不妨暂时撇开这种争议,来考察胡适的研究成果和他提倡的方法之间有无误差和迷失,或许可以窥知“创造无力”的一种端倪。
胡适是在《水浒传考证》中提出“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但该文所提供的例子却是浅近浮泛的。比如他从周密《癸辛杂识》所载的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得出“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和“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看法,进而论断“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还论断说元朝之被推翻“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读了龚圣与、周密的议论,可以知道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也许是汉族光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哩!”胡适宣传的“历史的方法”是重视“历史背景”和“历史价值”的,但他这番对元代水浒故事“发达”的“背景”和“价值”的解释显然是粗浅的,即使它是正确的,和他所标榜的新的自觉的科学方法也不相称。事实上,它与明人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中的“发愤”之作的见解的立论方法和角度几乎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李贽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代,《水浒传》作者有民族意识,所以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此外,胡适在应用“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时,说“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的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也就是所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这种说明又是似是而非的浮泛说法,因为它排除了其他的或者是“偶然”的因素。即使《水浒传》并非作于元代之说是可靠的,他的这种说明却流于简单化。而且,这实际上还是古人早已应用的方法,如古人辩证“苏李诗”非“西汉文”,也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因此,这又与他宣扬的新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不相称。总之,即使人们尊重胡适宣扬的“历史方法”,即使人们承认它是一种科学方法,也会发现他在应用时实在力不从心。这也是人们往往重视胡适的考证成绩而不重视他通过考证企图宣扬的新方法的重要原因。胡适的研究成果和他提倡的方法之间的误差乃至迷失,就使他的考证文章在整体上呈现出“旧”的而非“新”的面貌。他自己爱说的“考据癖”其实来自清代的汉学即朴学,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他尊乾嘉学者是“第一流聪明才智”的人物,不过他有时为了表示区别,就爱说他做的是“半新不旧的考据”。他在《水浒传考证》中曾说:“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评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打开一条新道路。”胡适当然知道他所崇拜的清代朴学大师们即使还活着也是不可能对《水浒传》作考评和训诂的,因为他们虽然把我国传统的考据学、训诂学和校勘学推进到了一个高峰,但他们的文学观念是落后的,他们一般不重视乃至排斥小说、戏曲这类“俗文学”。扬弃清代朴学家陈腐的文学偏见,继承他们的治学方法,用来研究“俗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一变化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王国维是重视“新思想”“新学语”的输入并推动中国文学和学术事业发展的有宏观审视眼光的学者,他还曾较早地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但他后来落伍了。王国维和另一位近代著名人物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以后都在北京任教,如果说梁启超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曾经改变文风,也兼用“国语文”来写作,从这一角度表示他对文化运动潮流的认同,那么,王国维却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王国维和梁启超不是新文学营垒中人,但他们在“五四”以后都还是被人推崇的“国学大师”。作为新文学营垒中的著名人物的胡适在提倡和研究国故的实践中与他们有不少共同点,在对待清代朴学的态度上更趋一致。1928年第六十四期《学衡》杂志登载的谷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中说胡适“尽受”王国维的影响,甚至说:“故凡先生有言,胡称臣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自先生而衍之胡氏。”这在当时也是一种论战语言,实又是攻击和贬抑胡适,胡适从来没有说过他深受王国维影响。但即使在事实上受到影响,也不是胡适的缺点,却是他治学的一个长处。
胡适和他同道的考据文章,当时也遭到非议和攻击,成仿吾就说“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而那是“非科学的旧法”,“所以他们纵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又说:“若这样的考证便是国学运动的全部,我们倒也不须多说了。”考据当然不是国学研究的“全部”,但考据也并非“无益”,而且还是研究中必要的工作。所以当时郭沫若说“仿吾亦失之偏激”。
郑振铎倒是赞许胡适的考据文章而且是在文学研究要走新路的前提下作出赞许的,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郑振铎说:“我们要走新路,先要经过连接着的两段大路;一段路叫做‘归纳的考察’,一段路叫做‘进化的观念’。”他在阐述“归纳的考察”时又归结为“无证不信”和“拿证据来”。他认为索隐派“红学”走错了路,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用的“新的方法”,是“归纳的研究方法”。郑振铎把他所说的“进化的观念”归结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实际也是同意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但郑振铎在30年代初转为接受弗里契的文学批评观念,又表现出和胡适的不同。
郑振铎和胡适都是新文学营垒中重视研究文学遗产并在实践上有大量成果的学者,他们提倡走“新路”,但无论从他们的文学史著作还是从考据文章来看,他们在实现自己提倡的“新的方法”上都显得匆忙,他们的实践与他们的提倡也都有差距。
鲁迅对20年代和30年代初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的态度是谦逊、宽容而又严格、认真的,也就是实事求是的,他在1933年12月20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向曹靖华推荐王国维的《宋元代戏曲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等著作的同时,也推荐了《中国小说史略》,但他又对他所推荐的这些著作表示不能满意。在这之前,他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不见得好”。鲁迅在1929年至1931年间翻译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艺术理论的时候,常同冯雪峰谈起研究文学史的方法问题。他在1930年还在理论上明确了复古与继承的根本不同点,论说了新文化大抵发达于旧文化的反抗中,同时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和承传。这时他打算编写一部文学史,只是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在用“新的方法”研究传统文学的实践中的匆促,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各自信仰、提倡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深入“融化”。当然,他们是意识到要深入“融化”的,他们不赞成仅以转述、套用为满足。郑振铎于1929年撰写的长篇论文《梁任公先生》中涉及了这个问题,是在称赞梁启超的成就时表达出来的:
第三方面,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这样的见解与方法并不是梁氏所自创的,其得力处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却能运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叙述力,大气包举的融化力,很有根底的旧学基础,于是他的文章便与一班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之人大异。
郑振铎的这种评价是否完全符合梁启超的实际,姑且不论。但他提出了一个古代文化研究者能够取得大成就的重要的主观条件:即使运用的理论、方法不是“自创”,但必须以“大气包举的融化力”来解悟,做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还要有“很有根底的旧学基础”。其实,不是“自创”而能“融化”,实际就已成为研究家自己的思想血肉,而在成为自己的思想血肉的过程中,通过突入、悟解和贯通,又会有所变化、张大和发展。这种张大和发展又不只是局限于对某种或多种理论、方法静止的诵习,而需要在应用、实践中反复完成。
郑振铎是不满意“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的,当时一些国粹派也用过类似这样的语言,但他们是出于攻击新学说的目的,和郑振铎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按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大凡介绍、应用新思想、新学说,总有一个由不那么融会贯通到逐渐融会贯通以至运用自如的过程,一直到达在不同的程度上张大和发展的地步。从全局来说,这个过程是不以人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年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点来阐说《红楼梦》,撰写了《红楼梦评论》,学人论定它在“红学”历史上的功绩的同时,大抵也都认为它有生硬也就是不那么融会贯通的弊病。承认应用新观念、新方法并达到融会贯通要有一个过程,而且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反复完成,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不仅仅以转述新学说为满足,不以停留于一般套用为满足,同样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郑振铎所说的“旧学根柢”,也是古代文化研究者应当具备的重要条件,在一般情况下,科学而沉实的思想力和深厚而广博的旧文化根柢这两者在研究者身上常存在不同侧面的倾斜,过去和现在都存在这种倾斜现象,将来或许也会出现。但从全局上说,却又需要不断地提倡扭转并切实解决这种倾斜。是否还应当这么看,学术研究中最可忧虑的还不在于有这种倾斜,而是在于一种浅薄的“平衡”,即既无理论思力,又无常识根柢。郑振铎所批评的“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的现象中,或许也有这种浅薄的现象。
“五四”时代的学者大都具有旧学根柢,这是他们从事古文化研究的长处。至于他们在用他们选择的“新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化时表现出匆忙,由此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思想融化力的不足,还有一种原因。“五四”文学革命前后,外国各种思潮被大量介绍到中国,那时纷至沓来的状况使人眼花缭乱,在纷纭万象的思想氛围中,每个人都要进行抉择,在抉择过程中,又有变化和转移,而且是那样的急速。这样的历史现象我们并不陌生:人们刚择定进化论不久,又改换选择社会学,后来又发现庸俗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的不同,于是又改换选择。正因为学者对某种理论、学说的融化力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需要反复完成,因此,抉择变化的急速,或许也是影响融化力的一个原因。
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论文的结尾,引用了梁启超的一首词,词中写道:“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们未能完成与那场伟大革命相称的对传统文学再估价的巨著力作,也可说他们壮志未酬,但他们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已经作出了他们所能作的贡献,他们还做了自我反省,表现出了学者应有的风度。因此,这里回顾历史,并借用胡适的“提倡有心,创造无力”一语来发表若干感想,决无苛责前人之心,只是出于吸取历史经验之意。
(原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