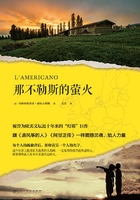在哑叔与傻子孙福之间我需要做出艰难选择,一步将决定今后的万步。回想往昔,心里时时揣着恐惧,走在陌生的大路上。那一圈圈被风吹起的黄土,卷起我历经的那些似梦非梦的日子,扑朔在我的眼前。我知道我依旧要走下去,不论我来自何方,我都将是立在天地间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一个将带着傻丈夫与孩子继续生存的人……
今天的树上,冷冷清清。光光的树干上,偶尔传来树叶的沙沙声,是在泥土里留有生命的最后几片,挣扎着爆发出脆弱的生命之音。
远远地看过去,天的那边空气很湿,空气没有颜色,呼吸后令心灵感知着水一样的滋味。在稀薄的空气里,直立着一间破败的瓦房,每次变换视角去看,破旧的瓦片之物都呈现着不同的形状。房子的根部,应该讲是靠近别家院墙的那边,已经长满了青苔,很脏也很乱。一点儿都不像王安石诗中所写的青苔那样美。走过去的人都是躲着它,生怕沾到了一点儿在脚上,惹来霉运。其实,路人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从懂事以来也学着他们,我想我的答案是这样吧。
空气湿得透不过气来,一堆荒草一堆荒草地堆着,是冬季用来当柴火烧的。我不敢点火,也从不敢让火种在这周围出现。当然我不是管这类事物的,只是我胆小,就怕干柴遇烈火熊熊燃烧。
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在小的时候,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能走出村子,到村口看看,对于我来说已是困鸟出笼了。慢慢的我长大了,大人可以放我走得远一些了,直至有一天,我陪二伯去了一趟城里,那宽敞的马路,形状各异的跑车,抹胭涂粉的俊脸,夜半耀眼的霓虹,小摊上喷香的点心,还有解囊予乞人的那份慷慨……我的思想境界就改变了。我知道,这个小村庄是多么地小,多么地小……外面有好多的黑白电视里才可以看到的文化,我愣是站在讲解人的身旁那么久都没有听懂。是啊,没有基础,学什么又会快呢。回家到村子,我每日每夜最盼望的就是能够走出村子,过一过城里人的生活。可我知道,我是不能的。我属于这片黄土地。
我已经习惯了穿着糟粕衣服的乡里人串门到我家时对我异样的眼光,我已经习惯了在他们口中一会儿城里人一会儿乡下人的命的断言。我不知道人的耳朵是用来听什么的,现在长大了我是拣着听的。所以,现在我在他们眼里是那么的不驯服。外人的孩子就是外人的孩子。
早晨起得很早,这是我很小时候的习惯。
在每早还没有出太阳的时间里,我总会看到柯爷爷艰难地挑着两个黑黑的大桶往东边的山上去,大桶里装的是粪。村子里每一家都有茅坑,呈方形或是长形或是不规则形状的。小解或是大解都是到那里。这些人排下来的粪便很有用,“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可以用来浇灌田地。
我总是很执著地跟在柯爷爷身后,柯爷爷已经习惯了。在挑担上,有他的烟袋,我很喜欢给柯爷爷装烟袋的。天气很冷,柯爷爷的双手想抄在兜里,可是挑担总是往他那已不平坦的肩头下滑着,他的两只瘦弱的大手不得不前后抓住挑桶的麻绳。我在后面跟得很紧。柯爷爷虽然年纪很大,腿脚还算灵活,我是走不过他的。
大粪的味儿是很难闻的,我干呕得累了,扶着一棵树。我明知道自己嫌弃这个味儿,可每早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是促使着我跟在柯爷爷身后。
还未忙多少农活,已是晌午了。家里人不会喊我回去吃饭的,因为我在哪里他们是不知道的,也不管我。
柯爷爷的黑褂大布袋里放着饼子,拿出来时已经像石头一样硬,像冰块一样冷,他喘着气使劲掰着,掉一点儿渣都赶忙寻到往嘴里填。他的口中有丰富的唾液,好像任何硬食物都会被他口中丰富的唾液融化。我的心很软,我最受不了这种场景。我特意找点儿事,比如在原地上装作跳方以驱逐眼眶里泪水的四溢横流。可是柯爷爷还是喊我了。他递给我一半。每次都是这样,我哪里能要他的东西吃呢。他无儿无女,我也是听家里人说的,好像是个老光棍,很穷。
我没有接,每次我都没有接。每次他都是默默地。
天气很冷,我打了一个喷嚏,冻得直发抖。柯爷爷马上放下手中的饼子,用瘦弱的大手搓着我的手给我暖和。听说年轻时他的力气很大,可如今很是微弱,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成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这么大的年纪了膝下也没有儿女养老。我终于止不住泪水,哭道:“柯爷爷,你好可怜!”
柯爷爷的手猛地颤了一下,或许是他没有想到这样一句话会从我的口中说出来;也或许在他年轻顾影自怜时他也曾这样感觉到;也或许是这样的话从来都是发自他自己的内心;或许是他多么希望周边的人会认同他境遇的可怜并且得到政府的帮助;或许他也明白得到人同情的话语并不会使自己的境况得到什么改变,但人活着是需要交流的,尤其是情感交流。
“我不可怜,你倒是小手冻得冰凉。”柯爷爷笑着说。
“爷爷。”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让我抱紧这位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的老人。
柯爷爷拍拍我单薄的后背:“好,好。”
冬季的天黑得很快。我跟在爷爷后面匆匆地往回走。在乡下的路上,我生怕从树丛里钻出个蛇怪之类的。每次柯爷爷都会看出我幼小的心事儿,他用苍老但温柔至极的声音告诉我:“不怕,爷爷手里有挑担,不会让虫子出来的。”
这时的我会一声一声地喊着并扯着柯爷爷的衣角:“爷爷!爷爷!”这是我一个九岁的小姑娘真情的童声。
我有一个弟弟,他与我并不亲。弟弟比我小四岁。我很少接触到他。妈妈也不让。妈妈不太搭理我,同样也不分配我做什么活儿。乡下每户的院子都很大。可以游戏,我自己游戏。怎么跳怎么欢呼,都没有人制止。我很快乐的。村南住的妈妈的表姐,她有个疯女儿,天天也是这样独自地一会儿跳一会儿叫。小孩子有时是忧郁的,看着人们都指指点点表姐是疯子时,我曾一度怀疑我与表姐一样也是疯子。不过表姐是经过医院开了证明的疯子。我却不是,我只是一个天真淘气喜欢独处的小姑娘。
妈妈带着弟弟到南村的表姨家去了,她没有带我去,我也不去。空空的房子,我没有爸爸。不对,不应该说我没有爸爸,应该说我本来就没有爸爸与妈妈。现在的妈妈是弟弟的妈妈。她不是很管我,也不约束我。她是话很少的一个女人,年轻时,应该很文静。她的皮肤白皙。我随便在几间屋子里逛着,随嘴哼几句歌,仿佛自娱其乐的心情永远没有止境。妈妈的锅上煮着肉,弟弟要了好几天了,妈妈才舍得出去切了一块猪肉,白肉见多。我们的日子并不好,实际上我们整个村子都不是富裕的,靠那么点儿庄稼糊口过日子。与前些日子去的城里截然不同,乡下是阴暗,城里是明亮。肉的香味已经从干瘪的锅盖的缝隙中飘出来了,好香啊!我像个身经百战的小贼一样围到锅台旁边,锅台里面的柴火还在熊熊燃烧着,是妈妈领弟弟出去时添满的。因为我不会加火,妈妈不用我干活。我从贴着锅台的竹篓里取了一双筷子。打开锅盖,热气击中了我的小手,我尖叫了一声松开了手,锅盖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正在这时,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平时她们是要去很久的,起码要两个小时吧,这次一个小时都不到。天啊,我多么羞愧啊,妈妈会指责我的,我低着头。锅上的热气还在冒,肉的香味还在飘着,可我现在一点儿都不想吃肉了。妈妈踏进中屋,锅盖很安静地扣在地上。
“伤到没有?”她的声音很轻很轻。
“没,没。”我拘束地挤出两个字,我与妈妈平时很少交流。在我记忆中她心里想什么没有人知道。来往的邻居及亲戚说什么她都言是,也从不参与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妈妈给我的印象,但之后就是这个女人把我又扔到了另一个地方。
妈妈没有再理会我,我自己打了一盆冷水,将手浸在里面能舒服些。我已经习惯了自己关心自己。其实,我伤得也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不是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或许我现在正在尝着早想填到嘴里的肥肉了,根本不会理会轻微烫伤的手。我抬起头看看妈妈的脸,妈妈哭了,她的睫毛上艰难地扛着泪珠,她不想让自己哭出来。
弟弟咕嘟了一句:“姨家的姐姐死了。”
死,在一个小孩心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永远都回不来的地方。那时的我对死根本就无意识,不知当时的弟弟是如何想的。
妈妈的那滴眼泪终于落下了,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去洗洗手,一会儿吃肉。”
我赶紧搬小凳,家里的饭桌很小,像是三个人要挤在一起取暖似的。
肉很香,妈妈一口都没有吃。
弟弟蘸着肉汤吃了好多干粮,大块大块的白肉往自己肉嘟嘟的小嘴里塞。弟弟的脸蛋很红,模样也很漂亮,像妈妈。
吃肉的第二天,是冬季里最冷的一天,也是表姐下葬的一天。
妈妈自己去了。
回来时,妈妈痛苦地倒在床上,生病了。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如此伤心。
这天早晨,柯爷爷没有挑着粪担出来。我离开家门很远了,户外很冷,我却不想回去。在妈妈痛苦的时候,我并没有尽到做姐姐的责任看护弟弟。那个家,虽然我从小就住在那里,但没有感情确是事实,并不是家里的人待我不好,准确地讲是我待他们不很平和。我独自去了柯爷爷的地,冬天所有的庄稼都干干地伫在那儿,黑黑的土地上散发着冷气,“咝咝咝”地像要吸住经过这里行人的脚。想到这儿,我飞快地往回跑。那片地离家有一段距离,我低着头看着脚下的路拼命地往前冲,像是脚下的每一块黑土都可能吸住我的脚。
“童童,慢点儿跑,慢点儿跑。”一个苍老的声音传到我耳畔。我听出来这声音是柯爷爷的。我抬起头一看,果然是柯爷爷挑着粪担,他又出来劳作了。还是穿着那件带很大口袋的褂子,那双干瘦的大手依然冻得发紫。裤管一长一短,还拖着地。柯爷爷的身材不高。
“爷爷!”我很高兴地扑过去,抓住他的挑担绳。
爷爷不住地点头:“这么冷,出来瞎跑什么?”
“我找爷爷!”我的声音是激扬的。一直抓着挑担绳,生怕柯爷爷突然不见了。
我跟在爷爷后面,今天爷爷的腿脚显得更慢了,走了不一会儿,突然他一蹲,就再也没有起来,粪撒了一地也溅在他干皱的脸上,口袋里的饼子滚动着很美的圈最后还是在粪上静止了,今天的饼子上有葱花。我呼喊着爷爷,爷爷的口里吐出白沫,眼睛睁了几下没有睁开,嘴巴始终没有张开说一句话。歪着脖子,蜷着身体,四肢弯曲着,紧紧地贴着黑土地去了。
村长找人草草地将柯爷爷埋掉了,那天妈妈不让我去。之后,我去了,看到的只是高高的坟头,我也不知道里面躺的是不是柯爷爷。
柯爷爷的离去,使我仅有的快乐也失去了。
冬天的夜黑得很快,天上的星星很少。老人说过,冬天的星星本来就很少。
柯爷爷去了,我每天都起来得很晚。鸡在院子里都叫傻了。我听很多从我身边路过的人说,我不是妈妈的孩子,妈妈的孩子只有弟弟。那我是谁,经常围着锅沿转着思考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很想念柯爷爷,他是我的朋友。而现在,空间对于我很自由,亲情对于我很压抑,像被夹住了两肋,呼吸很困难。我知道我要生存,我还要有信仰,那是可以使我有精神力量的东西,人生下来确实是为了活,就像活着那样活着,但不能缺了信仰。看见妈妈教弟弟写字,那些形状,我不会,可我会说话,说话也可以生活,不是非要会写字。但终于,我还是求妈妈教我写字,妈妈教我写字认字,我感觉自己有文化了……我可以像天空的小鸟一样起飞在乌云里,更可以起飞在晴空里。我漫山遍野地跑着,饿了就回家吃饭,渴了就回家喝水,妈妈真的不管我,越长大我越感觉自己和空气是一体的,成天只有空气是我的朋友。
在十七岁的时候,我从村后面的山坡上摔下来了,从此跛脚。弟弟给我捡来一根很粗的拐棍。像是藤子的,我很感激他。可之后他与妈妈就离我更远了。虽然,就在这块贫瘠的地界活动,总也有种四海为家的感觉,心一直被吊着,忽忽悠悠地飘着,到底要去往哪里,只有太阳出来时,才会想到是想要到达温暖的地方。妈妈对我说话的声音还是柔柔的。
妈妈让我嫁人,我躲在门后不出来,使劲翻弄着自己的冷炕,像是石灰下面可以挖出逃生的地图还有行路的盘缠。吃过那次午饭,我就迷迷糊糊地眼前像晃着谁在数钱的样子,想喊的声音一直在胸腔里,是走过去的脚步又狠狠地在小腹踏上一回的感觉。
好似醒也好似睡,像是睁开眼又像在闭着。听到很多人在说话、在笑,自己也在其中,就是张不开嘴说不出话。
我醒了,躺在另一张农村睡的那样的炕上。地上的摆设很是简陋,墙上挂了一张破碎的年画,还拖着很长的灰尘。我的拐棍就在年画下面。我努力地起来,头晕得很,我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这是哪里,一会儿跑进来一个傻乎乎的男孩子冲着我笑:“媳妇醒了,媳妇醒了。”我的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这个傻子叫孙福,是我的男人。
第二天,我又一次醒来,被窝里多了一个塑料瓶子,有很重的塑料味。一位年岁很大的老人坐在炕上。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难过地闭上眼睛,等待着。老人穿着粗旧的黑色布衣,这里很贫穷,从穿戴摆设就能看出来。
“你是我家的人了。”说完,老人很高兴地过来拉我的手。我厌烦地转过头,头很晕,还伴着剧烈的痛。我在被子里抽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