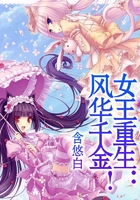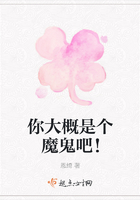老田属于那种对别人宽厚、对自己严格的人。他在主政部门时,没有见他激烈过,每每部门的会议,都在一个稍大些的办公室里开,如同农村田间地头的村民会,随意地坐着,谈点实事,无高谈阔论,只有信息情况的交流,简洁的工作安排,如此而已,要做的和要办的就解决了。而作为主角的他,不激烈,不焦急,不偏执,但也不马虎。属下的有条不紊,工作也没有出现过差池,也许那种纯正的文学和文化气氛,让各位编辑同仁、同事们各司其职,演绎得得心应手了。老田领导作风朴实,不指手画脚,不颐指气使,哪怕是对我这样的小字辈和新来的,说话也总是以商量的口气,不说官职(好像他“文革”前已是行政十三级,属高干之列),就是在年龄上,他也可以说是部门里有些人的父辈级,可他还是以细声和气谈工作,商量的口吻说版面,即使议论单位的大事小事,即使批评文化界的一些不良之风,或者激愤于某些孜孜于利禄权势的人、蝇营狗苟的事,他也不像我等之辈,恨不得与之决绝;在他也多是一种认真的分析,还为那些本来就是尸位素餐的人,那些混迹于文坛而捞取资本的人,作些“假若”、“如果”式的推想。比如,说他们也不容易,替他们的生存现状着想,宅心仁厚,为不多见。在“文革”中,老田被造反派打倒,也有个别同事落井下石,颇不地道,他的处境可想而知,可一旦平反主政后,他并不把过去的恩怨当回事,连那些对此有过节的人也心有芥蒂,可老田却对此付之一笑。总之,在他的眼里,总是看到你的优点,在他的心里,总是为别人想得多。与他共事几年里,我发现他没有批评过什么人,甚至于,对别人的挑剔和耍性子,他也不太计较。大约是1984年,一次因为一块小刊头漏发,开了“天窗”,造成了报纸上的不大不小的事故。在部门会上他自责,检查也批评了这件事,可是当事人却有些漠然,不当回事,好像还说了些不合适的话。我们都认为当事人太漫不经心了,而老田只是把这件事在大会上说过以后,没有因为对方的散漫而动怒,更没有因此而给其人“穿小鞋”。他好像不曾批评人,也没有见他因为什么对属下发火,更不会无名地动怒。这些,除了与他的修养有关,我认为,体现出老田对事对人,多以一个文人的思维来对待,无论是他的下属,他周围的人和事,他取的是平等宽厚,甚至于过分的自我担当。他行事风格是文人书生式的,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想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尽量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这种大度的领导作风,最容易赢得尊重。
其实,老田的新闻工龄是很长的,早在上海解放前,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并在《新民报》当编辑,那时候,在部门里按新闻工龄排,是四代同堂。他的文名,在文艺界的影响,对新闻工作的贡献,无论有个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头衔都属正常。他对此看得很淡,他没有那些把资历、能力当成倨傲的资本,一心想转化为职务官位,善于经营自己的人的做派。这几年,这种事情,特别是在圈子里,阿谀逢迎、要官找官的事多了去了,被戏为“五子(官位子、钞票子、孩子安排、房子、车子)登科”,而这一切,对老田来说,好像是绝缘的。他对生活的要求简单,抱朴静心,在热闹的都市里,他的家竟然长达二十五年没有做过装修,房子面积也没有改善过,除了图书增添之外,老古董式的家具和外露的电线,可以看出他生活方面的节俭。单位大院里像他这样的,数十年仍然安居于旧楼旧房的人,绝无仅有。生活的清静淡然,总让我觉得他保持有古代文人的一种高古之风,一种通脱雅致的清淡。他有人缘,有口碑。前几年,因为种种原因,文坛有人这派那圈的,爱划线,可老田没有人把他视为左或右或新派或旧派的,也因此,有些人就利用他的影响,让他出席有些活动,让他写字题词什么的,他倒不在乎,也不计较,所以,单位也好,文艺界也好,说到袁鹰,说到田钟洛,都亲切地称为好老头,好像他也就成了让各路人马都放心请的和放心供的尊神。
当然,老田的宅心仁厚,宽容礼让,是大智慧,而他的爱憎喜好,也十分明显。他最是容不得文坛和新闻界的那种夸饰大话的做派,他对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十分反感,只是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激烈壮怀,指名道姓,甚为不屑的;但他也是常有批评,坚守持重,这在他所写的一些杂文中可以找到明证。当然,历经沧海,白云苍狗,他见识得多了,有了自己的思考方式。他多是以书生意气,以文人的善良,以作家的注重心灵的规劝和救赎的方式,以求那些丑陋的东西,得以消失,得以清理,还世界以清明干净。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丑陋和一些负面的东西,老田是那种设身处地地为之找出合理性的理由的人。作为一个古典文化传统浸润深厚的老作家,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渗透在他的精神灵魂中。他对净化人事,清理环境,有着那么明显的期待,但这些每每在现实中,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或许老田还在以自己的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期待。这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灵,一个智者的精神性的追求。
老田平时没有特别的嗜好,虽偶尔也抽烟,却没有瘾,有一段时间,他抽的是一种绿牌的中南海,焦油低,对烟的知识还不如我等年轻的烟民;他也不擅酒,聚会上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量。虽年事高,他身体还很硬朗,行走一如我多年前见他时的模样。在我的印象中,他仅得过一次病,也还是二十年前,因胆结石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没曾见他有过什么病,哪怕是头疼脑热的。他住三楼,每天都说是被动地锻炼,常常下楼采买,提着小布包,邮信,买菜,一应俱办。家中有个自幼残疾的女儿,老伴吴老师身体也不好,这些都压在他肩上,一个八旬老人,其力所堪,但都得承担。
老田的节约是出了名的,他们这一代老新闻人,大多都有这样的好习惯。他用纸是正面背面两面用,有事给我写张便函,都把用过的纸和信封翻过来再用,有时候撕下台历当信纸,这种“敬惜字纸”的作风,对今天的常见的铺张,是一个警醒,也是多么大的反差!现在办公条件好了,可是常看到一些人随意地扯一张复印纸,写上个电话号码,或者几个地址几句话,就把一大张光洁的纸给浪费了,对比老田们的传统,令人感叹,徒有欷歔。
对老田,我当执弟子礼,但因我的懒惰,很少为他主动做什么。每想及此,心有惶愧。他每有新作出版,都不忘送我,还郑重地写几句话,有时是警言,有时是客气话,抬头直呼我名,显得随意,有几次竟以兄相称,令我不安。当年,他离休时,曾专门找出几本书送我,记得其中有《傅译传记六种》一书,题写留言以作纪念。现在,我找出这本十多年前的书,还余有墨香,然而,我也是头发稀疏,学无长进,辜负了老师的一片苦心。
每每读到老田的新作时,总想写点什么,像他这样的老作家,很少有评论文字面世,所以无论从师生还是作家的名头,还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来说,写点评论是应该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几乎没有为同事的著作写过什么,二十多年前应约为当时还是同事的李希凡先生的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写过一篇短文,以后也再没有了。按说为自己的老师写点什么,这也说得过去,在如今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可我却没有。但我敢说,对于他的作品尤其是近作,我以为还算了解。他的散文这些年写故人故事,写往年编辑生涯中的难忘经历,写文化人和文化事件,回忆见长。比如,他写陈独秀,写冰心,写夏衍,写胡乔木、周扬,写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化往事,这一类有多部结集问世。最新一本《抚简怀人》,就是一本回忆与当代名人之间书信过从、编撰往来的散文集,是他几十年副刊生涯中,与一些党政要人和文化大家们文章往来的记录,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还有,他的作品常与时代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新的思维和新的现象,他都十分的热衷和关注,或许与他长年从事新闻工作有关。比如,他在迈入新世纪的2000年,写过一篇《凝视这个数字》的短文,从世纪之交看2000这个数字,凝视它,想到这个世界的争战与美好的期望,以及青年朋友、祖国、未来等等,千字短文,微言大义,角度独具,浸透着老辈作家的拳拳之心。
今秋老田年届八旬,我这小小文字,权作献寿。词不达意,也不是田老师所愿。故以上文字纯属自作主张,但愿老师不见怪。
4.文坛常青树——袁鹰小记
何镇邦
我之认识袁鹰,当然也是先从读他的作品开始。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教语文。袁鹰的散文名篇《井冈翠竹》入选当时的高中语文教材,于是我多次地为学生讲授这篇文章,从分析文章所表达的革命激情到讲解颇有气势的排比句,学生们喜欢上这篇文章,我也喜欢上这篇文章了。从“作者简介”中得知,袁鹰原名田钟洛,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当主任。我虽向往之至,且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但由于身份的差异,是无法谋面的!不过由于喜欢袁鹰的散文,于是找来能够找到的他的几本散文集来读。后来,我为学生编选《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和参与《现代散文百篇赏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编选赏析工作时,就曾选入袁鹰的多篇散文佳作,记得其中就有选自他的散文集《风帆》中的《白杨》。在《白杨》的赏析中,我是这样概括袁鹰散文的特色的:“袁鹰的散文,善于选取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借物(借景)抒情,洋溢着生活的激情和浓郁的诗意;语言简洁明快,风格清新隽逸。”的确,袁鹰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散文,给人一种隽逸清秀的感觉,《白杨》作为兰新路上的旅途生活速写,作为一篇诗意盎然的抒情散文,同赞颂井冈山的竹子,以竹写人的名篇《井冈翠竹》一样,都是很能表现这种艺术风格的代表作。
同袁鹰见面认识以至有些来往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到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1984年和1985年之交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又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大会的筹备和开会期间的简报采写编辑工作。同袁鹰同志的见面,可能就在作协“四大”会议期间。20世纪90年代末,我从鲁迅文学院退休之后,应朋友之邀到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的长城润滑油公司编一家企业报,同袁鹰同志的来往就多了起来。袁鹰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朴实真诚,这一点同与袁鹰有过交往的人感受是一样的。但他的健硕、厚道、敦实,却与在他散文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隽逸、清秀、潇洒的风格颇不一致。可见“文如其人”并非一条铁的规律,应该常有例外,像袁鹰这种为人与为文风格不一致的就是一种例外。
记得在我主编的企业报《长城润滑油》上曾辟有一文学副刊《清水河》,京城内外文坛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在此发表过作品,袁鹰同志也是常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作品的一位名家,而且是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出一版新年笔谈,时间紧急,但是给他打个电话,他还是按时把稿子寄来的,我常常感念他对这个企业小报的支持和对我工作的支持。有几次邀请文坛朋友到长城公司参观座谈,尽管袁鹰同志已经不年轻了,且家中有病人需要照料,也是每请必到的。有一次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还说道,他卧病于榻的夫人还嘱咐他好好看看国企改革的情况,使长城公司的干部、职工和在座的文友均颇为感动。2001年春天,关心长城公司的文友们建议创办“作家书屋”,捐赠自己的作品和藏书给长城公司的职工,以推动长城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袁鹰同志在内的一批老作家的热烈响应。春寒料峭中,袁鹰同志冒着严寒整理图书,带头捐赠了一批图书给“作家书屋”,此事使我们十分感动。
前几年,我在北京西站管委会新闻中心工作的孩子遵从管委会领导的指示,在北京西站建成使用十周年之际,与《北京晚报》一起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征文活动,名为“我与北京西站”。我与袁鹰同志应邀出任这次征文活动的评委。在请袁鹰同志出任评委时我曾同他约定,请他出山,也是为了壮壮声势,他年纪大了,可以不看稿,只是最后把一下关就行了。可后来真干起来之后,他却坚持样样参加,启动仪式与颁奖典礼自然是参加了,初选出来的作品也要一一过目评选。从这次活动中,我再次感受到他平易近人,办事认真与朴实真诚的作风,并受到一次深刻生动的人生教育。
更令人钦佩感动的是,袁鹰同志虽然已年逾八旬,却还精神抖擞,笔耕不辍。我每年几乎都可以收到他寄赠的新书。直到去年年底,还收到他刚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并引起点小小风波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展开一读,清新隽逸的文思以及宝贵的文献价值使我眼睛为之一亮。
袁鹰同志真不愧是一棵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祝他健康!祝他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