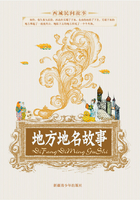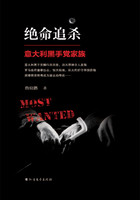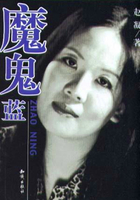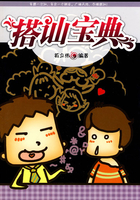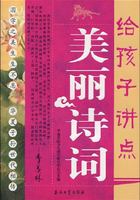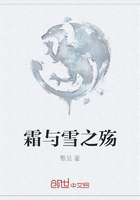叶大姐是文坛公认的一位小说叙述的高手。她笔下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头绪,人物关系、命运以及围绕在其中、或者作为背景的事件与物件,处理得那么从容,和谐,地道。像弹焦尾琴似的,用优美的手指,徐徐弹拨,让若古若今的曲调缓缓地进入读者的心灵。很显然,在她的小说里,当代的文化式样和传统文学的精粹,常常是结伴而行,形影不离的,这就使得她的小说有一种诗意的美。
少年时代的叶大姐,家,自然在北京。后来变化了,去了土黄色的西安。在这种颜色的天地里,人群中,叶大姐不仅做过医院的护士,还做过报社的记者。然后,东渡扶桑,去了日本的千叶大学读书。这样的经历,使得叶大姐的知识储备和感知领域一下子扩展起来。从叶赫那拉氏的子孙,到北京的女学生、西安的护士、报社记者,再加上赴日的留学生,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叶大姐成为一个挺特别的作家,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如树上的果子一样,人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了”。特别是叶大姐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使她天然地获得了对祖国、对叶氏之宗族,当然也包括土黄色的西安——静下心来——隔海瞭望与思索的机会。这对她能够全景式地讲叙神州天下的故事,无疑是一种天赐的力量与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之后她创作的小说,特别是对清亡之后各色人物的命运展示,很是入情,入理,入微,既有天然的灵性,又有女性的敦厚与善良,还要包括她南北闯荡之后的坦然、自信和不吐不快的风格。让老老少少的看官们掩卷之后,感慨万千,无法矜持。但是,叶大姐却提醒大家说:“有人说我写自己,在写家族史,这未免让人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文学作品跟生活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很难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
有时,历史和现实是不完整的,需要想象来补充,这恰恰是叶大姐的强项。记得前年在北京,在中国作协的招待所里与叶大姐见面,我特别欣赏她用陕西话讲的那些让人喷饭的市井笑话,非常让人开心。还有更开心的,同是那次见面,大会安排一个青年作家代表我们讲话。叶大姐便真的是叶大姐了,像党支部书记那样,严肃地指导那个青年作家应当在发言中先说什么,后说什么。那个老实且厚道的青年作家一个劲儿地点头,而且还很感慨的样子。但发言的时候,他根本没按叶大姐的“指导”去做。坐在下面的叶大姐也开心地笑了。那次分手的时候,叶大姐送我一包陕西产的、类似快餐面式的“羊肉泡馍”。黄色花纹的包装,很好看,给人一种很陕西的感觉。回到东北我没舍得吃,让小女儿品尝,小女儿吃过了说,“挺不一样”,但是不用但是了,只有到陕西去,才能吃到真正的羊肉泡馍,而且才能真正地走进叶大姐的世界。
5.走出叶广芩
叶广荃
不少读者都知道她的名字——叶广芩。
我的同事隔三岔五会对我说,我看到你姐姐又写了篇什么什么。或是电视里在演你姐姐的戏……同事和朋友们由于认识叶广荃便更关注了叶广芩。其实在一般读者当中,我想也未必,关键的原因是我是叶广芩的妹妹,人家乐意把这样的话对我说。自己的姐姐有人关注,这当然很好,她的作品,她的家庭,她的经历都有人问到,而我却说不出什么,我觉得她很一般,甚至太一般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向别人说道的。她每次回北京,我得事先帮她打扫屋子,得时不常地做些个家族的传统菜给她送去,得替她交煤气费、物业费、电话费……其实这些她自己都能干,偏不干,让我替她干,而她自己就在电脑前头敲字,一敲一整天,一天吃一顿饭——早点。有几回上我们家吃晚饭,饿得眼睛发蓝,问她为什么饿成这样,说是一天没吃饭,顾不上。
读过一些采访她和评论她的文章,有“走近叶广芩”的,有“又见叶广芩”的,还有“陕西有个叶广芩”的,读了都觉得有些阻隔,不知他们在说谁。也许那就是真的她,竟让家人感到如此陌生,如此遥远……我和她应该是属于“零距离”接触的人,由于距离太近,一切都变得很模糊,就如同看一幅油画,太近了全成了斑斓的色块,想的是拉开距离,远远地看,也许清楚。但是,远的走不近,近的走不远,这一近一远,就是角色的定位。要想更换,不容易。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是叶家兄弟姐妹中接触最多、关系最深的一对。
我和芩姐相差四岁,从小厮混在一起。从我记事的那一刻起,她便存在于我的周围了,贯穿于整个少年时代。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我们全被叫到姥姥家,人们围着母亲在说着什么,我和芩姐靠着炕沿站着,听着大人说话。突然,芩姐号啕大哭起来,我觉着应该跟着她学,也哭,其实我根本弄不懂为什么要哭。原来是父亲去世了。客死在外地,芩姐是在哭父亲。芩姐对那天是这样回忆的,“有一天来人带话说姥姥得了急病,叫母亲回去。我和小荃随着母亲来到朝阳门外的姥姥家,到了姥姥家。姥姥很健康,没有一点儿生病的样子,我说,姥姥您不是病了吗?姥姥没说话。大舅把我拉过去说,丫头,你得懂事,得为你妈想想,小荃还小,别吓着她。到底怎么了?我懵懵懂懂跟大舅进了屋,屋里有一桌未动的酒菜,这种非同一般的阵势让人心底一阵阵发凉。母亲见到我,哭了。母亲说,你父亲殁了……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
那年我四岁。从跟着她哭的时候起,好像就注定了,我们的行走轨迹往往踏在一个点儿上。芩姐的性格外表倔强,但其实是个心思很重、感情很细腻的人。父亲去世后的一天,母亲病了,她带着我去北新桥买东西。两个幼小的女孩子身带重孝,又没有大人领着,是非常扎眼的,夏天,胡同里净是些纳凉的人,免不了有些人指指点点。我看到芩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言不发,低头只顾走路,也不管我是不是能跟上她。回来时,她从另外一条路回的家。还听母亲讲过,带她去方家胡同小学报名上学时,负责报名的老师例行公事,问父亲在哪儿工作,她沉默了许久,哭起来,弄得老师很尴尬,母亲不好意思地一个劲儿说孩子不懂事儿。后来人们都记住了,不能当着她提父亲,父亲的去世对她幼小心灵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就如同后来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样。
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为生活而奔波,顾不上我们,对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放任自流,而这恰恰给了我们自由发展的极大空间。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考试得了一百分,母亲也没有太多喜悦,考试不及格,也不责备……
我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上房。房上乾坤之大,乐趣之多,没有上过房的人是绝难理解的。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大四合院里,院子南墙根儿有两棵大树,一棵柳树,一棵榆树。靠东北角有一个小过道,穿过小过道是一个长方形的后院,后院过去是花园,后来盖了一排北房,但规格不能和前院的正房相比,这一溜儿北房顶上就是我们的“房上乐园”。后院尽西头有一棵枣树,树旁边竖着一个梯子,这就是上房的重要通道。芩姐性格像男孩子,上房、爬树是家常便饭。母亲上班一走,芩姐立即就成了王爷,她问我,咱们今天干什么?我说,上房。于是就上房。噌噌几下就上去了,在上面如履平地,我们家养了只黄猫。猫也爱在房上待着,见我们上来,猫就跑,我们敢大步流星地在房上追猫。站在房顶上,向四周望去,连绵起伏,一片灰瓦,能隐隐约约看见景山,这时,芩姐就底气十足地喊那么两嗓子,唱“将酒宴摆至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会恰如其分地为她喊几声好。配合相当默契。两个小丫头,在房顶上这样张扬,也就是在当时,在大人放任不管的环境下,用“宽松”一个词汇足以概括。
这样的“好日子”不是哪个孩子都有机会能得到,至少,我的孩子今天我不敢将他撒出去,让他在房顶上喊叫。
我们第二喜欢的是演戏。应该说芩姐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好编剧,好演员。家里有的是老式衣裳,不唯长袍马褂,甚至还有两把头,花盆底,穿戴起来比戏台上还真。没有观众,街门关着,大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不怕谁笑话,所以在表演上我们绝对放得开,那些即兴的演唱,投入的表演,至今想来仍让人怀念。演瓷人戏是我俩的传统项目,戏台是母亲的梳妆台,台面分上下两层,上面那层较窄,是摆雪花膏瓶子、梳头油什么的地方,靠后面是面大镜子,造型很像大戏台。演员是家中形态各异、一寸多高的小瓷人。父亲是搞陶瓷的,家里这种瓷人多的是。演瓷人戏只能一个人演,这样就必须有一个人充当观众角色,而当观众的通常是我。芩姐一边摆弄着小瓷人,一边绘声绘色地念叨着戏词儿,一会装成小姑娘,一会儿又装成老太太,一会儿又装成小伙子,就是装狗,装老鸹,她都叫唤得很到位……她特别会编故事,一出一出的,有时候能把母亲也吸引过来,放下手里的活不干,专看她演戏。她演得非常认真,现在我体会到,她不是在哄我玩儿,那是她的所爱,是她的兴趣所在。她演累了,该我上了,我大多是演些简单情节的,实在没得演了,就把她演过的戏,再小改一下,好歹也算一出。偏偏她的记性非常好,每到这时,她就会揭露我,而我就死不认账……前不久,我和她一起去看望已经八十岁的四哥叶广明,芩姐和我们提起自己的梦想,说写小说实非所愿,她最钟爱的职业还是去唱戏!可惜,现在年纪大了,嗓子也不行了,只好怀着一腔遗憾看别人在台上表演。难怪她有时接些个电视连续剧脚本类的活计,干得十分得心应手,舒展自如,想来那还是她的戏剧情结。
画小人书是我们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事情。那时,我已经上小学、认字了。暑假,芩姐找来了白纸,说是要画小人书。一会儿就把纸裁成了小人书大小,拿针线一钉,完全是地道的线装书。接着就开始画起来。画画儿的本事我俩都不含糊,父兄都是画家,恭亲王的孙子溥心畲和徐悲鸿是四哥的老师,姐姐毕业于美术学院,耳濡目染,我们也敢在白扇面上涂鸦,全无顾忌。在当时我的印象里,芩姐的人物画画得棒极了,十分传神。记得有一次她犯了什么事儿,母亲说了她几句,第二天,满院子的墙上全是粉笔画的人头像。寥寥几笔,只画了脸形和翘着的头发,眉眼都没有,但我一眼就认出是谁,真是惟妙惟肖。我跟她说:“你画的是咱妈,你当我看不出来?我给你告诉妈去。”她说:“你要是敢告诉,以后甭想让我再带你玩儿。”我还真怕这一招儿,没敢去告密。母亲看了这满院子的头像,竟没发觉什么。当时,画小人书不光是画,还得编故事情节,芩姐编故事的本事又发挥出来了,那一出出的戏、一个个的故事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纸上,她竟然自编自画出了一本小人书!在芩姐的感召下,我也开始裁纸、钉本儿,画小人书。那年暑假我俩编、画了好几本小人书。这些小人书一直保留到我上女一中。“文革”时候,芩姐和四哥两个人关起门来,将家中的“四旧”做过一次大清理,名人字画、善本书籍、字帖卖了几车,是当废纸卖出的。唱戏的全套锣鼓家伙是她拿出去当废铜卖的,十四块钱,这套家伙是当年“富连成”的叶春善先生(著名京剧艺术家叶盛兰的父亲,叶少兰的祖父)为我们家选购的。祖辈留下的多少精美的瓷器在院子里被摔得粉碎……那次的毁坏是完全彻底的,让人心疼的。所处理的物件里,也有我们画的小人书,怕人说是才子佳人,给烧了。前不久,女一中的同学聚会,我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说,还记得那时上你们家去,看到你姐姐和你画的小人书,真让人不可思议。没想到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学,竟还对近四十年前的事记得这么清楚。东北作家阿成在谈到芩姐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叶大姐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现在看来,她小时候演戏、画小人书不能说跟后来的小说创作没有关系。小说的首要条件是好看,是情节,然后是语言、结构等等,好看的情节就是故事,怎么抓人是语言,如何讲清楚是结构,这对芩姐来说好像不是很难,她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要讲起来却很有吸引听众的本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跟她的小说风格很相像。搞文学得有天赋、有悟性,这方面,她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是佼佼者。
1963年,芩姐考上了北京女一中。我问她为什么不考离家近的女二中,她说,一就是一,排在二前边。这个回答到现在想来都挺有意思。我们学校的校名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女子”合成一个字就念“好”,就是北京第一好中学。在她的心目中,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最好。的确,“文革”前的女一中是北京市女子中学中数一数二的,要考进女一中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学校较远,芩姐中午不回来了,兴趣又转移到了读书上。她每天下午放学回来,都会带本课外书,是从图书馆借的。她要求自己很严格,不论多好看的书,都先放一边,先做作业,然后复习,一切都妥当了,才拿起课外书来。星期天也是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复习功课,她每礼拜天还要画画,画工笔,细细地一笔一笔地描,有时一张画要画一个月,说是要磨炼性情。而这正给我提供了看书的好机会,我每天下午早早儿的把作业做完了,眼巴巴儿地坐在廊子下等着她放学,她一进门,我就上去抢书包,把书翻了出来开始看。她借回来什么,我就看什么,而且得抢在她写作业的这点时间内看,所以看书的速度极快,因为不定她什么时候就会要走了。在那段时间里,我真看了不少书,反正是她看过的,我也全看过,不过也落下个不好的毛病,看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有时一本书一晚上就看完了。这种“快速阅读法”,到现在都改不过来。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报志愿很有些戏剧性。我的志愿是芩姐帮我选的,一共是三个:女一中、女二中、女四中。志愿交上去第二天,班主任让我去校长室,说校长找我。女校长和蔼可亲,先说了不少夸奖我的话,不过,最后我还是听明白了,是报的志愿出了问题。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三个志愿没有拉开档次,三个志愿跨了三个区,西区、东城、朝阳,而且都是这三个区的顶尖学校,一旦有一点闪失,将全军覆没。女校长微笑着,把志愿递给我,让我回去把第二、第三个志愿改一下。第二天,我把志愿交回校长室,女校长的脸上没有了微笑。我的志愿还是那三个,原因是芩姐不让改,还扔给我一句话“你只有一条路,必须考上第一个。”现在想起来,老师、校长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而我却是个不识时务的学生,又碰上了一个爱顶尖的姐姐。破釜沉舟,这是芩姐的良苦用心。从把志愿交上去的那一刻,我就没退路了。
最终,我考上了女一中,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9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