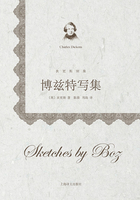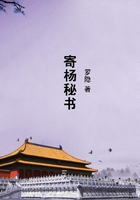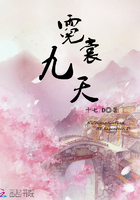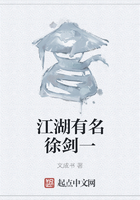1.致何镇邦的一封信
梁晓声
镇邦兄:
好!
你对我的要求,实在让我为难。
《时代文学》是每期寄我的刊物,前几年我在该刊还发过小说。它所辟的“作家写作家”的“名家侧影”专栏,我读过。但是,非常坦率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成为被写的对象。我这个人,实在是一个没什么写头的人,根本就不值当让别的作家来认真地写。不认真地写也是不值当的事。又,我和作家同行们,没主动的交往。同行中朋友是有的,不过就是说得来,相互可以托信,过心,却又淡如水的一种关系。我是作家不假,但我的人生似乎从来和文坛没什么关系。“文坛”二字对我只不过是一个词而已。我的言行主要在我工作的单位,我居住的社区,以及我的故交们的心目中。倘我对以上三方面任何一方面的任何人说:“写写我吧,有编者要这样的文字。”那他们差不多都会爽快地说:“行啊!”
而且我对于他们,是有的可写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我首先是一个稔熟的人,其次才是作家。
但难道我会真的让他们中的谁写写我吗?
那不滑稽吗?
至于你将联系哪位同行来写我,我是不管的。
我只完成你交代我的事,照片、签名及这一篇文章。
你说随便我写什么——这就仿佛在某些会上被主持人要求“随便说几句话”。
那种情况之下所说的话,大抵是可说可不说的,正如我这篇遵命的文章。故为其难。
那么就汇报我近期常在想的两个问题吧:
一、我这一代作家的先天营养,现在看来,单薄性是越来越显然了。我或许没资格这么说。那么就只说我自己吧。我一直认为自己青少年时期,便是亲近文学的青少年。所读文学作品,比普遍的同龄人稍许多几本。从前我一直夸张地自我估计了这一点,并且引以为豪。虽然现在我也勤奋地读着,却忽然有种感觉,怎么明明在营养方面主动地“吸收”,反而更加觉得自己单薄。
我的写作,第一靠经历,我这一代人,谁还没有点儿经历?第二靠经验,写了二十余年,谁还没总结出点儿章三法四?第三靠积极而又无悔的入世状态——我接受“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这一最低层面的理念,并且不耻于在这一理念之下孜孜实践,进而提高。第四靠的是洞察的本能。
这第四一点,乃是我写作二十余年来唯一欣慰的获得。
现在我对自己的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三流的一名书记员而已,类似乡镇文秘的那一种书记员。
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作家的好感觉。
获奖的次数并不能使我不好的感觉好起来。
现在尤其这样。
二、以我的眼看现在年轻一代的作家们。除了经历、经验和入世的状态他们与我不同,或某种程度上不及我,其他一概方面都比我强,而且强很多,太多。为什么单单不比洞察的本能呢?
因为这种本能,他们其实也是具有的。由于不同的经历,他们洞察世事的立场、角度也便与我不同,并且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往往赋予不同的表现。于是中国文学的总貌随之别开生面。
他们优长于我的方面,主要如下:
1.他们与文学亲密接触的时代,中国出版业空前解禁。他们是文学青少年时可选择的读物真是丰富极了,简直丰富得来不及从容选择,简直丰富得时常陷于选择的困惑。这使他们得天独厚地接触到了我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根本接触不到的许多文本。我的先天文学营养是单一的,他们的先天文学营养是周全的。起码,他们想哪样,便能哪样。
2.他们与文学发生亲密接触的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空前活跃,使他们得以在文学青少年阶段从多方面接受和领略文学真谛。这或许会导致他们某时迷陷于歧途,但总体上意味着文学的宝贵的自由原则。
3.他们驾驭语言的才情,普遍高于我“这样式的”作家。我甚至经常觉得,在新一代作家笔下,中国文字发生了不容忽视的质变。我起初是轻蔑的,现在我不敢轻蔑了。中国文字在他们笔下毕竟变得生气勃勃了,风趣幽默了,更加鲜活生动了。在文字与文学的细腻的关系方面他们显然具有比我“这样式的”作家更佳的感觉。
4.他们看中国的眼,已善于纵跃在中国之外。改革开放,使世界离他们近了。他们这一点,曾是我所批判的、反对的。现在想来,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往往比我“这样式的”作家看得更客观些。
5.他们中有些人原本学的不是文学,而他们之与文学发生亲密接触,也同时使社会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法学、科技、管理、经济等等学科对文学实现了良好的渗透,文学在他们笔下多姿多彩了。你会看出,我始终在用“文学”二字,而没具体谈他们的小说——因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写作,如散文、随笔、札记、杂文、议论文等,似乎更明显地体现着他们以上的种种优长。至于小说,目前还不能作太高的评价。丰富的文学营养,值得刮目相看的文学感觉,转化到小说里,对于具体某人而言,似要比呈现在散文类文本中更复杂一些。对于文学总貌,乃是更需要耐心期待之事。但已有多种迹象表明,中国前所未有的小说创作的新局面,正在他们的实践中渐露端倪……
我“这样式的”作家的优长之点,目前还勉强是优长,但不须多久,便注定不再是了——所以我不能“吃老本”,得虚心学习。以上汇报,原打算沉思而后梳理,且应了别人的约稿。今你催逼甚急,只得先寄你。
我不交你吩咐的这份差,你高兴吗?
“随便写什么都行”这句话,对写作之人是虐待。
此刻已夜十二点半,明日尚有明日事,一拖,只怕就不能按时交差了。
打住。原谅行文匆匆!
2.梁晓声印象
李国文
对于晓声,有好多话想说。第一,他是值得一说的作家;第二,如果撇开文学,仅仅作为朋友,我认为他更是值得一说。
他在中国时下健在的,还在写作的作家群中,知名度应该排在前十名中的一位。虽然文学圈里有人也许并不支持我的这种观点,但实际上,像梁晓声这样,不靠炒作,不靠人为的非文学手段,就靠他的名字,能够拥有相当数量读者的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是屈指可数的。可看有些作家,名气很大,名声很响,但所谓的“大”,所谓的“响”,只是在一个很狭窄的圈子里而已,一出这个圈子,便没有什么动静了。
不久前,一位在报纸主持读书版的记者,逛西单图书大厦。在二楼当代文学书架前,从架上抽出一本书,问他身边也在买书的读者:“请问,你读过这本书吗?”被问者接过来书,看了看,摇头。他又问:“你听说过这位当红作家吗?”
被问者仔细看了看,又摇头。
他又抽出架上的另外一本书,问:“这位女作家的书,你读过吗?”
被问者有点警觉起来:“你是推销员吗?”
他连忙解释:“我只是想了解了解,值不值得花钱买。”
被问者翻了翻书,念了书名和作者名,“没听说过——”当翻到扉页,看到这位女作家的玉照时,突然发表评论,“长得还算说得过去噢!”
当我听完记者先生这段报道后,顿觉好奇,连忙打听这位长得还算说得过去的女士的芳名。
他不答,我也只好作罢。
这种很随便的民意调查,自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作家和作品,在圈子里和在圈子外,其反响存在着碧落黄泉的反差,也是事实。
有一家出版社的老总亲口对我说,梁晓声的集子,在销路上,即使在时下文学图书相当式微的状态下,无须宣传,也能保证几万部的。有一家文学期刊编辑部的副主编说得又更玄一点了:“这个梁晓声啊,你不能不服他,他有一批属于他的读者。”
每个作家,都会有他相对应的读者群。我记得上个世纪末,晓声每年都要出一本回想录之类的大随笔,在书店里,是属于躺在那儿卖的书。一般图书,都在书店的书架上站着卖,能摆平在那儿出售,说明这本书好卖。不知为什么,新世纪以来,晓声不再有这类作品问世。有好几位铁路上的熟人,都是些极普通的购书者,还向我打听过。由此可见,读者虽然有时会被炒作所误导,但若是对某位作家有了专注的感情,便不大受到文学圈子里议论的影响。权威的看法和评论家的见解,有如东风吹马耳,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了。
有人认为某个作家好得不得了,挡不住读者不买账;同样,有人认为某个作家不怎么样,可读者偏偏喜欢他。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清一色的世界未免太可怕,文学也如此。若没有选择,豆腐一碗,一碗豆腐,那也太痛苦。
选择是读者的权利,谁也无法使那些到书店来花钱购书的读者一定要买这本书,而不让买那本书,那就违背市场规律了。市场,是严酷的,那些在圈子里名气很大,名声很响的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特别是长得还算过得去的女作家,有办法让评论家,让记者,让编辑表现出拥趸的热情,但那张玉照,未必能使读者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买她的书。
不过,书卖得少,并不表明书没有文学价值,对于作品的评价,从来是见仁见智,不必求其“舆论一律”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在圈子里得到赏识,是一种价值;下里巴人,老少咸宜,在圈子外获得呼应,也是一种价值。对象不同,期求也不同;口味不同,效果也不同。这两种价值,不存在谁好谁差的比较。说到底,能够进行文学仲裁者,最后只有时间。所以,至少要过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才能略见分晓。因此,此时此刻,说什么长长短短,好好赖赖,都为时过早。
我问那位副主编先生:“梁晓声的铁杆读者都是哪些人呢?”
他说:“应该是那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五十岁左右,插过队,上过山,下过乡,回城后当普普通通老百姓的那些人;特别是在其中生活得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特别是其中的女性。”
这两个“特别”,令人听得有些心酸。
因此,能为这些读者写作,或者,在写作时能想到这些读者,我想这个作家一定是好人。好人的心都良善,他想着那些不是很走运的普通人,于是,我挺佩服晓声,因此,他的作品能给这些读者带来多多少少的温馨,能够使他们郁闷的感情,多多少少地得到宣泄,我想,真可以用“善莫大焉”来肯定晓声的劳作。现在,该来谈谈我心目中的好人梁晓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写过一篇《好心》,发表在1993年9月9日的天津《今晚报》上。文章不长,现抄录在下面:
这个听来的故事,是我的朋友,作家梁晓声给我讲的。
他家住在儿影厂宿舍,一天,到北影厂去办点事情。这两家电影厂也就一墙之隔,没有几步路。但他在路上碰到一个行乞的妇女,还带着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朝他要钱。现在这些讨饭的常常拦劫似的挡住你,或拉住衣服不撒手地要钱。我对这类人采取不理会,绕着走的政策。但晓声,是个极具平民意识的作家。他不但是有太多的同情心的汉子,而且还是一个不怎么会说“不”的敢于断然拒绝什么的人,于是,他被缠住不放了。
“给两个钱吧!”
“可怜可怜俺们娘儿俩吧!”
“俺们饿了两三天啦!”
在我们这个首善之区,经常有这类“强要饭的”横行在街头巷尾,实在是大煞风景,有碍观瞻。政府也时不时地整顿,但遣送走了,不多久又会回来的。这类人就认为你应该施舍,应该给钱,不给,还会悻悻然地遭到不满。这在任何城市里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尽管是在首都,尽管不停地遣送,也难以绝迹。不过,即使那些世界上的一等强国、一等富国,也不能保证在地铁站里,在广场上,没有人向你伸出手来要钱的。想到这里,人家并不在乎,并且发照,准许持证行乞,我们倒也用不着不好意思了。
曾经有人写过关于我国各地丐帮的报告文学,好像是作家贾鲁生吧。据说因为在城市里行乞,比干活还来钱,于是有一批要饭专业户,长期驻扎在京城,要着要着,能要出万元户,要出小康之家呢!
梁晓声根据他作家的判断,相信这对追着他讨钱的母女俩,不是那种很有专业经验的要饭人,就给了她们一点钱,走了。等他从北影办完事返回,仍旧在这条路上,又遇到了这对母女,缩颈斜肩,在那里向行人苦苦讨要。当时是春三月,还不怎么暖和,见她们穿得也单薄了些,他动了恻隐之心。
“这样吧,”他说,“我家里还有些过时不穿的衣服,虽旧,可并不破,你们跟我回去,拿两件穿吧!”
北京春天的风,有时挺峭厉的。但晓声的心,却是非常的热。于是他的热心,好心,善心,就给他制造了一场烦恼。
“谢谢您啦,谢谢您啦!”这也许是真的母女俩,但也不排除是临时的组合搭配,以增加要饭效果而扮演母女的两个人,自然跟随着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了。
好在很近,就到了家,晓声翻出几件旧衣服送给她们。看到她们高高兴兴地下楼走了,就关上门,继续写他的东西了。这世界总得有点温馨才行,虽然这些旧衣不值什么,但看到她们那种愉悦的样子,他也感到一点欣慰了。
没想到,凳子还未坐热,有人敲他家的门,打开门一看,还是这对母女。她们说,“刚才您老给衣服的时候,还有一条旧毯子,能不能行行好,也给了吧!”
因为他太太焦丹上班去了,晓声吃不准这条旧毛毯家里还有没有用,该不该给出去,他急于写东西,也不想让她们老是缠着,就做主送给她们了。“好好,给你们,快拿走吧!”
这是上午的事,没想到,下午她们又来敲门了。
他万万没料到,一开门,一大群要饭的围在他家门口。那母女俩差不多把附近的同行业的人都招引来了,挤满在楼道里。前面的,大概是和她们同属一地一村的。后面挤上来的,她说,不和她们一伙的,是见她们得了便宜跟着来的。这些尾随而来,也想捞些什么的要饭的,并不相让。于是在楼道里,两伙人互相攻讦。她要求梁晓声只可怜可怜她们一伙,可又不让非她们一伙的获得这样的机会。后来者当然不肯示弱:“凭什么就许你们要,不许我们要!”
楼道里自然乱成一团,好像要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个乞丐王国的电影似的,弄得我的朋友不知该怎么招架才是。这场风波,闹了两三天,才告平息。整个楼群里的邻居,都对这位作家侧目而视,弄得他窘透了。
梁晓声给我讲他这段故事时,仍是一脸哭笑不得的样子。
这其实是个接近于闹剧的小喜剧,苦笑之余,倒也充分证实,晓声是毫无疑义的好人。
虽然,有时,这好人做得有点尴尬,有点吃力不讨好,但他乐此不疲。只要有人敲开他的门,晓声老师,如何如何,他不但会听下去,还会帮着出主意,还会解囊相助,还会找到有关部门,仗义执言,甚至到最后,求他的人反而插不上手,只好待着看热闹,他个人却东奔西跑地忙个不停。
有时候,我也奇怪,你们早先认识?
他承认,大多数,这些不速之客都是陌生人。不过,来求他的人,都能很快找到谈话的楔入点:或是兵团的战友,或是知青的后代,或是东北老乡,或是哈尔滨道里道外南岗跟他家能拉上一丝片缕关系的邻居亲戚,只要触动梁晓声的故土情结,文学情结,他就不能置之度外。于是那些热爱文学、愿意为文学献身、非要成为大师的文学青年,那些抱着尺把高稿纸写成的电影文学剧本,指望梁老师点石成金,然后得金鸡奖,得飞天奖的影视发烧友,便频频出现在他家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