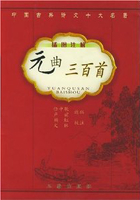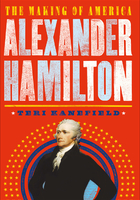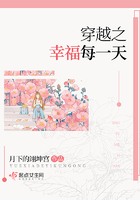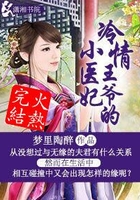(第一节) 为文学辩护
“为了说明诗如何重要,首先必须弄清它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这个第一步做得极不妙。”
瑞恰慈在其理论生涯开始时,就给自己(也给未来的新批评派)规定了这样一个任务。这样做是有好处的:首先把文学与人类的其他文化活动区分开来;作为一种艺术,它与其他艺术有什么区别;作为一种文体,它与其他文体有什么区别;还有一点,常被许多文论家所忽视的,作为一种人的与现实环境相关联的意识活动,文学与其他此类活动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什么特殊点。因此,所谓文学特异性(the differentia of literature)是三维的。
许多文论派别,尤其是形式主义的文论派别,很容易忽视或排斥这第三维。,他们的理论还涉及文学语言与“客体”的关系;但结构主义者却认为不必谈这个第三维;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根本不承认这第三维;而新批评派却在这第三维上立论,这是新批评派的一大特点。
西方文学理论家自亚里士多德起常把文学理论称为“诗学”,在古代,诗就是文学。在现代,诗已降为文学中一个次要体裁,诗论却常占据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新批评派以“散文”为对立面来说明诗的特征,所以克里格称他们为“诗的新辩护士”,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以“科学文体”(scientific discourse)为对立面在为“文学文体”(literary discourse)辩护。但使人头痛的是,他们有时的确是在就“诗”论诗,而把所有的散文文体当作对立面。结构主义文论家喀勒云:“诗学之于文学,恰如语言学之于语言。”实际上结构主义者所谓“诗学”(poetics),是“文学理论”的代称或雅称。而六十年代法国的“新诗学”派(Nouvelle Poetique)实际上主要研究小说结构。这个辩护对象混乱的问题能否如此理解:诗是新批评派所搜寻的“文学特异性”最完备的体裁。文学文体和科学文体实际上没有明确分界,有各种中介文类,组成一条连续的光谱,诗处于文学性最强的这一端。因此无论诗辩的对立面是科学文体还是所有的散文,辩护对象依然是文学特异性。
早前柏拉图就在谈论哲学家与诗人目标完全不同,但在十七十八世纪前,诗主要在宗教伦理前自辩。到十八世纪末,西欧文化生活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科学渐渐取得统治一切的地位。牛顿物理的精确体系与达尔文主义的严格因果律使不少人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均应以实验科学方法来分析,这就是泛科学主义(scienticism),在十九世纪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如果用实验科学标准衡量文化活动,文学就成了无法验证的呓语妄言,无存身之地。所以诺瓦里斯泣说科学毁灭了一切,济慈哀叹科学的进展破坏了诗的可能性。
早在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起而激动地为诗辩护,他们的诗辩方法是带着诗一齐无限地自我扩张。雪莱声称“诗人们是祭司……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华兹华斯宣布“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与终结”;从布莱克到阿诺德都想用诗取代宗教地位。对浪漫主义这种夸大狂,新批评派是很反感的,瑞恰慈总结成一句:“全是过甚其词。”
另有一些文学家的做法是把诗混同于科学。左拉是个突出的例子。他说:“医学以前是一种技艺(un art),现在正在变成科学,为什么文学就不能采用一种实验方法而变成科学?”他的雄心勃勃的实验结果是走向了自然主义。惠特曼则试图使诗与科学并驾齐驱,他认为诗“应当表现科学赋予人和宇宙的广袤、光彩和现实感……在诗的美中,有科学献的花束和最终的鼓掌”。诗在科学的意义上比科学强。
另一批浪漫主义者“从康德美学出发”发展了另一种诗辩:诗歌不涉及理性,不涉及概念及利害计较,因此诗比只靠理性的科学伟大。柯尔立治说:诗与科学作品相反之处在于“它建议将快感而不是真理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而济慈在诗中说,美被哲学一触就全部消失。
这种撤出理性阵地以退为攻的办法,成为十九世纪形式主义诗辩的主要路子。但新批评派却反对这种诗与真理不相容的观点,他们认为诗有认识价值,只是不同于科学的认识,这是新批评派一个最触目理论特点:“认识论”诗辩。
(第二节“拟陈述”与诗歌真理
1924年,瑞恰慈在名著《文学批评原理》中提出科学与诗的区分在于科学语言是“指称性的”(referential),而诗歌语言是“感情性”(emotive)的。他说:“一个陈述的目的可以是它所引起的指称,不管是正确的指称还是错误的指称。这是语言的科学用途。但一个陈述的目的也可以是用它所指称的东西产生一种感情或态度。这二者的区别只要弄清楚就很简单。”
然而,这二者的区别远不是瑞恰慈想象的那么简单。瑞恰慈的理论,实际上源自文学语言虚构性(fictionality)这个十九世纪实证主义文论家所用的命题,瑞恰慈只是加上一点,说其用途是要激发感情。我们可以看他在一年前(1923年)的《意义之意义》中给了文学语言一个典型实证主义式的区分标准:要判明我们对语言的用途是符号式的(symbolic)还是感情式的,最好的试验法是问一下,“在通常的严格科学意义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答案是与真理性相关的(relevant),即符号式的,如果不相干,则是感情性的。他举了个例子:“埃菲尔铁塔高九百英尺。”这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却是符号式地使用语言,因为有关真假;“人是蛆虫”,这就是感情式地使用语言,因为根本说不上它是对还是错。
没有比这种“试验法”更实证主义的文学理论了。其漏洞太明显,韦莱克就指出文学作品中不少地方完全能在现实中证实,例如巴尔扎克《幻灭》中写印刷厂,左拉《小酒店》中写巴黎下层社会等等。不过我们不必在此多费笔墨,因为瑞恰慈自己很快放弃了这种陈旧的观点,而以作者使用语言的目的上来找文学的特异性:“感情式”语言的目的是激发感情。这种说法实际上也不能成立,正如兰色姆指出的:“每种经验,甚至科学经验,都有感情。没有一段讲述(discourse)毫无兴趣,亦即感情,而能够站住脚。”瑞恰慈自己也明白说话者不想获得感情(赞同)反映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瑞恰慈命题的重点其实不在“感情性”上,他是想说文学语言的真实性与现实无关。这一点,在他1926年发表的小册子《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中说得更明确。在这本书中,他把诗定义成为“非指称性拟陈述”(nonreferential pseudostatement),他说,诗的语言,“其真理性主要是一种态度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发表真实的陈述不是诗人的任务。”
我们不厌其烦地把瑞恰慈“拟陈述”命题的前后表达方式说清楚,是因为新批评派全体一致地反对“拟陈述”说,而且新批评派的基本理论就是在这论战中形成的。这场论战从二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末,争论的焦点是诗歌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表达真理的问题。在这个文学理论的重大问题上,“新批评之父”瑞恰慈只是提供了靶子。
诗歌真理问题实际上是西方文论自古典期以来的老问题。左拉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到布瓦洛的全部文学批评都在阐述一个原则,即一部作品应以真理为基础。”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被提出而没有被信服地加以论证。
我们上面说过唯美主义几乎一致反对“诗歌真理”说。坡认为“诗与真理像油和水一样无法调和”;波德莱尔说“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是它自己”;王尔德干脆称艺术为“美而不真的谎言”。瑞恰慈并不同意唯美主义这种看法,他认为“任何艺术都必须以真理为其主要工具”,但他认为诗歌中所表达的真理只是一种“可接受性”或“使人信服的力量”(convincingness),这样他就把诗歌真理与西方文论中关于“相信”(belief)的旧命题重合起来(参照宋朝郭熙画论,他认为画应当使人觉得“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在瑞恰慈看来,文学作品与事实是否相符是傻瓜才会考虑的问题。只要作品能激起我们整饬的、前后一致的情感反应,使我们“相信”,它就包含了真理。因此,这种真理只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可以有真的“拟陈述”,也可以有假的“拟陈述”,真假之别只在于作品是否能激起我们前后一致的情感反应,但不论真假,它们都是“无客体的”(objectless),也就是说,与现实无关。
在这么一个大圈子的论证之后,瑞恰慈实际上走向与唯美主义者相同的结论:他认为济慈的公式“想象当作美的东西即真理”能成立,只消把这“美”改成“有秩序的反应”。
为说明这一点,瑞恰慈举了一些例子。他说:“《鲁滨孙漂流记》的‘真理性’在于所讲的东西之可接受性,在于这些叙述的效果、兴趣之可接受性,而不在于这些叙述是否与流落荒岛的水手亚历山大·赛尔刻克的(Alexander Selkirk)(英国水手,曾因海难独自在荒岛上居住十年。其事为作家笛福用作《鲁滨孙漂流记》题材)事实相符。”
这种把心理反应的有效性作为真理标准的做法,实际上是受了实用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新批评派一直指责瑞恰慈“拟陈述”说是承袭了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等实证主义者的衣钵,而瑞恰慈本人却说只有“死顽固实证主义者”才不同意他关于“相信”的论证。其实瑞恰慈“拟陈述”命题与穆勒逻辑学关于排中律的论证的确相合。穆勒把矛盾排中律解释为人的“相信”中不能存在这样的判断,实际上他是以两个相反判断之不相容代替两个相互矛盾的陈述之真理性不能同时并存。
新批评派反对“相信中出真理”的理论。首先,他们坚持认为诗歌真理并非一种“无客体”的心理反应有效性,而是一种对客体的特殊知识。诗的价值不是感情性的,而是“认知性的”(cognitive)。如果一首诗是真正的创作,它就是我们以前未能得到的知识,而批评的职能就在于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完美的知识”。这是新批评派反复阐明的一个立场。所以退特骄傲地说浪漫主义诗辩只是抵抗科学,而新批评派证明的是诗在进行与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活动。
但诗歌究竟如何表现这种对客体的特殊知识呢?为什么诗的不符合实际的语言不是“谎言”呢?在这个问题上新批评派“内部”又出现另一种分歧。兰色姆认为这种表现真理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科学,是因为科学的抽象使世界失去了血肉,只剩一副骨架子;诗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具体性,诗靠这种具体性把血肉还给世界。因此兰色姆把他的文集题为《世界的肉体》,并且认为“美就在肉体”。布鲁克斯解释道:“文学给我们的知识是具体的——不是概括事物,而是一种对事实本身的特殊的关注。”这个解释符合兰色姆原意。
但是,如果诗歌真理仅在于其具体性,那么新批评派不过是回到柏格森的立场:“艺术不过是对于实在更为直接的观看”。兰色姆承认他对诗歌真理的看法来自柏格森:科学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只与一般打交道,因此科学反映的是片面真理。艺术则是与具体打交道,它反映具体真理。退特也用柏格森的术语,称诗歌的具体真理为“质的知识”,与科学的“量的知识”对立。
其实这种思想更源自康德。康德明白宣称:“我们有一种纯审美判断能力,靠了它我们可以判断形式,而不靠概念的帮助。”
事实上,文学真理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从希腊古典文论起,西方文论家和美学家就被这问题困扰着。柏拉图认为客体模仿理念,而艺术模仿客体,因此艺术与自然隔了三层,艺术中真理性最少;而亚里士多德正相反,认为诗接近真理:“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要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物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这是后世“典型论”之类古典主义的文学真理观的出发点。例如维柯就认为:“诗歌真理是哲学真理,具体真理(physical truth)若与之不符,应被视为错误。”
而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只道出真理的一半。不少新批评派渐渐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两者的结合使诗歌具有一种真理性。艾略特的“感觉性融合”论是新批评真理观的起点。他的看法我们将在下文(第三章第四节)中详细讲到。他们渐渐理解到诗歌真理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这样,新批评派实际上就从柏格森的立场开始走向黑格尔的立场:“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看。”
新批评派关于诗歌真理的论证,实际上串结起新批评派的全部主要理论。正如布鲁克斯所指出的:“我们对结构的关心,来自我们对意义结构的关心。”
以上讨论可视作新批评哲学基础的一个粗略的引子,从下节起我们将逐点讨论新批评理论的细节,到第三章结尾时再来回顾新批评派对文学作品基本特征的理论之成败得失。
应当说明的是,瑞恰慈本人的看法也在渐渐变化。1931年他自辩说:“拟陈述”指的是诗歌并非陈述,而不是说诗是假陈述,到1934年他又把诗歌定义为“最全面的言语形式”。新批评派欢呼这是瑞恰慈认错,“离开实证主义”而与新批评派会合。
(第三节) 本体论
兰色姆1941年的《新批评》一书逐个检查了先前各种关于文学特异性的理论:道德论、感情论、感觉论、表现论等,认为都没有解决诗歌与科学的分野问题。该书最后一章题为“征求本体论批评家”,谁应征呢?他自己,他在之前六年,1935年,就提出他主张的是“本体论批评”。这个奇怪的自作广告典型地表现了新批评派的自信。
“本体论”(ontology)是个哲学名词,它原是十七世纪唯理论者为证明“存在本质”(神性)的终极真理性而引入哲学体系的。康德认为“物自体”在经验之外,无法认识,因此他反对本体论研究。但到后来这个词被一般化了,变成哲学中关于存在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的研究,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就被现代研究者分成了本体论和认识性两部分。现代哲学如新实在论、现象学等都讨论本体论,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认为没有超越象征媒介之外的实在,坚持康德的反本体论立场,但其他新康德主义者也开始谈本体论,本体就是哲学中第一性的,无须证明而自我清澄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