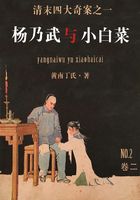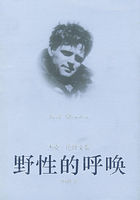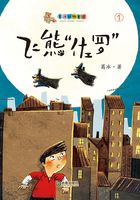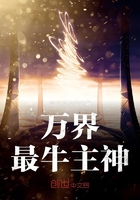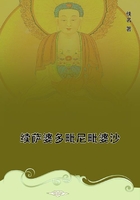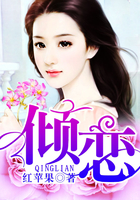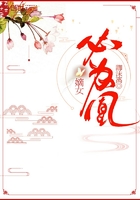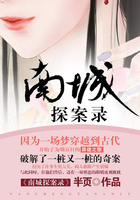来源:《清明》1998年第02期
栏目:短篇小说
大风。气温骤降。冬天真的来了。
天是灰色的。树是灰色的。房子是灰色的。人也是灰色的。在这样的天气应该洗个澡。可是学校澡堂今天不开放。明天也不开放。后天呢,后天也不开放。要洗澡得等到下个星期二。
姚夏感到浑身上下都很难受。
认识姚夏的人都说他有洁癖。一个男人住的房间竟然收拾得那么干净。其实只有姚夏自己知道那些角角落落里有多少灰尘。姚夏觉得最脏的是自己。成天灰蒙蒙地活着,哪怕是洗了澡也没有用,很难找回那种洁净、清爽的感觉。澡堂里总是那么多人,你洗澡的时候总是有两三个人等在你身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你在水龙头下搓洗赤裸裸的身体。换衣室里也是人挤人,不时有人蹭你一下,这样的肌肤之亲留下的是一种滑腻的感觉,久久驱之不去。
昨晚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伊凡在法庭上说:“……谁不希望父亲死呢?……”
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德末特里“无辜”被判刑,斯麦尔佳科夫畏罪自杀,伊凡因内疚自责而精神错乱,阿辽沙弃家远行……最后的审判到来的那一天,谁敢在上帝面前说:我是无罪的?
姚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早晨醒来,房间里的灯还开着。
昨夜恍惚中听到老鼠啃啮书箱的声音。恐怕这不是梦境。那些原是用来装方便面的纸板箱,老鼠要咬穿它们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人类在进化,鼠类也在进化,老鼠们的牙齿想来是愈加尖利了。
姚夏想得赶紧去商店买个捕鼠夹。
姚夏就是那个在今天还一门心思想当作家的人。
姚夏很早就想写一个中篇,名字都想好了,叫做《恐惧与激情》。生活中充满着让他恐惧的事物,也充满着激情。姚夏觉得自己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构思。只等写作激情降临,几万字的中篇就可一气呵成。等待,等待,等待了一天又一天,激情总是杳无踪迹,这才是生活中最让人恐惧的事情。以往总是在秋天,姚夏的创作冲动最为强烈,可是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了,冬天已经来临,姚夏还是每天坐在桌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仿佛心灵正进入冬眠状态。
姚夏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黑人摇滚乐手,穿着的汗衫胸前写着:Dance or Die。姚夏想自己也真该穿一件那样的汗衫,只是胸前的字要改一改:Write or Die。
要命的是现在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姚夏又找出莎莎过去的信来看。
姚夏一直在想:莎莎到底算一个怎样的女孩呢?好女孩?坏女孩?似乎两者都不是。
但是无论如何,莎莎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特别是当她穿着那件红毛衣的时候。许多年之后,姚夏也许会把他和莎莎之间发生的许多事忘掉,但他会永远记住那件红毛衣。他想。
那是冬天里难得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莎莎的房间里。带着暖意的阳光透过浅蓝色的窗帘照进来。阳光没有照在莎莎身上,但姚夏还是感受到了那件红毛衣上发出的热力。后来姚夏就把莎莎抱在怀里了。
莎莎是姚夏妹妹的同学。有一段时间妹妹小颖总是在姚夏面前提到莎莎。小颖说,你一个人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怎么找得到女朋友?于是那年寒假,姚夏就认识了妹妹的同学莎莎。除了失败的初恋,莎莎是第一个和姚夏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孩。那天在莎莎的房间里,姚夏抚摸了莎莎那头黑发,然后吻了她。那一次姚夏的动作有些粗鲁放肆,而莎莎并没有生气。
为什么在内心深处你一直以为莎莎不是一个纯情女孩呢?
星期天一直下着小雨,直到傍晚的时候雨才停。姚夏和冯湄一起去了湖滨公园。
公园在郊区,游人很少。凉风一起,游人就更寥若晨星。剩下一个很大的湖,给人浩渺无边的感觉。日之夕矣,姚夏和冯湄环湖而行。湖的西岸一片荒草连天的景象。整洁的林荫路消失了,一条土路坑坑洼洼,仿佛没有尽头。姚夏感到掉进了一片无边的黑暗里,远处万家灯火,处处笙歌的城市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永远无法抵达。如果这时候碰上一个剪径之徒怎么办?
姚夏说:“那我就只好与他拼了!”姚夏想如果刚才有几个歹人一拥而上,又一个个身强力壮,一个家伙看住我,其余的像恶狼似地扑向冯湄……
“你放心,那我就去跳湖。”冯湄说。
姚夏感到心里的某个地方被什么东西忽悠地扯了一下。那不是心旌摇曳,而是实实在在的痛。姚夏想自己有一天也许会死于心力衰竭。这很好,我们毕竟没有生在战火连天的波黑,也没有生活在动荡不已的中东,我们难得会死于非命。
看着冯湄在前面走,姚夏告诫自己:不要愤世嫉俗。愤世嫉俗是幼稚的表现。
回去的路上冯湄买了一只气球。那是一只充了氢气的气球。它使劲地昂着头,如果没有绳子系着,它会飘向哪里呢?——呵,它飘不到哪里去的,头顶上的天花板会挡住它的前程。一只可怜的、宿命的气球。
冯湄一松手,它向上飞去,很快便被天花板挡住了去路。它就那样可怜巴巴地匍匐在天花板上。
隔壁音乐系的方明在叫:“姚夏,电话!”
姚夏慌慌张张地跑过去接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姚夏听到方明叫他接电话,心脏就慌慌地狂跳不已。
遇上点什么事便人仰马翻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姚夏在心里骂自己。
冯湄从来不问是谁来的电话。
姚夏说:“是我妹妹来的电话。”
冯湄问:“哪个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