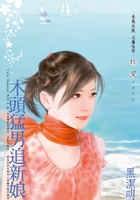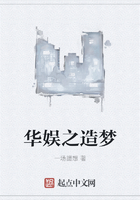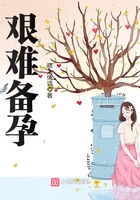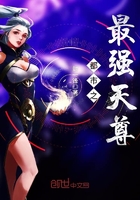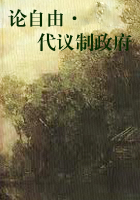来源:《凉山文学》2017年第03期
栏目:小说
从县城隔着蜈蚣河谷看对面的东山梁子,有一条顺着山势盘旋缠绕的机耕道,把桃子坪、拉和沟、马桑坪三个公社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营盘、寨子给连在了一起,然后从日比德垭口翻过山梁通向80公里外的安科区,让人觉得这些地方交通挺方便似的。实际上,当年蒋博在这儿教书的时候,只有在农忙季节前夕,政府要组织支农物资下乡,或者秋收之后要拉公粮入库了,养路段这才忙着找些村民来平路。这些临时找来的“养路工”拿的工钱很少,又没有“上岗证”,就把修路保畅通这样的大事当成是在生产队修饬修饬田坎沟渠一样,随随便便就近取土将路面上的大坑小凼垫一垫,把路中间的“鱼背脊”铲一铲,能使车子吭哧吭哧地通过就行了。因此,除了这时能看见车子跑外,平时大部分时间通不了车,反倒成了一条人走马驮的大道。
蒋博1982年7月师范校毕业分回了屯子县。看在他父母二十年如一日在县内最偏远的力瓦区教书的份儿上,县文教局终于开了下恩,改变了原拟分配他去安科区的方案而照顾到了东山梁子桃子坪中心校教书。
到桃子坪一段时间后,蒋博很快就适应了,感觉到确实比父母教书的地方要好得多。首先是进城方便。星期六放学后,三几个年轻人邀约起,走过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县城感受感受当城里人的味道了;而从力瓦区到县城,那是近百公里的山路,蒋博父母没有特别的事情一年进不了一次城。其次是供应优待。虽说每月三十斤口粮仍有粗粮、细粮之分,但比起力瓦区把面条、灰面等同大米一样都当成细粮,粗粮卖的包谷米米或苦荞颗颗而言,城关粮站供应的细粮只是大米,面条和灰面则变成了粗粮。再次是气候暖和。力瓦区上是一个在六月天也会突降鹅毛大雪,平时连蚊子都不长的地方;而桃子坪海拔千米左右,种水稻、产蔬菜,特别是一个冬天过完了,蒋博的耳、手、脚没再像在力瓦生活时长满了冻疮。这些都让他感到很满足。
屯子县位于大凉山的边缘,乌蒙山区腹地,奔兀耸切的峡谷峻岭乃是大自然不停洗涤雕刻的盆景。虽经几百上千年的朝代更迭,除金沙江沿岸有两三个码头小街外,县治内却一直没有形成统辖、辐射一方的大小集镇,现在县、区、公社三级的所在地,大多是解放后人民政府择地修建挂牌而成。桃子坪公社就是这种情形。党、政、工、青、妇和供销社、信用社以及农机站、农经站等都挤在一个占地两三亩大的院内,两横一竖三栋房子全部就安顿了。院外左侧是公社卫生院,右侧就是蒋博所在的中心校了。除这些公家建的房子外,附近连个卖凉粉儿的小摊子都没有。
蒋博从小在家中洗衣煮饭惯了,生活自理不成问题。只是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也喜闹不喜静,从读中学起就过惯了集体生活,现在当老师了,上课和学生在一起还可以,而放学后,一个人就感到寂寞了。
很快,蒋博和卫生院的李医生熟悉了。李医生叫李且,削挑身材,清癯脸庞,上嘴唇一排齐整的八字胡,于雅儒之中透着时尚。那时,粮、油、肉类统购统销有计划,每一位城镇居民每一个月只有两斤肉的指标。但公社一级从农民手中统收肉、禽、蛋等上交够了任务后,自己也可提留一部分,用于接待客人和过节时供应本级职工。当然平时接待的毕竟不多,一年也只有两三个节庆,常常是公社机关食堂以各种理由将这些给拿走了。因此,一般来说除了大院里的人可以搭伙外,其余的是不行的,比如说学校的老师,但李医生例外。
李医生在卫校主要学的是五官科,而到了这一人一院的公社卫生院,只好内外兼医,甚至连妇产科都要干,蒋博就有好几次陪着他去村民家中接生。他态度好,医术也不错,在当地颇有口碑,时常有人向其带一些时令瓜果蔬菜,偶尔还有抱个公鸡,拿筐鸡蛋什么的。乡下人朴实,他送东西来你不收是会生气的。自从二人成为朋友,卫生院便成了蒋博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每每有意料中的惊喜。李医生总会拿出特意留着的腊肉呀、鸡腿腿呀,或者水果呀,花生呀之类的让他独享。有一次,蒋博还在上课,李医生带口信叫他放了学就过去。等蒋博急匆匆跑来,李医生提出一个平常挑水的锑桶,笑吟吟地向他眨眨眼。他揭开盖子一看,是半桶煮熟了的鸡蛋,怕有五六十个。李医生说,今天我们两个把它干掉!蒋博大喜,两人围着桶就开吃。但鸡蛋虽好,那也不能过量,蒋博吃到第六个时,就再也咽不下去了。害得他不仅当天恶心打干呕,而且一连好几天,只要一打嗝,嘴里就是一股浓浓的鸡屎味。这情节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记忆犹新。
时光飞逝,一晃到了83年3月份,李医生要调去区卫生院当副院长了。听到这个消息,蒋博一方面为好友高兴,区公所和县城建在一块儿,到区卫生院实际上就进城了,这是乡下工作的人梦寐以求的;另一方面也感到失落,两人以后在一起的时候就少了。李医生劝道,虽说不在一个地方了,但仍然可以常来常往。再有就是接任的杨医生,这人好处,相信和你也会成为朋友的。
不久,李医生走了,杨医生来了。
杨医生叫杨光,二十七八年纪,个头和李医生差不多,也留着八字胡,只是肤色要黝黑些。经李医生介绍,蒋博和杨光也很快变成了朋友。杨光性格开朗,好交朋友,不管大人、小孩,都能找到共同语言,不多久点便与团邻四近混熟了。他心灵手巧,凡是木工、电工、泥工这些出自手上的活路,一看就会,一弄就精。三十多年前沙发属于稀罕物鲜有地方卖,即使有卖的也买不起,于是很多家庭纷纷自己买料自己做,一时蔚然成风。那时造的沙发没有现在的样式繁多,通常是一个长沙发加两个单人沙发,需要的建材有:杂木半方,棉絮四至五床,坐垫弹簧四十双,靠背弹簧四十五双,麻布口袋十二至十五张,以及麻绳和大、中、小型铁钉若干。杨光有次到一个朋友家玩儿,见其正在打沙发,便当了两天帮手,回到单位后,依样画葫芦地舞了起来。
还别说,他这样捣鼓了一阵,沙发越做越精致。衡量手艺好不好的标准,首先看整组沙发各部分之间大小和高矮的搭配是否协调成比例;再次看沙发的棱角是否分明和平直;最后还要看坐垫和靠背表面是否硬实一致。如果达到了协调、平直、硬实,那么所做的沙发就是顶呱呱的了。而杨光做的不仅达到这些标准,且还省时间,少用料,有造型。县上的,特别是卫生系统的闻讯后争相来请,一时间比当医生的名气还大。他来桃子坪,不仅把做沙发的名声带过来了,还引出了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