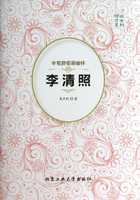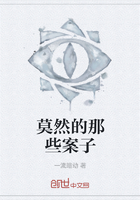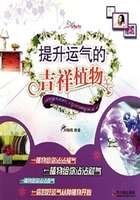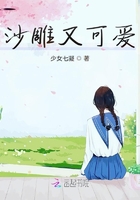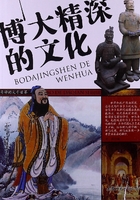来源:《南方文坛》2017年第06期
栏目:文坛钩沉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1993年4月5日,“张光宇艺术回顾展”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展厅开幕,满头银白、76岁高龄的张仃在众人簇拥下,现场讲解,如数家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之后在“张光宇艺术研讨会”上,张仃首先发言,开门见山指出:“当代中国伟大的艺术家张光宇先生逝世30周年,但他的艺术还没有被社会充分认识,没有得到弘扬,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欠张光宇先生的账!”说到最后那句话时,老人声音有点哽咽,全场肃然。接下来,张仃质疑迄今为止中国现代美术史讲述的一个大漏洞——“主要篇幅叙述正统艺术与艺术家,中国画、油画、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而大批杂志画家很少接触。张光宇以及一批老艺术家的作品深入千家万户,其社会影响之大,较之中国画油画有过之而无不及。”[1]
通过张仃,我知道了张光宇;也是通过对张光宇的研究,我对中国现代美术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所了解,为自己的无知羞惭,也为历史的“不公”而困惑。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张仃已停止漫画、装饰性绘画创作多年,正尽全力于焦墨山水的艺术探索,变成一个“国画家”。然而,他依然念念不忘张光宇。
事实上,自张光宇逝世以来,张仃一直魂牵梦萦,不能忘怀,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那样:“在逝去的故人中,人与作品最令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张光宇了——他逝去二十年,恍如昨日。一方面感到他不在,生活中失去了极为重要的砝码,一个合成因素,无论是友情、艺术、事业……意识到失去的是真实的,无法弥补的;另一方面,光宇又似一直存在,他与他的艺术影响,一直在起作用,有如陈酒,愈久而愈醇,活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句虚话了。”[2]东北汉子的张仃,很少写这样缠绵的文字,足见张光宇在他心中的分量。严格说来,张仃与张光宇属于两代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一南一北,文化背景大不相同,论政治身份,一为民盟,一为中共。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如此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今天的“我们”,到底欠了张光宇什么样的“账”?所有这些,都是本文想追问和探讨的。
在《亚洲的骄傲》一文中,张仃这样回忆他与张光宇相识的经过——
1936年我17岁(实际应为19岁——笔者注),因参加进步活动入狱,刚从监狱出来。一无所有,靠画谋生,但屡被一些漫画刊物退稿。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十分活跃。我在北京见到张光宇画的《十日谈》,凭直感相信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他的漫画政治性很强,专攻打偶像。主要矛头直指蒋介石和日本人,很有勇气。手法模仿珂弗罗皮斯,丑化对象好极了,很有装饰性。与张光宇思想和趣味投合的自我感觉,使我开始向张光宇办的漫画杂志投稿一试。我将《买卖完成了》和《春劫》两幅漫画配合一篇短文一并寄给他后,也并没有把握。一天,我在南京开架书店里偶然见到这些漫画出现在张光宇办的杂志上。张光宇为这组漫画制了铜版,并加标题列在“全国漫画名作选”内。张光宇一次给我15块银元的稿费是我给报馆画画的月收入的总和。我敲开了张光宇的门。叶浅予即是看了这组漫画后知道我的,我们在南京一见如故。鲁少飞也来信约我为他主编的《时代漫画》画封面。继我的《皇恩雨露深》和《同志》等作品之后,我在“时代派”的杂志上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漫画,竟有30块银元的稿费存在张光宇处。抗战爆发后,我到上海,由同学韩烽陪同找到时代图书公司。张光宇一见我,就从里屋高兴地迎出来说:“原来是个小赤佬![3]我还以为你是东北大汉,原来是个小张学良!”当晚他打电话约来叶浅予、鲁少飞、胡考等人相聚通宵。当时张光宇是时代图书公司的经理,更是中国漫画的奠基人,很有名望。第一次见面,他却是这样平和爽快。[4]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张光宇与张仃素昧平生,在他尚未出道,处境十分艰难时发现了他,提携了他,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质的飞跃。当时的张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介“京漂”,卖漫画插图为生,寄居在南京城外的一座破庙里,每天为吃饱肚子到处奔走,晚上在烛光下画画,有时穷得连蜡烛都买不起。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父母赋予的姓名“张冠成”改成了“张仃”,孤苦伶仃的“仃”。值得说明的是,文中没有说明的“屡被退稿”的那家刊物,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左翼漫画杂志,叫《生活漫画》[5],主编黄士英,上面经常发表左翼漫画家蔡若虹、张锷等人的作品。这家杂志因进步的倾向和严肃的内容得到过鲁迅的赞扬和支持。自以为是左翼的张仃,挑了两幅自己满意的作品寄去,一幅揭露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当局,鱼肉中国人民,另一幅表现农民暴动,没想到全退了回来,连个说明也没有。张仃惶惑了:我不也是左翼的吗?何以遭到拒绝?不发表作品,没有稿费,何以生活?困境中,张仃将画稿寄给了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张光宇是当时上海自由漫画界的领军人物,正与其弟张正宇一起主持上海最大的出版公司——时代图书公司,后台老板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同时出版五大期刊:《时代画报》(叶浅予主编)、《时代漫画》(鲁少飞主编)、《万象》(张光宇、叶灵凤主编)、《论语》(林语堂主编)、《时代电影》(席与群主编)。张仃在北京私立艺专读书时,喜欢读张光宇《十日谈》上的漫画,对其高超的艺术手腕很是佩服。说实在的,把画稿寄给张光宇主编的刊物,张仃心里并没有底,这位来自东北的毛头小伙子,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的艺术潜力。然而张光宇一眼看中了张仃,就像伯乐相中了千里马。由于张光宇的提携,张仃在中国漫画界一举成名,其结果,就像叶浅予形容的那样:“张仃这个名字在30年代初露头角时,漫画刊物的编者们好象发掘到一座金矿,舍得用较大篇幅发表他的作品。”[6]
笔者曾当面请教张仃:“既然你那么崇拜张光宇,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向他投稿?”张仃这样回答:“当初自己比较幼稚,认为只有左翼是为劳苦大众的,自己虽然很喜欢张光宇的艺术,相信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但又觉得他是在用自己的本事为资本家服务,他经营的时代图书公司,后台老板就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邵是大买办盛宣怀的女婿,鲁迅先生讽刺过他,这对我也有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是自己犯了左派幼稚病。”
张仃敲开了张光宇的大门,给他带来复杂的后果:在上海漫画界一炮走红,使他获得了安身立命的资本,而加盟以张光宇为核心的自由漫画家团体,给他打上了一个灰色的政治烙印。两年后,张仃满怀热情投奔延安,却受到冷遇,后来执教鲁艺,被当作另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视为“党内民主派”,一再受到警告;直到“文革”抄家,红卫兵小将逼他交出所谓的黄色漫画。所有这些坎坷,都可以追溯到这段经历。
七七事变后,在同仇敌忾、全民抗战的氛围中,张仃带领抗日漫画宣传队,辗转西安、榆林、内蒙古,最后去了延安,张光宇去了香港。这一人生的分道,对于两人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仃因投奔革命圣地,以自己的才艺服务于革命事业,后来又加入中共,因此获得组织的信任。张仃日后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席艺术设计师,出国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接管旧国立北平美专,任中央工艺美院的业务副院长、院长,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然而,有一个插曲不能不提:1940年9月,应国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聘请,张光宇偕丁聪、徐迟等人赴重庆中国电影制版厂任场务主任。而此时,正是张仃到延安后最苦闷、最彷徨的时候。鲁艺执教一年零四个月,动辄得咎,画几张变形的肖像漫画,被说成是丑化革命同志,请单身汉同事吃顿牛肉,被说成是拉拢群众,甚至连喜欢毕加索的作品,也成了大家的笑柄,最后不明不白地被下了课。桀骜不驯的张仃,如何忍受得了这种屈辱?得知张光宇到重庆的消息后,张仃马上作出决定:投奔张光宇,办一本《新美术》杂志,介绍解放区的美术创作。
关于这次重庆之行,张仃这样回忆:“尽管从延安去的人都带有某种‘危险性’,张光宇并不避嫌,热情接待我们,对出《新美术》推动美术事业的想法也很支持。”[7]当时他们一起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宿舍里,天天聚在一起,聊艺术,有机会还去中苏友好协会画素描。真是一段难得的黄金时光[8]。作家徐迟记录了张仃的诗人气质和叙事的艺术才能。一个晚上,两人相对而坐,一个谈,一个记,陶然相醉,忘了时间:“他先谈了一连串的长白山的森林故事,熊瞎子的,东北虎的,以及身穿红肚兜的小孩在林中跳舞,用木棒子一打,她往地里一钻,然而刨开那地,可以挖出人参来。我听了,记录了,情绪逐渐高涨。接着。给我讲了一家三代的故事,也许可以说,这就是他自己的家史了,这段故事他谈到深夜还没谈完,第二天又接着谈,又谈到深更半夜,我记了满满一本笔记本,简直精彩极了。”[9]
一张历史老照片,见证了那段愉快的时光,那是张光宇、张仃、丁聪、胡考、特伟的合影,背景是重庆中国电影制片的布景棚,五个艺术家随意而处,个个神情自如,一派潇洒,看上去像一张舞台艺术剧照,其中张仃坐在地上,两腿舒展,笑得灿烂。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形势骤然紧张,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纷纷离开重庆。据张仃的回忆: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他来不及同张光宇告别,就带着艾青、罗烽回了延安。张光宇与丁聪、徐迟不久绕道缅甸回到香港。《新美术》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