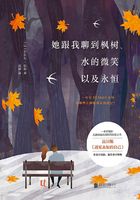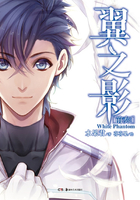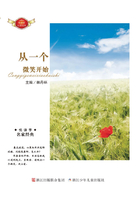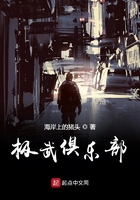来源:《清明》2003年第02期
栏目:中篇小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地人只知道天津卫有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但久居天津卫的人都知道,天津卫除了那三宝之外还有一宝——少爷。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会儿,“少爷”在天津卫那可是响当当的一道“名胜风景”。那年月,大报小报天天都有少爷的新闻,有一大户的少爷就曾放过话,说全城的报业应该给少爷们颁发“荣誉奖”,否则,全城少爷们联合沉默不语的话,报社就得关门。为嘛?没了新闻。当然这话是说大了点儿,可也没辙,谁让天津少爷们就爱说大话呢。少爷们不仅爱说大话,还爱干一些露头露脸的大事,而且还一个少爷一个脾气。谁的脾气大,谁的老子钱多,谁就能折腾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为什么少爷们能造出那么大的架势来呢?关键在于富贵人家把发家的重点都放在了少爷身上,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家业才能兴隆不衰。这么一来,少爷们的“点儿”是越来越高,因此在天津卫,少爷们的故事,不论是哪朝哪代,都是引人入胜的。
鲁文天鲁少爷出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出生时,正是家道兴旺的时候,他爹又是中年得子,而且生出他之后,他娘便再没有生养成,所以鲁文天一落地,就是锦衣玉食,宝贵得不得了。活到了二十四岁。千宠百娇的鲁文天鲁少爷弄得一身的猴性。就是这样,他爹还给他找词呢,我儿子是腊月生的——天生就该是动(冻)手动(冻)脚的。爱折腾就折腾呗。
鲁少爷的猴性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讲完的,他几乎天天都能弄出几个段子来。不是今个儿把德国造的自鸣钟捣弄坏了,就是明个儿猛吃黄豆猛喝凉水,然后挨屋去放臭屁,弄得鲁家的下人老妈子们捂着鼻子乱跑。还有一次更甚,用夜壶沏茶,甭管谁来了,抱着夜壶冲着客人“吱儿吱儿”地啜饮有声。最后鲁老爷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顺手给了他一拐杖。这可了不得啦,他当着满屋的宾客,咧着大嘴,龇着一口小黑牙,学他妈坐起了“地泡”。没有办法。在外人面前一向拿腔作势的鲁老爷还得反求他,谁让鲁家千顷地就这么一根独苗呢。
鲁少爷自小吃精米白面,可却长了一口小黑牙,黑得让人起鸡皮疙瘩,再加上大背头,那长相真是让人过目不忘。在他爹的商业圈子里,鲁家的这个“宝”比他爹在经营上的老奸巨滑还有名气。从小长这么大,人家孩子除了玩儿就没干过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儿。听戏养鸟打茶围,吃喝嫖赌样样熟,听一声蛐蛐叫,就能知道是山东宁津的外埠货,还是天津卫老地道外棺材里蹦出来的本地货。
鲁少爷玩,那是他有供着他玩的资本,他爹鲁作民是天津卫有名的诚洋纱厂的大股东,股份占了百分之三十。要知道百分之三十到底是多少钱?反正算不好,这么说吧,诚洋纱厂有八万纱绽,这八万纱绽一转,三十个人点钞票,一天点不完。只要诚洋纱厂的机器动一天,就够鲁少爷打滚造一个月的。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小日本抓紧了在中国的经济垄断,尤其是对棉纱业的控制。就拿天津的棉纱行业来说吧,一九四二年新年的钟声刚敲过没俩月,已有裕元、恒源两家纱厂倒闭了,而在华北一带赫赫有名的北洋纱厂也是负债累累。人们都明白,这是小日本暗中捣的鬼,他们通过种种手段,造成棉贵纱贱的市场格局,致使一大批纱厂陷入困境,然后日本人再逐一进行收购。甭看每天大街上小日本鸣着警笛抓人,可在商战上却行迹诡秘。大凡有点民族感而不想投靠日本人的棉纱业大户们,把个小日本恨得牙根儿痒痒,但却又都无计可施。因为日本人打商战从不自己出头,所以棉纱业大户们想应战都找不到一个具体的靶子,只有急了的时候骂上一句“我操所有小日本”。
一九四二年的鲁家,也是风雨飘摇。
这天,鲁文天鲁少爷跨出东马路自家的朱红大门槛时,一脸的茫然。今儿个干点儿嘛去呢?他鲁少爷胡造的日子在一九四一年底就已经是旧话了,日历牌一掀到一九四二年,满天下的人都知道了诚洋纱厂快撑不住了。这大户人家别看平日里进账不少,可一旦生意“折”了,不仅本利无收,最惨的时候,就是卖房子卖地也填不上那个“窟窿”。天天忙着收拾残局的鲁作民再也顾不上宠他的宝贝儿子,任鲁少爷怎么胡缠,能要出的钱是一天比一天少。昨个鲁少爷去劝业场大罗天玩时,一进天纬球社,身穿红背心的领班就对他说,上个月的账还没清呢,这个月您老不能再记账了,一律现钱,付了钱,就开局。过去,谁敢跟鲁少爷这么说话,他去天津卫嘛地方口袋里带过钱!都是记账,月底到鲁家账房去结。如今落到这份上,真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
时下正是初春,满天飘扬着白绒绒的柳絮。刚刚迈出门槛的鲁少爷要是搁平时,准会蹦出一句群英后妓院大老鸨小李妈的一句口头禅“这不跟大姑娘的手一样吗”,可这会儿,鲁少爷一点情趣也没有,他把沾在眼睫毛上面的一朵柳絮一巴掌胡噜下来,骂了一句脏话。
干嘛这么大火气?说这话的人操着一副公鸭嗓,十个人听了准有九个半会皱眉头。可鲁少爷一听却打心眼儿里乐了。真是天降救兵。
臭小子,你打哪个旮旯儿里又蹦出来了,我可想死你了。鲁少爷冲着那人嚷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