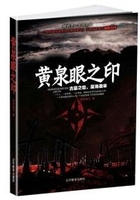在“人间”,苏阳有一个五脏俱全的家,和大多数奔忙于上下班齿轮之间的工薪族一样,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对这个世界的指望在消失,最后,感觉到自己一直是在靠巴结芸芸众生而活着。苏阳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八年,身边有一个用了十八年的时间把他塑造得无比矮小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高大的妻子,有一个把童年典当给上下课铃声的女儿。妻子是初中数学教师,虽然个头矮小,但有一个匀称的体型和一张摆放整齐的脸,还算漂亮。十八年,光阴按揭的是付给生活的利息,一个漂亮的女人在苏阳眼里却逐渐丑陋起来,丑陋得几乎成了一个坏人。他总是在心底暗暗使劲,可十八年了,似乎也想不出一句最有力气的话来作临门一脚的反驳,只能是无数次还没开始发作就苦笑着败下阵来。有时候他想说,王晓静你他妈的就是一个小人,你用无比下作的手段来维系这个家庭,让一家三口真的像别人看到的一家三口一样,你内心的幸福藏着你自己不愿意揭发的真相。有时候他想说,王晓静你真的不配大模大样地行走在人群中,你需要的一切,恰恰是别人不齿的;你假装不在意的,恰恰是你最在意的。王晓静你为什么一点也不觉得累?你每天在一个只有三个人的世界里咆哮,你每天都看见你的理想离你越来越远,你每天都在伸出一双手问这个世界索取你所需要的东西……王晓静啊王晓静,你为什么做不到真正的目空一切?
王晓静看他的时候,总是透着一种无比轻蔑的眼神,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只苍蝇也比苏阳值得世人关注。当然,苏阳比不上一只苍蝇,是十八年之后,之前并不是这样。王晓静再漂亮,也只不过是百里过半,哪能像当初的苏阳,随便往大街上一站,掏一根火柴点一支香烟,就有很多女生从眼睫毛里偷看,那是百里挑一啊!农村孩子能把自己带离罗圈腿、包谷嘴和少年白,真不容易。二十二岁的苏阳站在文体局灯光球场的大门外,迎面走来二十二岁的王晓静。二十二岁的苏阳命犯桃花,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当时真的不该得罪跳舞跳得最好的肖若曦,也不该对唱歌唱得最好的陈可可恶语相向,他在人群中摸过王晓静的头,就被王晓静赖上了。文化馆馆员同时又是凤城篮球中锋的苏阳走到哪里,数学教师王晓静就跟到哪里。爷爷说,这姑娘矮啊,你要想清楚。苏阳笑了笑,说,这样好啊,以后她要是不听话,我就用一只手把她提起来,然后扔窗外去。王晓静笑得风摆柳树干,却只见柳树叶子动。爷爷趁王晓静不在眼前的时候,对苏阳说:“象鼻鹰嘴秃麻雕,晒背驼子莫相交;有话别对矮子说,矮子是个送话包。”最后两句被刚好推门进来的王晓静听见了,她看了一眼坐在床沿上的苏阳的爷爷,没有说话。五年后,爷爷死了,王晓静没有陪苏阳回老家奔丧。苏阳问王晓静,你什么意思?王晓静说,我是个矮子,爷爷不喜欢我,如果我去了,说不定爷爷的灵魂见了我,会迷路的,就过不了奈何桥。苏阳第一次想揍她,但还是没有揍,后来的十几年,苏阳无数次想揍她,也还是没有揍。
王晓静进门,对着躺在沙发上看一本文学杂志的苏阳说,看看,看看,我才半天不在家,这家就成了这个样子。苏阳问,这家怎么了?王晓静顺手将沙发上的电视机遥控器拿起来,放在了茶几上。苏阳想,是不是移动一下遥控器,这家就比之前好了许多?那么,她不在家的这半天,除了遥控器被移动了一下位置,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吧!甚至,他压根就没有动过遥控器。苏阳知道,这个家唯一发生变化的,是姓王名晓静的这个女人。苏阳打了一个下午的篮球回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王晓静说,你倒是活得滋润,你是全凤城的体育明星,文艺骨干,打了这么多年的篮球,排了这么多年的节目,自己却连一个球都不如。苏阳盯着她看了三秒钟,洗澡去了,边洗边想,这女人到底需要我成为什么人物,我又能成为什么人物呢?当初我在球场上飞奔,你王晓静不是屁颠屁颠球场四角转,手掌都鼓出泡来吗?苏阳给上一年级的女儿苏小扣辅导数学,王晓静一把抢过女儿的身体,放在怀中,大声地对她说,你爸是搞体育的,不懂数学。
好吧,我就做一个生活的局外人,有什么不好?苏阳只是在心里和自己开一个玩笑,没想到这个玩笑真冷,他这个局外人就一直做到现在。王晓静说,我要换一套房子。苏阳刚要开口说点什么,王晓静就恶狠狠地说:别说了,咱们这套房子我已经找到买主了。王晓静一个人去看房子,一个人去付首付,按揭贷款的时候,苏阳去签了字。王晓静一个人守着工人装修房屋,一个人给新房的门框贴上了大金字的对联。王晓静说,我们学校吴副校长的父亲过世,多热闹啊,酒席摆了三百多桌,教育局长都亲自赶往吊唁,人家收了五十几万的礼金呢。苏阳刚要说话,被王晓静抢过,说,要是摊上咱们,怕三十桌也摆不上,能收五万块就不错了。苏阳好想问她,咱们家到底是谁死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但没问。
苏阳和王晓静、苏小扣三个人走在大街上,迎面遇上穆兴海和成芹两口子带着双胞胎儿女走过来,王晓静对苏阳说,你看看人家。苏阳和王晓静躺在床上,王晓静问:咱们为什么不买一辆车?苏阳说,没钱。王晓静问:为什么没钱?别人家的男人当乡长当局长,光一年的收入都可以买几辆车,你呢,倒好,当个球,一辈子连奖金是什么东西也没见过。如果王晓静非要拉着苏阳和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如果他们在路上遇到熟人,王晓静肯定会对苏阳说:你看看人家。有一回,他们在菜市场遇到丈夫刚被双规的许平飞,没等王晓静开口,苏阳就说:你看看人家。说完这句话,苏阳内心一阵狂喜,脸上浮现出无比惬意的笑容。“恭喜你成为一个有娱乐精神的人!”苏阳悄悄地对自己说。
进城十八年的苏阳,始终没有给过自己一次发自内心的肯定。十八年后的今天,苏阳仿佛已经成为另一条好汉,提着一根藏在骨头里的哨棒去深山打一只老虎。其实不是,此时的苏阳要去的是一个他没有见过的世外,此时他正行走在绝壁上,尽管大雾散尽,他也只能看见前面三个石阶。
走着走着就什么也不怕了,走着走着他就敢东张西望了。他看见白森森的岩壁下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石缝,石缝里有几所很旧的房子;他看见初秋的大锅圈,有长着麦苗的田地,居然一垄一垄的;他看见放牧在斜坡地上的牛和马,看见炊烟从茅草屋顶缓缓升起。
一直往下走,抬头往上看,天空突然变成一个蓝色的锅盖,四面的绝壁就像即将合上的手掌,把白色的挂着头盖骨的身躯挤在一起。苏阳觉得,自己真的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怨言和冷眼的世界。这世界就像躲在外套里面的贴身小袄,像缝在内裤里侧的口袋,令人想不到,就算想到了,也不愿意把手伸进去。再往下走,石阶没有了,路渐渐敞亮起来,可以看到更远的路的身形,路的两边也稀稀疏疏地长了些低矮的灌木。就在这时,苏阳看见前面的路上有一座小小的房子。
说具体一点,应该是个窝棚。估计除了在大锅圈,你绝对看不到这样的房子。房子建在路上,房顶就是斜伸出来的岩石;外侧的一壁,是两棵活着的树和一堆死去的树枝架起来的,树往上生长,干枯的树枝就被抬起来,下面留下两个椭圆形的孔,却充当了窗户;在进路的一头,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一堵墙,看得见石头与石头之间泥土的颜色。开始,苏阳认为自己应该绕到其他地方寻找往下的路,但他实在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于是推开石墙上那道留着几个窟窿的木门,走了进去。小房子呈长方形,长度不到一丈,宽度只有四五尺。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居然摆放了三张窄窄的课桌和九个木凳子。岩石上有一块不到一平米大小的黑板,黑色几乎快要褪完了,快要还原成石头的颜色了。不会吧!原来这是一间教室。苏阳弄不明白,三张课桌为什么要配九个凳子,九个凳子连起来的长度远远要比三张课桌长得多,怎么摆放呢?就算教课的老师用上一个,也应该多了两个凳子出来。再一看,他明白了,原来地面被石头挡住的地方,刚好生出一个平整的石头台面,刚好可以作为课桌,只是必须向靠右的方向摆放凳子,也就是说,有两个孩子必须在上课的时候扭过头来才能与其他孩子保持一致。石缝里生长出几株细小的毛竹,叶片嫩嫩的,绿得还很耀眼,估计孩子们坐下来的时候,张开嘴就可以衔住一片竹叶。房子的另一头,同样是一扇留着窟窿的木门,推门出去,苏阳就可以继续行走。
路不再像之前那么陡峭,苏阳感觉到自己与大地的距离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于是松了口气,回过头来看看路上的小房子,心想,孩子们正在读书的时候,如果有人要打此地经过,得先把孩子们都叫出屋子,一个个贴在岩石上,人走过了以后才又让他们回到屋子里继续上课。可又想,谁又愿意从这条路上经过呢?除了大锅圈里居住着的人们,大概很少有其他人吧。当然,这是之前,或者说,这是要放在遥远的从前才能成立的假设,因为就在前不久,这个地方曾经因为一个小学校而名噪一时。前些日子,常有人三五成群地来大锅圈,他们带着相机和旧衣服来,带着小袋包装的大米来,也带着无限的好奇和疑惑来,他们来的时候,大锅圈绝壁上的石阶上肯定响起了一阵阵惊惧的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