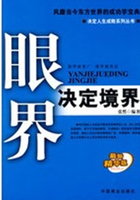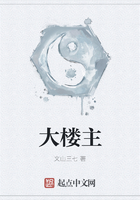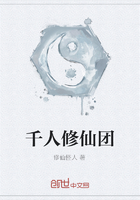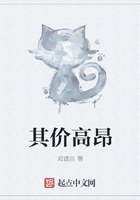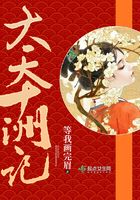来源:《北京文学》2006年第06期
栏目:现实中国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看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至今享受着“工人编制,农民待遇”,没有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四金”。
“医疗器械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进行假治疗,这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她说。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
有人说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有人说她就是中国的“唐·吉诃德”,也有人说她是啄木鸟,在啄害虫。她家的保姆却说:“陈医生是在拿石头砸天。”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她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她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
2006年3月,人民的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
住房,教育和医疗,这是中国百姓最关注的三大焦点。
住房关系着人们生活的质量,教育关系着人们未来的生存状态,医疗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
人,在医院降生,回到医院辞世。医院是生命的始点,也是终点。
佛家认为,人生有四苦——生老病死。这“四苦”都需要医生帮忙解弭。医生在病人的眼里是神圣的,西方将医生誉为白衣天使,东方则将医生视为菩萨。
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在生命的苦旅上,医院是驿站,谁都免不了要跟医生“亲密地接触”。张洁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写道,母亲在开刀手术前,拉着医生的手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在病人的眼里,医生是最亲的亲人,他托付给医生的是生命,生命是一切的平台,失去了生命,权力,金钱、爱情。事业。未来,还有家人的幸福都要归零。因此,不论什么人站在医生的面前都要虔诚、敬服和信赖。不想信赖也要信赖,你别无选择,生命都交人家去打理了,再掖点藏点还有什么意思?
亲人,是需要双方承认才能确定的。不论希波克拉底誓言、《赫尔辛基宣言》,还是中国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都认为,对医生而言,病人的健康高于一切。医生要对得起病人的那份信赖,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医生首先要有慈悲同情之心,决心解救百姓疾苦。若有人求医,不要看他的贵贱贫富,老少美丑,恩怨亲疏,同胞老外,智商高低,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也不能瞻前顾后,先考虑自己的利弊和生命。
“这些医生究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还是撒旦派来的魔鬼?”
在20世纪末,几千年来的信赖动摇了,从没有过的疑惑出现了,病人将医生一分为二,一类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类是劫财害命的“白衣魔鬼”。在“白衣魔鬼”的眼里,疾病就是他的钱口袋和来钱道儿。他们要跟疾病狼狈为奸,密切勾搭。落在他们手里,小病会搞得你倾家荡产,大病让你家破人亡,健全的让你缺少“部件”,残缺的让你支离破碎……
老百姓愤愤地说,“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卖药的并不可怕,只要捏紧钱包死活不撒手,他就干没辙。最可怕的是医生,他说你有病,你没勇气否认;他要你服这药,你不能买那药。有时,你明知那种药药价虚高,医生会得到回扣,还得咬牙买。破财免灾,这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可是,“白衣魔鬼”的逻辑却是破财招灾。他们将谋财害命的游戏已玩到了极致,俗话说:“倒霉上卦摊。”那是自找挨骗,如今是倒霉上医院,那是无奈,有病拽着,不去不成,明知被宰,也要拎着钱袋子自己送上门儿。
who(谁)?“白衣天使”还是“白衣魔鬼”?当病人在医生的对面坐下,心里难免要打鼓。
有的医生委屈地说,医生倒霉就倒在媒体上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败类只是少数,也有医生很客观地说,现有的医疗体制就这样,我们不宰病人,医院就要宰我们,不仅让我们拿不到工资和奖金,甚至要“炒”我们。谁不想当孙思邈、希波克拉底、白求恩,可那样在医院混得下去吗?
天使和魔鬼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就像李逵容不得李鬼。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较量。
正义终归要战胜邪恶,世界不可能划归魔鬼,中国的医疗界也不可能让“百年魔怪舞蹁跹”。可是,人们要记住天使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
为什么要把光量子说成激光?医院怎么可以骗病人?从医28年,陈晓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困惑,这么迷茫,这么痛苦。
1997年7月24日,这本来是个寻常的日子。寻常的日子就像从树上飘落溪流的树叶,打个漩儿就冲走了。可是,这片树叶却滞留在陈晓兰的心里,漂不走了。
早晨6点,她就上班了。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的办公区内还沉浸在梦境。理疗科位于办公区,距院长和书记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她打开门,来苏儿味扑面而来,理疗器械和理疗床像一群乖孩子似的迎接着她。她将它们一一看过后,换上白大褂。在所有的衣服中,她最喜欢穿的就是这白大褂,几十年来怎么都穿不够。女儿说过,妈妈穿白大褂最好看,最像医生。
医生不是演员,不是演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为做好医生,她坚持提前一小时上班,拖后一小时下班。在给病人治病前,医生需要一个心理缓台,来净化心绪。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在工作时间出来的,晚下班一小时,一些病人就可以在下班后来看病了。
“陈医生,x科的医生非让我扎激光针不可,我不扎他就不给我开药,”开诊后,一位老病人上来对陈晓兰说,“光扎一针激光针就要40元,再加上药费就得100多元。激光针扎上后不仅很痛,还浑身颤抖……”病人信赖她,看病时遇到问题都会找她商量。
“激光针,什么激光针,我怎么不知道?”陈晓兰疑惑地问。这时,理疗床躺满了病人,她脱不开身,只好让护士到注射室取一份说明书来看看。
陈晓兰将说明书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据说明书介绍,这种疗法能够降低血黏度,增加血氧饱和度,适用于治疗脑血栓、脑动脉硬化等症,是一种先进的医疗器械。
“那激光针一扎,人就抖起来。”旁边的两位病人说道。
一个病人抖,两个病人抖,怎么病人都抖呢?是输液反应,还是器械的问题7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她给病人处置好,下楼去了注射室。
狭小的注射室弥漫着浓重的臭氧味儿,输液的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坐着。陈晓兰说,她想看一下“激光针”,手忙脚乱的护土抬手指了指:“这就是,”她走过去,弯下腰,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像月饼盒似的器械,那上面有“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几个字,与之配套的是·石英玻璃输液器”,在输液前,先对药液进行充氧,然后让含氧的药液流经治疗仪,经激光照射后输入病人的静脉。
蓦然,她见那盒子上印有“ZWG-B2型”一行字,一年前,在晋升医师职称时,她申报内科。外科或者儿科医师,可是医院却非让她申报医技类医师,申报医技类医师是要考医用物理学的,这对1968年中学毕业,没有学过物理的陈晓兰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她知道,自己得罪了院长,院长在刁难她,她想去找区卫生局讨个公道。“如果你有本事就考出来,没本事就别丢人现眼,怎么那么没骨气,像是跟人家讨饶似的,”爸爸生气地说,“真不像是我的女儿!”说完,爸爸妈妈就不再搭理她了。她只好硬着头皮申报考了医技类医师。参加辅导班学习时,她每次都早早去,坐在第一排。老师在上面画,她在下面画。可是,老师讲的是什么,画的是什么,她都不明白,好在课后爸爸给她辅导,妈妈托人帮忙找一位大学的副校长给她补习。结果,有许多读过医用物理学的医生都没考及格,她却考了86分。
陈晓兰直起身子,当着病人的面对护士说:“这哪里是激光?回家查查字典吧。”说完,转身回理疗科了。
金钱的能量往往是无法估量的,它可以把冷僻变成火热,也可以让火热变成冰冷。如果你是医生,只要在处方上写“激光针”三个字就可以赚钱,在“激光针”的后边写1就可以拿到7元钱,如果写7,就可以将49元畅畅快快地收入囊中,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天上掉下一只钱口袋?对,那些汲汲于捞钱的医生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拼命地向病人推荐“激光针”,甚至逼病人就范,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动地球。”钞票改变了医生的支点,“激光针”在广中地段医院流行起来,在狭小的注射室外病人排着长队等候扎“激光针”。
“你昨天是不是讲了一句影。向医院经济效益的话?”第二天早晨一上班,院长悻然过来问罪。
“没有呀!”陈晓兰莫名其妙地看着院长。
“你是不是讲过光量子不是激光?”
“是啊。”她恍然大悟,“光量子确实不是激光,那上面不是写着‘2WG’吗?那是,‘紫外光’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说着,她拿出书来,跟院长解释道:“激光和紫外光,一种是受激辐射发出的光,一种是自发辐射发出的光,二者的物理性能是不一样的。”
她抬头,发现院长已气呼呼地走了,她望着院长的背影,百思不解,不明白医院为什么非要把紫外光说成激光,难道激光就等于高科技?近年来,激光在普外。心脑血管,泌尿。口腔,妇科、耳鼻喉。眼科。肛肠科都被广泛应用。将“光量子”说成激光,病人容易接受,觉得多花40元钱值得,如果说是紫外光,病人就会觉得物无所值。
可是,紫外光不是激光,医院怎么能欺骗病人,医生怎么能说谎?苦恼会让人思索,思索在不经意间就会推开意想不到的柴扉。药液经紫外光照射后会不会发生药性变化?她疑惑了。“药物可以用紫外光照射吗?”她打电话问老师和上海有名望的医生,多数医生都认为不行。
“光量子”像光阴冲不走的淤泥滞留在她的心头,堵得难受,她是一位行医严谨,恪守规范的医生,为此深受病人的欢迎,写给她的表扬信像春风中飘飘洒洒的花瓣,按医院的规定,医生上交一封表扬信奖励2元钱。她却把表扬信锁在抽屉里,拒不上交,她认为,医生就应该为病人治好病,就应该像对亲人那样来对待病人;不论医生待病人怎么好,只有不够,没有过分。医生给病人看好了病就要受到表扬,那就像赞扬裁缝“非常会做短裤”一样,让人耻笑。
陈晓兰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每天上班后,她除上厕所之外,从来不离开诊室,可是,同事却非常喜欢在她那儿坐坐,她那儿不仅有几张舒适的理疗床,还有她这位乐于助人酌医生。她心灵手巧,不仅理疗室的一些器械是她自己做的,而且同事的雨伞、拉链等东西坏了,她都会一声不吭地给修好,她淡泊名利,在医院。人们往往会为半级工资打破头,她却把两次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她从来不主动讨好领导,也不跟别人拉关系,却在医院口碑极好,每次选先进,她都全票通过,
可是,她却感到自己在医院越来越“水土不服”了,从医28年,她从来没有这么困惑过,这么迷茫过,这么痛苦过。
一位病人死了,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子医生给她开的那瓶药——过期失效的药。面对这种图财害命的医疗腐败,她怎么能够保持沉默?
28年前的上海北站,知青们在跟亲人告别,月台上泪雨纷纷。爸爸、妈妈,奶奶,还有一些亲属簇拥着身高只有1.48米、梳着两只小抓鬏的陈晓兰。大家目光依依,泪水滚落,她刚满16周岁,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门。她感到很新奇,欢心雀跃,喜笑颜开,好似不是去江西安福县插队落户,而是去北京大串联。
“呜——”的一声,知青专列呼啸着驶离上海,车窗外的爸爸,妈妈还有奶奶的慈爱面容不见了,小弟跟着火车跑动的身影也像一片落叶似的刮走了。陈晓兰“哇”地咧开嘴——哭了,蹦着跳着喊着要下车了,带队的老师哄了一阵子,才把她哄住。
车厢情惜,沉沉闷闷,知青满脸黯然。陈晓兰在厕所里,像个孩子似的跳高去摸上面的一根管子。一下,两下,三下,她摸着了,开心地笑了。她出生于上海滩家道从容的读书人家,父母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家里有50多位亲属遍及海外,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文革前,她家不仅拥有一幢三层小楼,还有两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那时,她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当毽踢。
有人吃饭了。吃饭也会传染,本来没什么感觉,突然看见别人吃东西就饿得抓心挠肝了,知青们纷纷从行囊里取出吃的,摆放在茶几上,摆出与这些吃的决战的架势,陈晓兰的行李很沉,可是里边没多少能吃能穿的,有的是榔头、锯子。刨子,规格不同的凿子,什么七分凿、五分凿、三分凿;有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药物,还有听诊器、止血钳和一个布娃娃。
她从小就想像表姨那样身穿白大褂,做一位医生。她最理想的是做外科医生。爸爸说,当外科医生要心灵手巧,不仅能缝缝补补,还要有木工、钳工的手艺。为此,她买了一些木工工具,在家里“吱嘎吱嘎”地锯木头,“乒乒乓乓”地做凳子、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