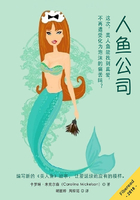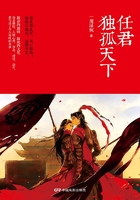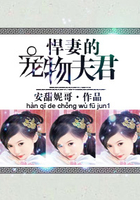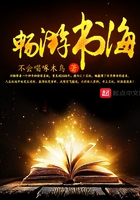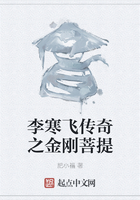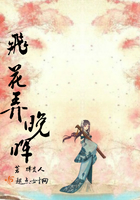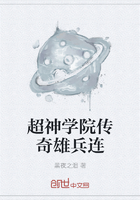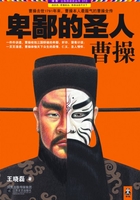来源:《时代文学·上半月》2014年第03期
栏目:中篇撷英
那天我正在开会,出去上卫生间,手机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铃声响了,她的名字被其他人看到了,我回来后有人笑:甜沫?这不是济南人早上喝的粥吗。
甜沫是我同学,严格意义上讲是小学同班初中同级的同学。在我眼里,甜沫从小就漂亮,记得是在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重新调整座位,把我和王晓梅分开了,我和甜沫坐在了一起,甜沫抱着书包来到座位前,手指王晓梅问:“你喜欢和她还是和我坐在一起?”
我看着她闪烁的大眼睛,回答:“和你。”
甜沫回头看着王晓梅大笑:“王晓梅,你输了,你比不过我。”
五十年过去了,儿时绝大多数的记忆都被岁月抹去了,为了官扎营拆迁,我们再次见面,当时甜沫批评王晓梅,不能拆迁办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的要求合情合理,总是愁眉苦脸能解决什么问题?
王晓梅看看我,看看甜沫说:“我怎么能和你比,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输给你了。”
其实甜沫姓田,大名叫田秋艳。田秋艳上面有七个哥哥,她母亲怀胎十月,在家里分娩的时候半天没有动静,急得她父亲在外面直转圈跺脚:“生了吗?”
过了一会儿传来孩子的哭声,接生婆大声喊道:“生了。”
她父亲问:“添个么(济南方言:添了个什么)?”
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着急说话不清,还是因为母亲刚刚力气用尽影响了听力,母亲骂道:“歪蛮儿的(济南口头语),刚生孩子就让我喝‘甜沫’,我要吃鸡蛋!”
一家人都笑了。接生婆在屋里喊:“田大哥你终于有闺女了。”
于是,甜沫的名字伴随着她的哭声来到了人间。
甜沫的母亲之所以对“甜沫”两个字那么敏感,也是有原因的,她从小做甜沫,在官扎营一带,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丫头的做的甜沫格外好喝。
如今丫头已经八十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尽管有七个儿子,但是她住闺女家,说闺女是她的贴心小棉袄,不像儿子动不动就给她力愣(济南方言:耍横)。小棉袄就是小棉袄,甜沫忙,不能亲自照顾母亲,就给母亲请了个保姆,一天三顿饭伺候。但保姆第一天到家,第二天她就把人家撵走了,还批评甜沫不会过日子,说家里有我干活你还请保姆?
甜沫住的别墅,有自己的院子,甜沫雇人专门养花,还从南方买了一些名贵品种,结果甜沫的母亲像电视剧里的石光荣一样把花刨了,种上了辣椒、小白菜、黄瓜、丝瓜,种的最多的是菠菜。说俺闺女喜欢喝甜沫,做甜沫离不开菠菜。她还经常失踪,甜沫就到处找她,最后总是在她以前住的老街道——官扎营找到她,后来甜沫发现母亲不在家就不再找了,直接到官扎营。官扎营街坊邻居都羡慕她,说她有福气,养了一个那么能干那么有钱那么孝顺的闺女。
但是,甜沫母亲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知道自己是谁?甜沫无能为力。你想想,有谁能知道八十多岁老人的故事。这个心愿可能要变成一辈子的遗憾了:甜沫的母亲家是哪里的,父母是谁,姓甚名谁一概不知道。她结婚时,甜沫的父亲问她,你叫什么名字?甜沫的母亲回答:“丫头。”
甜沫母亲年轻时,官扎营就流传一个故事:一年冬天的早上,官扎营毛林子开饭铺的张老板到火车站接货,那是他当兵的儿子从南京给他发来的。官扎营离火车站很近,而且火车站通向官扎营有一个后门,进站出站十分方便。张老板接的是从浦口来的火车,天不亮火车就到,张老板起了个大早来到官扎营通向火车站的后门,他还没有听到火车的声音,就听到门口一个孩子的哭喊,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一个几乎赤裸的女孩子蹲在地上哇哇大哭。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很多,你想管是管不过来的。张老板从女孩子身边走过去,随便看了女孩子一眼,没有想到就这一眼,改变了甜沫母亲的命运。女孩子在冲张老板笑。张老板发毛了,心想这个孩子必然和我有缘,否则不能哭着哭着我一看她她不但不哭反而笑了,我要是不理睬,不但是罪过,极有可能会失去什么珍贵的东西。张老板四下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就把孩子抱了起来,问孩子你是哪里来的?父母哪里去了?孩子一概是摇头。张老板有些担心,不会是残疾孩子吧?张老板问孩子,你多大了,孩子忽然用标准的济南话说:三岁。你叫什么名字?张老板问。孩子回答很响亮:丫头。
当然,这只是张老板自己的一个说法,官扎营的老人还流传着另外一个说法,那就是张老板和他一个相好的孩子,他的相好把丫头生下来养到三岁,由于兵荒马乱,实在无力抚养就悄悄地扔给了张老板。对于这个说法,张老板非常生气,大骂这是“蹦牡根”(济南方言:胡说)。传说归传说,反正张老板放弃了浦口来的货,直接把孩子领回家,原以为家里肯定会大乱,老婆肯定会骂他:一大清早领着一个女孩子回来,谁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私孩子(济南方言:私生子),会不会有什么病?没想到,老板娘看到孩子满脸的笑容,说我给你生了两个儿子,咱家就缺一个闺女,咱就当小狗小猫养着就是,大了还可以帮我干一些家务活,在饭铺干活呢。
于是,在张老板家里,丫头慢慢地长大了。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知道甜沫的母亲是丫环出身,想让她在大会上忆苦思甜,甜沫的母亲说,在张家有吃的有穿的,吃的比现在都好,隔三差五能吃到肉,穿的也比现在好,老板娘经常把她穿过的衣服给我们,那布料好着呢。红卫兵启发她,说他们打不打你啊?就像南霸天,黄世仁打丫环一样。甜沫的母亲说,也打,谁还不犯个错,你把碗摔了,你把粥熬糊了,那还不挨打啊,犯错了就该打,就像我的儿子,犯错了,我就骂他、打他。红卫兵小将只好放弃饭铺资本家丫环作报告的打算,走的时候还警告她,以后不许替资本家说好话,否则斗你!
甜沫的母亲后怕,对红卫兵的甜沫说,幸亏我没有说我差一点跟着去台湾。红卫兵的甜沫很认真地说,台湾人民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是你去了那儿,不但和我爸爸成不了两口子,也生不出我们,说不定你还要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甜沫的母亲撇嘴,不屑地回答:“你以为我们现在过的日子就比人家好啊,说不定我到了那里,嫁给有钱的主,比嫁给你爸爸那个拉车的强。”
红卫兵的甜沫听了这话很生气,说红卫兵真该叫你去,但不是作报告,是挨斗!
母女俩当然是开玩笑,甜沫母亲十八岁那年,张老板一家离开了济南。
不管是小狗还是小猫反正是在张老板家里慢慢长大了,她的身份自然是丫环,是仆人,是干活的,甜沫的母亲长到比桌子还高的时候,张老板说,你去帮助你李婶做甜沫吧。
甜沫是济南人早晨喝的一种粥,严格意义上说是济南市民早点的传统食品。关于甜沫的传说很多,有乾隆的,有纪晓岚的,有明末清初的,有考取功名的官员错把甜沫作沫甜的传说等等。其实这都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把喜欢的东西加上历史色彩,以此标榜自己多么有文化,当地的历史多么悠久。其实,甜沫原先就是北方人喝的小米面粥,是济南人特有的语言造就了这样一种食品。
甜沫的做法很简单,熬好了的小米面粥,再煮一些花生、粉条、豆腐皮等摆在旁边,拉车的人来了,喊:“老板,来一碗。”
卖粥的把粥端上来问:“添么(济南方言:增加什么)?”
拉车的说:“菠菜、花生。”
于是卖粥的就往粥里面加上这些东西。
卖菜的来了,要一碗。卖粥的人问:“添么?”
卖菜人说:“豆腐皮、粉条。”
于是卖粥的就粥里面加上这些东西。
耍把戏的人来了,要一碗……久而久之,做甜沫的人想,这样多麻烦,何不把这些东西一块放到粥里。“添么、添么”逐渐成了“甜沫”。
这是一家之言。关于甜沫的来历,民俗学家可以写上一本书,美食学家可以写一本书,都会把甜沫讲得头头是道。
张老板的一句话,让甜沫的母亲开始了做甜沫的生涯。
开始,就是为李婶做甜沫当下手:烧火、刷锅、洗碗、洗菜……后来就熬粥、煮豆子、煮花生、煮粉条……甜沫的母亲勤快,眼里有活,往往是李婶想要拿勺子,还没有说话,甜沫的母亲就把勺子递了过去;李婶想要抽烟,在身上找洋火,火苗已经送到李婶的眼前……这自然博得大家的喜爱。李婶慢慢就放心地让甜沫的母亲做甜沫,时间长了,李婶就在一旁喝茶抽烟,看着甜沫的母亲一步步成为甜沫大师。
张老板和老板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外当兵,一个在外地上学,身边没有孩子,一些家务也放心让甜沫的母亲去做,白捡了这样好的孩子干活当然高兴。
甜沫的父亲就是因为喜欢上甜沫母亲做的甜沫而喜欢上甜沫母亲的。
甜沫的父亲是拉车的。
甜沫的父亲拉的车,现在已经没有了。他拉的车,车把像碗口一样粗,车轱辘像现在的吉普车一样大小,装上挡板能拉煤,卸下挡板能装体积很大的东西,不亚于现在的小型货车。大车的两旁车帮各有几个挂钩,那是拉套子用的,装载沉重货物时大车需要两到四个人帮着拉套子。甜沫的父亲是中间驾辕的。这种车在民国初期就开始有了,一直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逐渐被汽车代替。在甜沫父亲娶甜沫母亲的时候,这种车是最普遍的运载工具。
拉这种车虽然是苦力,但让人佩服,因为一般人干不了。碗口一样粗的车把,你的手需要把它攥住,车的背带往你肩上一搭,百十斤车的重量就在你的肩上了。车装上货物,轻了上千斤,重了几千斤,需要你拉着向前。上沿儿(济南方言:上坡)的时候,虽然有人帮助你拉套子,但是拉套子的人担负的责任不大,靠腿和腰使劲拉就是。驾辕的不一样,两只胳膊拉着大车,需要掌握平衡,两个肩膀担负全车的重量,腰和腿要强力支撑,哪一个方面支撑不起来,都会造成危险。下沿儿(济南方言:下坡)的时候,拉套子的人可以休息了,驾辕的人不能,两条胳膊高高抬起,压住车把,用大车后面的车帮摩擦地面,让车慢慢下滑。你的胳膊不够粗壮,你腰的力气挺不住,腿的力气走不稳,一旦压不住,危险比上坡都大。
拉这种车的人,一般是身高体壮,他在你跟前一站,就像一座山,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吃得多,多得让你害怕。
济南历史上有很多名吃:甜沫、牛肉烧饼、鸡子儿包、油旋……这些东西的确好吃,用甜沫父亲的话说是给那些细发人(济南方言:仔细人或讲究的人)吃的,拉车人吃不起。吃不起是因为拉车人吃得多。拉车人吃什么?吃的是锅饼。
和喝的甜沫一样,锅饼也是这个城市的名吃。其实早些时候是下苦力人吃的食品。据记载,标准的锅饼是把面粉用温水搅拌均匀,再放入老面头,用手搋匀。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搋起锅饼的发面也要累得满头大汗,所以搋出面来是很硬的。烙熟的锅饼,两面都是很硬的“壳”,一咬掉渣却香馨,虽然硬得像啃石头,却硬而不艮,外硬里软,味道香甜,嚼之有劲而不粘,久食不厌,久存不变质,充饥耐存,干香甘美,可口开胃,因而备受干体力活人的欢迎。
一个锅饼一般五斤重,甜沫父亲年轻时,一顿半个。吃饱后,浑身舒坦,力大无穷,拉起车来喊着号子响亮,走起路来铿锵有力。
官扎营毛林子是甜沫父亲拉车经常路过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饭摊、饭铺,烧饼、油旋、水饺、馒头、包子等等应有尽有,甜沫的父亲拉车就是吃锅饼。吃起锅饼不能像现在的人吃饭那样,有菜还有汤。老田半个锅饼下肚,嘴对着水管子(济南方言:自来水管)猛喝一气,然后用袖子把嘴一抹……当然,老田也喜欢喝甜沫,喝甜沫就喝甜沫母亲做的甜沫。
甜沫的父亲和甜沫的母亲都说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相互吸引的,但有一点很明确,一九四八年的解放军的炮声成了他们结合的礼炮声。
甜沫的母亲记得很清楚,张老板一家是被一辆美式吉普车接走的,当时老板娘坐在地上哭喊,说我们的家就这么不要了吗?我们房子怎么办?我们饭铺怎么办?任凭张老板怎么解释她也不走。甜沫的母亲在房子的角落里看到张老板的儿子张吉泉急得在家里打转转,他说济南已经被共军包围了,济南沦陷是早晚的事情,他是护送军用物资支援济南的负责人,准备把父母接到南京,如果老两口现在不跟着他走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甜沫的母亲认识张吉泉,张吉泉是张老板的骄傲,上学时是学校的优等生,后来又考上军校,甜沫的母亲大了以后见过他一两次,无论是张老板的儿子还是国军的军官都不会理会一个下人的。
老板娘最后还是被儿子和张老板架上车,汽车的喇叭声和老板娘的哭喊声在官扎营的街道上响了很久。老板娘的哭喊声和美式吉普车的喇叭声消失了以后,甜沫的母亲才清醒过来,她想起张老板对她说,这个家、这个饭铺就暂时交给你了。她还记得,张老板上车了,又转身下车,看着在一旁紧张发抖的丫头说:“你害怕什么,你做你的甜沫,共产党来了也要喝甜沫。”
眼看着美式吉普车都开动了,张老板像是有千万语一样脸色憋得通红,终于汇成一句话:“我们还会回来的。”
张老板走了以后没有多久,枪声炮声响彻济南的天空,丫头一个人孤独地蹲在饭铺角落里,眼睛看着天空又圆又亮的月亮瑟瑟发抖。这时,甜沫的母亲听到有人敲门并且在喊她的名字:“丫头,你在吗?你不要害怕,我来陪着你。”
甜沫的母亲后来对人说,拉车小伙子的声音盖过了枪炮声,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开开门扑向拉车小伙子的怀抱。
枪炮声消失以后,大街上的标语换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张老板说得对,甜沫的父亲仍然拉着胶皮轱辘的大车,甜沫的母亲仍然做她的甜沫。所不同的是,甜沫的母亲和父亲在毛林子的饭铺里一个儿子接着一个儿子地生起来。
他们唯一的女儿呱呱落地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时隔三十五年,张老板说的话应验了,不过不是他回来了,是那个开着美式吉普车的张吉泉回来了,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甜沫的生活轨迹,为官扎营又添了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