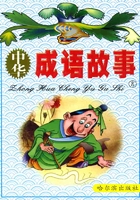看到客人房间灯光熄了,古太太蹑手蹑脚回到卧室,她知道自己和丈夫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自从嫁给年长20岁的导师古又今,古太太除了将身份角色从学生转为妻子以外,很多时候还充当丈夫事业发展方面的高参。“老师,你既然这么想重回母校F大学,那倒不妨听从成处长建议,先打通裴老先生这一关。想来导师如父母,求他帮忙再正常不过了,没什么开不了口的。”其实古太太从未见过裴自岑,跟古又今结婚后也很少听丈夫提起这位老先生。
古又今牵动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你以为天底下导师对学生都像我对你这么好啊,天真。”
古太太扑进丈夫怀中:“那我对你不好么?嫁了你这个年龄差不多大我一倍的老头,我图什么啊。”
古又今抚摸着妻子细嫩的脖子,感叹道:“就是为了报答你,我才要抓住人生最后的机会跳一次槽。不知哪天我撒手西去,也好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嘛。”
古太太捂住丈夫嘴巴:“胡说什么?要不是看你待在这个小小商学院里委屈,我才不鼓动你跳槽呢。”
古又今转入正题:“你和成冠雄其实都不了解裴自岑。这老先生不是你想求他就肯帮忙的,倔劲儿上来六亲不认,跟他讲师生之情绝非易事。”
当年古又今与秦洋争“浦江学者”败下阵来,裴自岑又不肯让出《经济学研究》主编位置,他一气之下动了出走念头。那段日子他一面在沪上其他高校寻找新东家,一面故意在系里放出想要跳槽走人的风声。古又今以为自己是裴自岑的关门博士生,毕业后也发表过一些颇有影响的论文,在学术界算得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经济系领导和校人事部门断然不肯把本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轻易拱手相送。只要校方有人出面挽留,他则可乘机开出条件,作为继续留在母校工作的一种利益交换。不料还没等系里和校人事处正式找他谈话,裴自岑倒亲自打电话把他叫了去。
那天古又今刚进门,裴自岑就朝他发难:“又今哪,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没有一个像你这么爱钱的。听说你把自己当块肥肉吊起来拍卖,谁肯出价高就卖给谁,是不是啊?”古又今十分震惊,心想这老头如今足不出户,消息还真灵通。他辩解道:“裴先生您这样比喻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换个环境我照样可以做学问。现在提倡人才流动,学术自由,我哪点做错了?”
裴自岑说:“你忘恩负义!F大学培养你这么多年,因为你家境困难年年都给你最高数额的助学金、奖学金,还用公费送你出国进修。现在你学术上小有成就,就以此当资本来向母校要价了。你若还念我老头子是你导师,就听我一句忠告,人活着要有志气,无论是谁,不先学会做人,休想真正学会做学问。”
古又今不敢与裴自岑争辩,沮丧地离开导师家。但他相信树挪死,人挪活的老话,下定决心离开母校F大学。那时古又今还有个完整的家,妻子是他本科同班同学,了解他事事都想出头占高枝的性格为人。妻子无数次劝说他:“你已经在股市上赚了不少钱,何必再跟秦洋争‘浦江学者’,人活在世界上不能什么都要,更不应该做出对不起F大学和裴老先生的事情来,你得学会感恩。”古又今根本听不进妻子的话,得不到“浦江学者”头衔或《经济学研究》杂志主编位置,他感觉自己在F大学憋屈得几乎活不下去了。
然而出乎古又今意料的是,沪上几所原本对他很感兴趣,恨不能尽早将他从F大学挖过去的高校相继改变了态度,甚至以各种理由推迟与他商谈调动事宜。古又今以为是自己开价太高,又要住房补贴又要科研经费,吓退了未来的新东家。于是他主动降低条件,只提出要住房或是购房补贴款,科研经费可日后视其科研成果再定。即便这样放低身段,那几所令他动心的高校,仍然迟迟不肯下决心引进他这位难得的人才,古又今百思不得其解。
那年成冠雄还只是F大学人事处一名小科员,与古又今颇有些私交,便点拨他道:“古老师你也不想想,裴自岑是经济学专业泰斗,兄弟院校同专业的掌门人哪个不敬着他,他不点头,谁好意思从他手下挖人?况且你老兄此举多少有点背叛师门之嫌,把裴老先生得罪了,他只消一个电话,肯定没人敢要你嘛。”
成冠雄一番话如同醍醐灌顶,说得古又今浑身发冷,颤抖不已,脑子却从未有过的清醒。他总算明白自己翅膀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硬,离开F大学这处老巢独自飞翔的话,迷路或栽跟头几率依然很大。古又今是个识时务者,他选择了忍耐,并且及时调整跳槽计划,不再四处寻找新东家,而是一副安安心心在F大学待下去的模样。教研室同事私下里问及古又今调动工作进展,他则一脸诚恳表示:“既然裴老先生希望我留在F大学,我岂能不遵从师命呢?”好像他之所以继续在母校工作,完全是看裴老先生面子。
教研室有好事者曾去裴府证实古又今的话,裴自岑听后一笑,既未承认也不否认,毕竟是自己带出来的博士生,总要给他留条路走。后来几年中,古又今申报科研项目或是评定职称,都去找导师帮忙。裴自岑亦不计前嫌,鼎力相助。他为弟子的学术专著作序,无偿审读弟子的科研项目报告,这些工作对一位耄耋老人而言并非轻松事情。导师的善意让古又今感觉到一丝温暖,他也曾想过一辈子留在F大学教书做学问。然而终究抵挡不住杭州商学院西湖边这套公寓房和不菲的科研经费的诱惑,古又今终究还是离开了母校F大学。
夜深人静,古太太熬不住倦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染成浅褐色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古又今怜惜不已,轻轻摇醒妻子:“你先去睡吧,我得再想想成冠雄说的话。”古太太其实并未睡着,她趁势搂住丈夫脖子:“你也别想了,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