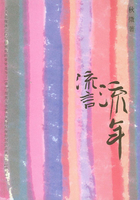到了单位,看见经理正在张罗着开会,他把公司里所有没有出外勤的司机全召集起来,然后宣布了一件事情:山里的银矿急需一批设备,现在这批设备已经运到了市物资局的库房。银矿委托运输公司将这批设备立刻运进山里去,运费给得很高。现在是大雪封山期,这时候进山危险性很大,要搁在平时,这么高风险的活经理一口就回掉了,因为一旦出了事,后面杂七杂八的麻烦事会把人烦死。但这次任务是通过市里一位副市长亲自安排下来的,银矿是市里的支柱产业,屁大点的事都可以惊动市领导。副市长在电话里把这次任务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经理只得硬着头皮扛下来。但如果把这趟活硬性派给谁,万一在山里出了什么事,司机的家属可不会答应,因此只能动员大家自愿报名。
经理先是说了一通“经济发展”、“改革大潮”、“政治觉悟”等等穿靴戴帽的话,听得底下的司机一个个昏昏欲睡,有一位还嚷嚷道:“经理大人,你快一点行不行,我这儿可还憋着一泡尿呢!”大家一起哄堂大笑起来。经理也是从基层的货运司机一步步干上来的,平时跟大家嘻嘻哈哈惯了,就说了句:“你就先尿在裤裆里吧。”
等大家笑完了,经理说:“同志们注意了!现在说说运费问题:银矿这回肯出血,我也就不亏待弟兄们。这趟活下来,除去油耗、车损,按40%提成,想干的就报名。我这里只要两个人,报晚了就没份了。”
底下一阵喧嚷,但喧嚷过后,却没出现经理预期的踊跃报名的场面。谁都知道只要接了这趟活,就等于把一只脚伸进了鬼门关。钱固然重要,可相比性命,钱就有点像个“屁”了。
又等了好一会,经理有些生气了,先骂了无数个娘,然后说:“你们这些个×货,平时有点好活一个个孙子一样撵在老子屁股后面,现在碰上点硬骨头就都不想啃了,一点都他妈的不讲奉献……”
坐在经理后面的徐大伟这时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早上上班来的路上,他就下决心要跟经理商量调他去开大货了,凭他跟经理的关系,一个月安排几趟往返带货的长途任务,一个月下来挣个两千多不成问题;一年下来就能攒个小三万,加上自己这些年存的两万多块钱,按揭个两居室的房子再加上装修应该勉强够了;再向父母张口借一点,应该可以达到于晓燕结婚的条件了吧!结了婚,于晓燕总不会再像现在这样眼睛长到脑袋顶上了吧?他甚至想:我要真有了房子,一个月又有两千多的收入,是不是该换个比于晓燕漂亮一点、脾气更服帖一点的小妹妹结婚呢?这样一想,于晓燕的诸般缺点便在脑子里一一闪现:爱睡懒觉啦,贪慕虚荣啦,爱使小性子啦。最使他恼火的就是她打心眼里似乎就有点瞧不起他。男子汉大丈夫,被个女人瞧不起,真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样越想越多,脑子竟然乱了起来,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想得到什么。
经理在会上一提起往银矿送货,他马上想到这可能是个机会。一来可以解经理燃眉之急,这样以后拉货结账经理肯定会对他优先照顾;二来他这两年多来一直给经理开小车,如果他直接下货车队,可能会有一部分货车队的司机对他不服气,说不定还会背地里给他穿小鞋。去年给书记开车的小郭因为出了一次事故,差点没把书记的命送掉,于是便被贬到货车队,但他下到班里没两天就被整得不得不申请调离。货车队司机都是糙脾气,最看不起没点真本事却想在货车队跟他们分一杯羹的混混。徐大伟虽然不是混混,他的驾照是在部队实打实考出来的,自认技术还是过硬的;但要在货车队站住脚,还得干点有分量的事才行,如果把这趟险活跑下来,将来在货车队肯定会被人高看一眼。
诸般好处想完,剩下的就是这趟活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是否值得去冒这个险。徐大伟刚来运输公司工作那年,曾开着一辆老掉牙的东风车进山拉矿石,那段险路他是走过的。说险其实只险在翻达坂的七公里路上,所有吃大货这碗饭的司机只要一提起翻达坂,脸上的神情就立刻严肃起来。别看这短短七公里,每年多少车在这里翻下了山崖。
总结起来,这段路的险可用六个字概括:道窄,坡大,弯急。
这七公里达坂路是倚着山脊开凿出来的,宽度只够一辆车单行,隔五百米有一处稍宽一点的平场用来上下错车。由于这条道上跑的车多半是往下拉矿石的,按照轻车让重车的行规,上山的车要主动给下山车让道,而由于弯多弯急,路又是在群山之中绕来绕去,一般很难看见前方是否来车。所以上山的司机一上达坂就得支楞着耳朵,听到前方有汽车喇叭声就得提前找错车的场子,如果一不留神跑过了错车的地方,和下山的车顶了头,那对不起,你上山车就得乖乖地打倒车,一点点往后退,一直退到能错车的地方。原先矿上也曾考虑将这段路加宽,但只加宽了一公里就作罢了。因为路是倚山而凿,又没有相应的防护措施,加宽后山体塌方的危险性会加大许多,一下雨,加宽的路段往往被松脱下来的山土填塞,得不偿失。这条路自七十年代起就一直维持现在的宽度,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