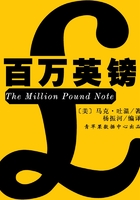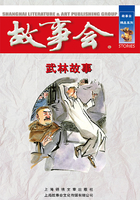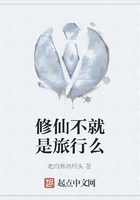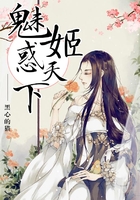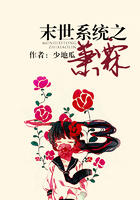哑巴阿南终于在三十五岁那年找到了女人。可是还没有过上两年有女人陪伴的日子,就又回到了从前。不同的是,身边多了两个与他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孩子。
这件事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如同高原的风季,整整持续了一冬一春。
我原以为阿南只是个哑巴,看来他还是个傻瓜呢。
但他的傻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他一点也不傻,只是比别人善良。
……
人人都知道有点傻气的阿南是个孤儿。他在七岁那年成为孤儿这件事,谁都不能怨,只能怨他的父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把自己喂给了老鹰,让他孤零零地在山乡艰难奔波、忙碌、啜泣、歌唱。
沦为孤儿,阿南的内心深处一定隐埋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寂寞、烦躁、忧伤……但是,好就好在他是个哑巴,不能借助语言表达思想,跟漫山遍野的花啊草啊树啊没啥两样,所以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向旁人表露心迹。除了江杨,多数人看不出他内心究竟掩藏了多少忧愁和烦恼。他有时倔得像头未经驯服的野牛,使起性子来,直叫人发怵。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比慈祥的男人还慈祥,比温柔的女人还温柔,比善良的佛教信徒还善良。
阿南的父母在临终前,把他连同房产、牛羊,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全都托付给了江杨村长。那位叫江杨的村长多次准备把阿南接到自己家里一起过,可他不干,硬是不愿离开父母留给自己的家。不过这并不影响江杨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尽其所能给予他关怀、照顾、呵护,使他得以健康地成长。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成了一名独立生活、远近闻名的石匠,而且有幸过上了相对富足的日子。这样一来,阿南父母的那些个亲戚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事儿,既用不着照顾他的生活,也没有机会从他身上揩油。只是在见到他的时候跟他打个照面儿,寒暄一下。逢年过节,送一句最最寻常不过的“扎西德勒”。村里人有意无意地注意到阿南从不跟亲戚们走动,即使哪个亲戚生病了,他也不会去看一眼。因为他只是个哑巴而不是傻子,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父母当年为何把自己托付给了江杨而没有交给亲戚们。简单点说,亲戚们之于他纯粹跟一般的乡亲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在他们身上流淌着跟自己相近的血液。由此,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亲戚渐渐地从他的记忆里淡出了。老实讲,亲戚们的存在除了表明阿南不是从哪个石缝里蹦出来的,也就没有别的意义了。
好像已经提到过,从表面上看,阿南是个非常乐观的人,整日乐呵呵的,眼睛和嘴角总是流淌出无忧无虑的笑意,很少见他脸上挂过愁云。但是寡妇祁梅的病故,曾一度使他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变得焦躁、烦闷、易怒。当然,经过时间这位神医的精心治疗,他的性格慢慢地又恢复如初了。我们村里的人都喜欢他性格中憨厚、谦和、实诚的一面,就像喜欢地里的庄稼、山头的草木和棚圈里的牛羊一样。甚至有人认为在全乡找不出第二个性格比他好的人。鉴于此,所有人都乐意接近他,把他亲切地称为“我们的阿南”。只是很多不熟悉他的外乡人,见他那副傻乎乎的样子,便自然联想到弱智、残障、傻瓜、酒鬼等等最为通常而恶毒的字眼。
疏于别人管束的阿南,像山里没人修剪,却长得笔直、挺拔的柽柳,除了有时为祁梅的两个遗孤跟人家较劲外,就没有做过什么讨人嫌弃的事儿。
令江杨感到欣慰的是,在祁梅的遗孤上初中以后,阿南奇迹般地会说些“请坐”、“请喝茶”之类的简单句子,也很少呜呜噜噜了。只是吐字不清楚,而且依然没能甩掉啊吧啊吧、呃呃哦哦。
也许是两个孩子非常听话、争气,自己又能说些短句的缘故吧,我们的阿南年纪越大,越发显得快活,满脸漾动着难以抑制的幸福感。这不,他一得空,就望着挂在墙壁显眼处的全家福,对着他永远都看不够似的祁梅那张脸,动情地叽里咕噜半天,向她汇报她走后家里发生的事情,营造出满屋子的喜悦气氛。而讲得最多、最开心的还是两个孩子的事儿。
阿南只要在家,他就会笑眯眯地望着根敦帮他在拉萨通过电脑处理过的全家福,喔喔噜噜地感慨半天。他在心里时常想,要是祁梅还在,我会让她好好享福;要是这两个孩子喊我爸爸,那该是怎样一种幸福的景象啊。有时看着两个失去了双亲的孩子,他联想到自己早已去了异域的父母,挖空心思想象父母的音容笑貌,暗忖,我跟这两个孩子命运相同,我一定要像江杨大叔照顾我一样,把他俩照顾好。要是这两个孩子出息了,祁梅的亡灵肯定会得到哪怕是些许的慰藉。
阿南思念祁梅和爱怜两个孩子的情思,宛然一股股春风,荡进了清泉里,刻在了岩崖上,浸入了骨髓中,萦绕在家里家外,扯不断,撕不破,没个消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