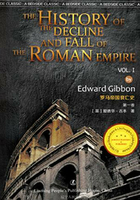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6年第06期
栏目:中篇小说排行榜
金秀和金玉,同样站在高颜值起跑线的姐妹俩,命运之路最初仿佛分岔于姻缘,然后在岁月里渐行渐远,她们有怎样的命运和性格?
老早我就想跟人说说我大姐金秀和二姐金玉的故事,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主要原因是我面矮,抹不开面去讲自己姐姐那些花花绿绿的事,总觉得不够仁义。
现在是时候了,我这俩姐,一个已躺在京城协和医院的病榻上,再也没有能力为坊间提供闲话;一个已彻底在祖国大地上蒸发,只有年节时偶尔能听到她英汉二合一的越洋问候。两个一度生活在唾沫星中的女人,已脚前脚后淡出我们的生活。
从金秀开始吧,她是我们家老大。
看我大姐金秀现在的憔悴样,谁都不会想到她当年是何等的光彩照人。关于她当年的模样,那脸蛋那长辫那身材,我真想细细道来。只是,长相这事是各花入各眼,难有统一的尺子,所以我还是谦虚点,借邻居王老师的话来说。王老师是教美术的,专攻古典人物,审美不会走眼。他说,金秀就是梳辫,如果把头发绾上,手执轻罗小扇,身着宽袖斜襟的缎袄,活脱脱就是末代格格。王老师并未意识到他的话所产生的影响,未意识到他是在前瞻性地进行赏识教育。他的话让金秀多次偷偷把头发绾起,拿着大蒲扇在镜子前款款而行,似乎行走在一百多年前宫中的幽深小径上。也因此三天两头迈着格格步款款地到王老师家串门。她不白去,每次都能得到专业又权威的赞美,还能额外赚回火辣辣的目光。那些目光都是王老师的学生给的,一群热爱艺术、心气颇高、水平一般的半大小子。他们看到金秀当然会眼露异光,焕发出澎湃的创作激情。也不管金秀同不同意,坐地板上,蹲凳子上,趴窗台上,陆海空地对金秀一通素描。画好后在上面郑重其事落上款,多半都有字号,某某山人某某居士某某子,日期清一色是戊辰年芒种之类。这帮人中只有一个例外,总是实打实写真名,和身份证上的一样,朴实又自信,让人看了踏实。这个后来成为我姐夫的人叫余建设。
建设画金秀画得最不像,可金秀最喜欢。看画上面的人,衣着发型轮廓确实有金秀的影子,可要说是鉴湖浣纱的西施也行,说是大观园中葬花的黛玉也行,反正是进行了深度演绎。金秀便认为建设行,有艺术功底,别人画她是机械操作,建设是艺术创作,这小子肯定会有出息。再去王老师家,她专找建设对面坐,全方位地让未来的画家对她艺术加工。后来她只接受建设单独创作。再后来两人开始选择创作地点,到湖畔公园郊外去画。拈花垂目,抱树掩身,倚石仰天,张臂迎风,把能想到的造型全艺术了一遍。
经过一番高雅的折腾,建设终于把金秀画到了手。
当时他们才参加工作,金秀从卫校毕业后分到妇保医院当护士,建设在我们市唯一的四星级酒店做厨师,红案,切墩的。经济上的独立使金秀有了底气和勇气向家里摊牌,说处了一个朋友,想找时间领回家和家人见见面。
按理这是我们家的喜事,好呀,爹妈看看未来的女婿,弟妹看看准姐夫,理当欢欣鼓舞。我爸我妈却挺深沉,把欲见未来姑爷的迫切心情表现成了勉强应允。我和金玉喜形于色地开大姐玩笑,说她刚参加工作翅膀就硬了,想飞了,不想和弟妹一个锅里搅马勺了。说她学刘巧儿,劳模会上认识人一个,这一回可要自己找婆家……我还很世俗地问她,男朋友是干啥的,长得帅吗?金秀说,在大酒店上班,搞艺术的。我听后有过短暂的疑惑,酒店里有何艺术可搞?但这种敏感马上被艺术二字冲散,我不知金秀领回来的人是啥艺术形象,但我想肯定错不了,搞艺术的嘛。平平常常的人谁好意思去搞艺术?
当金秀把建设领到我们家,说是她男朋友时,我们都有些惊愕,继而付之一笑,这怎么可能?建设在客厅拘谨地向我们点头问候时,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建筑工人,虽然能挖掘出一种劳动美,可当我姐夫却是先天性的遗憾。建设不单工作不理想,人长得也不争气,又黑又瘦,个也不高,金秀穿上高跟鞋能和他持平,两人明显不般配。
我爸打眼一看,便武断地认为他们没戏,小家雀怎么能和堂前燕比翼齐飞。他并没引起高度重视,只是拿出长辈的矜持让烟让茶的间隙,对建设说他们年龄还小,要趁年轻多学点吃饭的手艺,把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提醒建设不要被金秀的表象所迷惑,说她挺大个眼睛忽闪忽闪的,瞅谁都那样,不一定有其他意思。
二姐金玉还把金秀拽到院里,一本正经地教训她,姐,我看建设哥挺实诚的,你可别拿人家开耍。金秀说,我没耍他,我们真是朋友。金玉说,得了吧,他长得跟非洲难民似的,你能看上眼?说死我也不信。金秀说,去去,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看以后你能找个啥样的。
我们家的态度在建设和金秀的意料之中,知道老金家不会轻易接受他们,早在登门之前就做好了承受各种挫折的准备。爱情之路跟科学道路一样,充满崎岖坎坷。可崇高的爱情哪有一帆风顺的,哪一个不是泪水泡出来的?梁山伯和祝英台顺利吗?罗密欧与朱丽叶顺利吗?
金秀的压力不只是来自家庭,他们妇保医院也给她制造了挺大麻烦。他们医院有个饶有趣味的传统,就是院领导愿意在本院医护人员中给自己儿子选对象。曾经最漂亮的一个护士做了院长的儿媳妇。院长姓刘,职工们便把院长的儿媳妇叫“流产”,意思是刘家的财产,名花有主,外人休得再打主意。后来书记的儿子也在本院找了对象,书记姓尹,职工们便因袭术语,把书记的儿媳妇叫“引产”。同事间的对话经常会蹦出“流产”“引产”:“别议论院领导,‘流产’就在隔壁查房……”“‘引产’来电话,让送两箱盐水……”当大伙嘻嘻哈哈的时候,忽然发现,常务副院长的儿子几年不见也蹿成了大小伙子,踩到了谈婚论嫁的起跑线。有意思的是副院长姓南,大伙异常兴奋,说妇保医院该有“难产”了。于是大伙兴致盎然地猜测起谁能是“难产”来。正当大伙半真半假地为副院长家事操心时,金秀分到了妇保医院,在妇产科做护士。大伙眼睛一亮,有了,“难产”出现了。群众的观点多半是正确的,凭金秀的长相副院长挑不出瑕疵,如做“难产”,肯定胜过“流产”“引产”。而且他们对金秀的家庭背景了解得十分透彻,父母都是工人,没啥大能耐。最关键的是金秀还分在了累死累活的妇产科。所以大伙断定金秀在妇产科干不长,很快就会因为“难产”调到院部去。果然,猜测“难产”的喁喁声此起彼伏时,南院长便找金秀谈话了。
谈话是在他办公室进行的。本来这事应该由第三者出面,先旁敲侧击再穿针引线,成不成当事双方都不伤自尊。可南院长认为没必要走那道程序,认为这事只有成功,没有第二个结果,甚至金秀会对他的亲民举动感激涕零。在简单聊聊工作后,南院长问我姐多大了。金秀报出了虚岁。院长说,噢,比我儿子小三岁。然后非常自然地说起他儿子——
我们家你这个小哥,也是专科毕业,分到了外贸局,那批学生他的去向最好,没用我出面,完全是靠自己成绩说话。那英语说得比汉语都好,局领导说了试用期满就派到国外“驻办”去。那个儿比我高半头,国庆时候学校组织阅兵式,年年都被选进仪仗队。军训多苦呀,苦也咬牙给我上,我对孩子从不娇惯。他妈妈就不一样了,当妈的啥心都操,这不,刚上班就把他的新房准备好了……
院长把儿子的硬件简明扼要地介绍完,直截了当地说,要不你们接触接触?年轻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共同语言,交流交流很有必要。
有一种表情介于哭笑中间,平时无论怎样挤眉弄眼也拿不出来,必须是窘事缠身才能逼出来。南院长面前的金秀就是这样,说不清是笑还是哭,双手揉搓着白大褂,手上的汗水已使衣角湿了一片。她眼睛盯着桌子上的电话,嗫嚅着说,谢谢院长,那什么……我已经……那什么……有……男朋友了。
我们知道这次收编性质的谈话,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姐轻描淡写地提了提,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甚至还有一种脱险的庆幸。我爸我妈心里如何怪罪金秀,如何对失去大有作为的女婿而惋惜,我不得而知,不过看他们黑着的脸和拉饥荒的神情,估摸已到了沾火就着的临界点。二姐金玉一个劲数落金秀,像中奖彩票送给别人一样替金秀惋惜。她问南院长有多高。金秀说一米七二七三那样。金玉比画着计算,忽然惊叫道,他儿子有一米八多。金秀说,一米八多又咋样,至于一惊一乍的吗?金玉说,姐,你要是真不干,我可上了。
我们惊异地看着金玉,比听到金秀回绝南院长还让我们意外。我不相信二姐是玩激将法,虽然她有一肚子心眼儿,就跟石榴肚里的籽一样多,可从她说这话时的语速和神态上看,完全是情急吐真言。金玉发觉失口,马上修补说,我是想给同学介绍,这么好的条件不拿下太可惜,你问问南院长,外面人能不能做“难产”?
金秀瞅瞅我爸乌云密布的脸,不再理会金玉,埋头吃饭,偶尔给我爸妈夹筷菜,用她略显弱势招人同情的眼神,拜托家人别再继续这个话题。
大姐和建设的关系按着两人的既定方针,不鸣笛也不刹车,向着未来稳步推进。值得一提的是,建设在即将成为我们家大女婿的前俩月,却做出了超出他年龄的举动,提出要和金秀分开一段时间,说是出去写生。金秀问去哪儿,建设冒出一句,八千里路云和月,战士双脚走天涯,跟着感觉走呗。把金秀哭得,问建设是不是变心了,不要她了。建设表现得非常决绝,在金秀的泪眼中,背着画夹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建设毫无前兆地说走就走了,这事做得太有性格,太男人了。为这事,金秀第一次和我爸妈顶起嘴,质问他们是不是背地找过建设,对建设说了什么,把一个大活人逼得远走他乡。本来这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画画的腿勤,都爱往外跑,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到处走走看看再正常不过。建设可能是借机制造距离美,耍点让金秀那个档次的五迷三道的小聪明而已。让金秀一哭闹,好像建设奔赴前线一去不复返了。我爸说,就凭那小子的蔫劲和磨劲,可能把到嘴的肉吐出来吗?金秀,你掐指算吧,超过百天不回来,就报案说你爸谋杀。
不过一个月,建设就又出现在我姐金秀面前。只是与走的时候判若两人。新版的建设已是长发盖耳,胡子拉碴。穿着满身是兜的牛仔装,双肩挎的帆布包。与其说像画家,不如说更像漂泊的行者。他看到金秀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我回来了。第二句:过去的建设死了。
金秀一时恍惚起来,这个每天在梦中无数遍呼唤过的男人忽然现身,让她有种隔世之感,不知这个自诩已经涅槃了的男人是否继承了先前的情缘?半晌,建设才稳稳当当地过来,把不知所措的金秀揽到怀中,吻她。金秀一下醒了,哇地哭起来,捶他,然后死命地抱他,怕他再走,再涅槃。就是在重逢那刻,她倒在建设怀里说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话:建设,咱们结婚吧。
建设说过去的他已经死了,这话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一个月野外行走的结果。这一个月,他问自己最多的就是,靠画画能画出未来吗?大自然气象万千,人世间风情百态,自己的两把刷子能记录下什么,表现出什么?看着画夹上野外写生的草稿,他悲哀地意识到,自己的笔力画不出啥名堂。即使画再多的蛋也成为不了达·芬奇,就像喝再多的酒也成为不了李太白一样。而靠专心本职工作就有未来吗?这条道比画画还暗淡,他对味觉远没有对色彩敏感,根本没有大厨基因,不可能在葱姜蒜中岗位成才。夜深人静时看到真实卑微的自己,确实是件残忍的事。建设痛苦地领悟到,要想混个好未来,必须放弃马勺和画笔,这是对自己负责的第一步。当时正值新一轮经商热,商风日炽,建设便顺应潮流,选择了投身商海。
建设经商的想法几乎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明摆着,人间正道是经商。只是建设父亲提出个先决条件,捣腾买卖可以,但先把媳妇娶回来,这是一辈子大事。于是,建设在毅然决然结束厨师生涯不久,便和我大姐到政府领取了执照。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二,响晴的天,连狗都躲在墙角吐舌头。吃过午饭,我爸让我上“一副食”买两斤肉,晚上做红烧肉,乐呵乐呵。我觉得应该,打今天开始,金秀就是余家的人了。
“一副食”在中山东路,斜对过就是民政局大楼,一楼的门市房是婚姻登记处。我拎着肉从“一副食”出来,金秀和建设正好从登记处出来,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暴露在七月的骄阳中。往家走时,开始我还打算追上他们,可马上打消了念头,他们在前面走的样子实在让我意外和不爽。那情景,至今想来还让我堵得慌。
柏油路面像被水淹了一样,泛起一阵阵热浪。两人撑着一把伞,打伞的是我姐。可能是喜气熏的,建设脚步很轻快,金秀穿了高跟鞋,有些跟不上,时不时紧跑两步,以保证那把伞能稳定地遮住建设。而我姐,有时是半个身子在伞中,更多的时候整个人全暴露在烈日下。我看到我姐的的确良白衬衫已经被汗溻透,一手打伞,一手用手绢不停地擦着脖梗子。
我姐颠颠地跟在建设身后,那伞始终没离开过建设的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