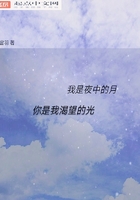来源:《章回小说》2011年第10期
栏目:农家书场
我母亲是河下镇白马湖村一个凶猛的农妇。只要我母亲一声吼,全体村民的肉要抖一抖。
她的凶猛来源于很多因素,比如貌美如花的她却嫁给了一个弯如秤钩的驼子。生存如无数只蚂蟥,吸干了我母亲的青春美艳。她被生活的风刀霜剑砍杀了所有的精华,宛如那根被人们遗弃在运河边枯萎的芦苇,在寒风中伶仃地战栗。可怜的母亲,在她瘦骨嶙峋的胸膛里,有六张饿得奄奄一息的嗷嗷待哺的嘴,其中四个儿子还哭着喊着和她要老婆。所以,我母亲有很多理由凶猛。
关于我母亲的故事,在白马湖村流传很多。我母亲那时候是白马湖村运河对岸泾河村的一个农家姑娘。我父亲很调皮,常爱到运河边玩耍,运河里有各种船只驶过。而我母亲来运河是因为淘米洗菜洗衣服。这两个人隔着一百多米的运河看过来看过去看到对方朦胧的模样。本来她是绝对嫁不到我们家的,虽母亲以为她貌美如花,但我们家是河下镇知名地主,我父亲又一表人才,想嫁我父亲的女子多着呢。
问题是发生了一件事。在我父亲十六岁时的夏天,那天中午热得不行,太阳跟疯狗似的将人一个个咬回家,偏我父亲神经搭错了,他竟偷偷地跑出来,带着竹竿,上面粘着点面筋,到运河堤边的树林里捉蝉去。
正当他忙得不亦乐乎,有一个人跑过来,问父亲有什么地方好躲。父亲听远处有枪声,不知道他是英雄侠士的闲书看多了,还是脑子进水了,也不管这个人是好人坏人,他就决定救人家。将人家藏在一处河堤的坟洞里,自己跑起来。后面追的人以为父亲是目标,就狂追,父亲在前面就狂跑。后来跑不动了,就朝一边的一个荷花塘里一跳,他潜到荷叶下,等追的人走了,他得意洋洋地回到家,向家人吹嘘一通。懂得点医道的祖父吓坏了,神色大变,想一个热燥得大汗淋漓运动到沸点的人,突然跳下极阴极寒的荷塘,那是什么概念?祖父赶紧让人用药水泡他,父亲还是寒毒侵身一病不起。祖父为了给父亲治病,用光家里的积蓄,开始几亩几亩地卖地了。三年过后,家里一无所有,父亲的命是勉强保了下来,但我们家却是穷人了。祖母从米缸里淘出最后几斗米,为我父亲娶了泾河村我的母亲。洞房花烛,母亲看到曾经风流倜傥的地主少爷,变成瘦得跟鬼一样弯成秤钩状的驼子,那一定是傻到底了吧。但嫁了就嫁了,没法子改变,那时候还不兴离婚,只有男人休女人,女人没权休男人。
白马湖村人说我们家运道改了,以前有钱时,两三代都是单传,战战兢兢的就怕断了香火,能养育一大帮孩子时没孩子可养。现在穷光蛋了,竟跟下小猪似的,一窝窝的。我母亲连生了五个儿子,虽只存活了四个,但加上两个女儿,还是硕果累累。按这儿农村的习俗兄弟姐妹排序,夭折的哥哥还算上位置的,所以我是老六。据说母亲生第五个儿子时,就不愿意养他了,提起新生儿就扔进洗干净放上水的马桶里,将自己的儿子淹死在马桶里。这是预谋杀人呀。
对于这个故事,我母亲常骂村里人乱嚼舌头根子,那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死婴,还是个下肢扭曲带残的孩子。母亲只好托人将死婴埋进荒地了。村里人说的我不相信,哪有这么残忍的母亲,不过因为母亲的种种行为,我也将信将疑。在争粮食争工分争责任田争水的诸多战役中,我母亲用她的牙枪舌炮轰倒白马湖村所有的人。所以大家攻击她,我能够理解。因为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儿女太弱势,再加上农活家务出头露面的事,都靠母亲一个人,她的能干就显得太凶猛了,不论是在村里还是家里,她都表现极端的强势。
我可怜的父亲,是打不过骂不过我母亲的,他已完全忘记反抗我的母亲了。我母亲以为她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将我们全家人都打入水火之中。在我的记忆中,她似乎就没笑过。在众位兄弟姐妹中,我母亲对我最不好,因为只有我敢反抗她,而且和她一样凶猛。所以我母亲常打我,往死里打,骂我往最毒处骂。我恨我母亲,恨的理由也很多,从我母亲对我的言语,全是恨和刻毒。我们哪像母女,好像彼此都欠下对方血债似的仇人。
知道我的童年每天都想什么吗?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我母亲是我继母的证据。这样,我可以向全世界狂吼,这个乡下凶狠的女人不是我妈。
还好,我后来遇到大王了。它将我从孤寂仇恨里拉了出来,给我一丝情感的温暖,并彻底地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第一次和大王相遇,是在那个冬日的夜晚。
月色从院子里那棵光溜溜的泡桐树枝桠上挂到地面上时,已是一幅很风雅的版画。我从这幅版画上鼠蹿而过,在我打开茅屋的门时,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动物也尾随我进了我的家。
在那张肮脏的小床上,我梦到一位王子。在柔软地舔着我散发脚臭的脚趾头。
第二天早晨,妹妹一声恐怖的惨叫,将我惊醒。身上那破絮翻飞的棉被踢到一边去了,可怜的妹妹瞪大眼看着一只丑陋龌龊的小动物。两只小动物对视着,相互哆嗦着。
看着妹妹无助的眼神,我鄙薄地伸出我的爪子,夹住这丑陋龌龊家伙的一只耳朵。小东西唔唔地垂死挣扎。我吸着鼻涕裹着破被子,拎着这丑陋的东西朝外走。
善良的妹妹这会儿缓过神来,声音像从风箱里挤出来的风似的,不能连贯细声细气地叫了声不要弄死它,放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