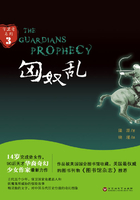我已走到院中,站定。睁着眼,因为瘦出极品,我的眼眶是突出的,眼球是鼓出来的,活灵活现的死鱼眼。死鱼眼还糊满了眼眵。眼眵有点妨碍视线,我擦了擦。然后,瞄着那棵粗大的泡桐树根,思量着,能否一下子就摔死这小东西。听了妹妹的叫声,我的思维短路,忽然停下了。我开始仔细地瞅着在我的利爪下拼死扭曲着身体嗷嗷叫唤着的丑陋的小东西。
这丑陋的小东西,瘦得筋骨都杵出来了,被一层黏稠稠泥巴鸡屎猪粪什么的糊得不知道它是何方怪物。我想,就是这么个丑陋龌龊的小东西,在我的梦中舔着我的脚趾头,让我以为是我的白马王子在亲吻我?
恶心从我的胃里长出来。就在我要吐出来时,忽听得一声喝骂,死东西,你整天就这个死相,将被子拖出来干什么?六田,昨晚又死到哪儿去了?整天的在外疯,要是遇到长毛飞怪,将你吃了,倒让我省心了。
我的身体一晃荡,裹着的破棉被扯走。我的手腕一麻,那丑陋龌龊的小东西咬了我一口,唔的一声掉到地上,屁滚尿流地逃跑了。与此同时,我的鸡窝头被挠勾手一把薅住,我光着屁股,鼻涕眼眵直蹿,手腕上鲜血长流,被挠勾拖进了屋子。
你看看你像个人吗,好人死多少,为什么你就不死?我的母亲,将她的挠勾手一只叉到腰上,一只死死地薅着我的头发,支棱着麻秆似的长腿,唾沫星子从我的头顶直朝下泻。现在轮到我如那只丑陋龌龊的小动物了,在挠勾手下痛苦地扭动着赤裸裸丑陋的身体。
这会儿,我总用自己那双高深莫测的死鱼眼,恶狠狠地盯着地面,有一种将愚蠢玩到底的意思,一股冷笑从自己的肺腑里愤怒地爬出来,你就真希望我们死?有一天,我们真的死掉,你就开心了?
我的母亲没想到我会攻击她这么一句话,愣住了。她瞪着我诡异的眼神,在她的眼里,我就是一个怪胎。我点燃了母亲的怒火,她吼叫起来,养了你们这群王八蛋我开心过吗?我从早到晚睡过一次安稳觉吗?我没日没夜地苦,跟你们享过一天福了吗?你们这群不成器的王八蛋,还有脸说?怎么不钻地缝闷死,河里没盖子,怎么不投河淹死……
对母亲诸如此类的死法,我只有凶狠地眦着自己那睥睨一切的死鱼眼。而我的母亲,她是最怕我这种丑陋的死鱼眼了。
血呀,我可怜的小妹妹惊恐地看到了这一幕,她的喉管抽着细细的刮锅似的声音。
这声音钻到我母亲的耳膜,刺得她有点难受,她薅着我头发的挠勾手抖了一下,松开了。我哧溜地蹿到自己的房间,三下五除二地穿上了破棉袄破棉裤。说真的,并不是我有裸睡的怪癖,而是我除了破棉袄破棉裤,唯一能穿的一条裤头,昨天洗了,身上再无一物。离了破棉袄破棉裤,只能一丝不挂。
我顺手从身上棉衣的破洞里掏出一团脏不拉兮的棉花,朝流血的伤口一捂了事。这会儿,我的四个哥哥都起床了,他们对我早晨挨打的场景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无论我有怎么样的伤痕,似乎就是应该的。
院外有一种响动,我知道,那是粪勺粪兜的响声。我走了出去。我的父亲就站在院子里。他那四十五度的驼背结了一层霜。他的身上、嘴里、鼻孔喷着热气,我的父亲就像一头经过繁重劳作的牲口。
我望着犹如牲口似的父亲,心生怜悯,这是我九岁时内心最真实的写照。父亲每天一早必是出去拾粪。这时候,人和畜一夜的排泄物都舒舒服服地躺在每个大小角落,有的甚至还冒着热气,等着我父亲去捡呢。父亲收获到这样的成果后,就会放到自家责任田的粪塘里。
我的母亲,通常对我父亲是很鄙夷的,那种嫌恶的眼神是丝毫不用遮掩的,理直气壮的。我那四个哥哥更不用说,没人认为我父亲有存在的价值,也许他们从未想过,没有我父亲,哪有他们。我想对他们简单的头脑,这样的道理显得太深奥了。
我大哥三十岁,还没找上媳妇,在一九八四年的农村,他算得上极品大龄光棍了。其余的三个哥哥一字排开,我的四哥也十七岁了,都是识几个字再不肯读书的主。我母亲让我大哥学个手艺,指望有个活命的本钱。自从大哥学成瓦匠活后,其余的都是瓦匠,但因我大哥不是用心的角色,手艺学得半拉子,其余的只好都是半拉子。
我大哥算得上聪明,可惜过了头就不地道,游手好闲,手艺不当手艺做。在村里瞎晃荡。受他影响,其他几个哥哥都一样,跟村里一帮不学好的小杆子(小青年)混在一起,在村里干些鸡飞狗跳的破事。家里人不知为他求爷爷拜奶奶的谈了多少媳妇,没一个人看上他的。这不,昨天村里的四婶还帮他介绍一个。那个粗短的黑妞,睃着我大哥流着口水,感觉我大哥人样长得不错,想不在乎我家的三间茅屋。可我父亲偏偏出来递个茶水,他那皮包骨头牲口似的驼背,吓得黑妞一跳。尽管大哥唾沫溅了三千尺,说自己的父亲是邻居。可看热闹的邻居都笑了,偏黑妞又不是白痴,更觉得我大哥品德有问题,而且找女人迫不及待的心情更有问题,原先蹿出的一团小小的爱火,被南极的冰山熄灭了,看亲的人作鸟兽散。事后我大哥差点没痛揍驼背父亲一顿,我母亲也是杀千刀的骂早不来晚不来,偏这时出来,癞蛤蟆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将孩子的一门亲事又搅黄了。我母亲一骂起人来就会上瘾,口沫横飞狂喷到晚,直到一个邻居来家里拉呱,才将翻飞的唾沫掉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