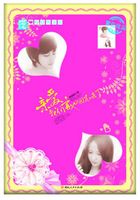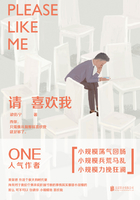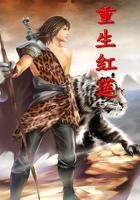来源:《北京文学》2004年第05期
栏目:现实中国
一个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的孩子,进入中学之后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变成了差等生、坏学生,这到底是孩子的错还是学校的错?按说家长是教育的消费者,该交的费用都交了,可孩子成绩上不去,做家长的反成了替罪羊,任老师传唤和训斥,这让身为家长的老周心里直搓火!
儿子13岁那年,他让儿子退学,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儿子18岁生日那天,他对儿子说:“我只养你到18岁,从明天起,你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吧。”而且一个子儿也不给。
周建湘和儿子子轩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却有一年多没见面了。父子俩拒不见面,对老周而言,是因为他一直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则——一个子儿都不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和儿子之间还不具备对话的基础。而对子轩而言,他也许是想用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事实给父亲一个“响亮的耳光”。
子轩18岁生日那天,老周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只养你到18岁,从明天起,你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吧。”
老周不但要儿子自立门户,而且一个子儿也不给,且说到做到。这不但让子轩恐慌,也让他心里充满了夹杂着怨恨的委屈。
其实,他们父子间的恩恩怨怨要从子轩13岁那年谈起。
儿子13岁那年,老周让他退学,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儿子子轩13岁时,老周作出了一个全家人都反对的决定——让儿子脱离正规的学校教育,从学校退学。他对儿子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周建湘的学历是教育学硕士。从兰州到海南,他先后在高校做了20多年教师。老周说自己是具有“父性”的教师:严厉、不虚假。他也一直在用这种态度做人、做父亲。
儿子的聪明人人都夸,上小学时,他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小学毕业时,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一所省重点中学。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子轩也许会按部就班地上高中,进大学,然后戴上一个学士或硕士、博士什么的帽子。
子轩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也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特点(是特点,而特点不一定就是缺点),调皮,不听话,坐不住。他上的那所省重点中学是个培养大学生的地方,能进那所学校的都是经过一番拼搏才挤进去的学习尖子。拿老周的话说“一个个都是学习机器”,而且都特听话、特循规蹈矩。
子轩似乎与这样的环境格格不入,很快就成为班上的“捣乱分子”,成绩也起伏不定。刚上初中的男孩子,正处在朦朦胧胧的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开始发生突变,他的捣乱也许是为了吸引老师和同学的眼球,也许就是荷尔蒙冲动。可是老师却不愿这样想,很快就将子轩打入了另册。老师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有他的难处,更何况是重点中学的老师,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高考。为了这个终极目标,他们常常简单武断地将学生分成好学生和坏学生,优等生和差等生。老周至今都不明白,一个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的孩子怎么一下就变成坏学生、差等生了,这是儿子自己的错,还是学校的错?反正老周认为不是家长的错。
老周和妻子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训斥”,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面前,听满脸怒气的老师历数子轩的种种不是和“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的指责。回来后,子轩的臀部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经常在学校走动,老周开始注意观察儿子受教育的环境。他发现,孩子学习的教材大都还是他当年上学时学的教材,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语文课本是最具人文特色的课,可是对于学生来讲,连最基本的精神自由都没有——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写长城,必须联想到解放军。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而是学着说假话、套话、空话、大话。而所谓的科学教育其实就是题海极限训练,本来一年就可以掌握的知识偏要熬上五六年,把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都磨没了,结果都训练成了“二傻子”。各科教学都是“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认识规律”,学生学到的都是“定论”或“结论”,学到最后以没有问题而告终。
老周认为,如今的学校仍然完好地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生产特性,仍在有计划、有模式、高速度地批量生产着人造新品种。学校教育实际上是“好孩子”教育,教出来的孩子从小就长得像真理似的,没什么缺点也没什么优点。
老周说他每次到子轩学校去,总会产生一个奇怪的联想,他会想到AA鸡。AA鸡是美国人用遗传优育技术培育的一个生物品种,从出壳到上市不足两个月,料肉比接近2∶1。AA鸡的特点是:笼养,只吃精饲料;早熟,几无性别特征;群居,安定团结无动乱倾向。此物种成长的唯一目的是增磅增磅再增磅,达到料肉比的最佳值时接受人类的宰杀。
回顾儿子退学后所遭遇的一切,老周说:”我可能会检点、反省自己在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上的得失,但永远不会为孩子当不上AA鸡而后悔。”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