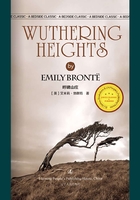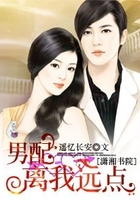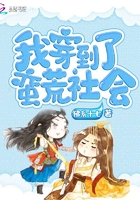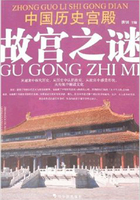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4年第01期
栏目:长篇小说
引言
一辆轿车在山间的土路上行驶着,车内端坐的丁苟怎么也无法摆脱那双眼睛,这是一双祥和、安宁、不时流露出对故乡眷恋的眼睛,可自己怎么老感觉到这双眼睛流露出一种杀气呢?为什么老是把这双善良的眼睛与鹰隼般的眼神划上等号呢?是自己老了出现的幻觉吗?好像不是。这鹰隼般的眼神又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呢?仿佛是在梦中留下的印记,但他内心一再肯定,这眼神在自己的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应该是在战争年代敌我双方对峙中留在自己记忆中的,不是梦幻,更不是自己无中生有。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双眼睛呢?人家是台湾老兵,难道是在土地革命或解放战争中的某一战斗中相拼杀而过目不忘?是哪一次战斗呢?他穷尽自己的搜索,无果。打的仗太多了,辽沈战役中的黑山阻击战,白刃格斗十几次,怎么记得是谁呢!不对,这双眼睛不是一瞬即过,它在给自己留下深刻烙印的战斗中出现过多次。此时,这双眼睛温馨祥和,不带半点敌意,“唉”,他轻叹一口气:“人说年纪大的人是以前的忘不了,现在的记不住,我连以前的也记不住了。”
陈保上车后不久就意识到,与他同一车厢的这个满头白发的精壮老汉是共产党军队中的一位高官,当他第一次直视自己的时侯,他猛然一惊:这是一双熟悉的眼睛,一双在敌我相争、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四目相对,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眼睛……
逝者如斯,国共两党面对面血火相争的日子已过去近六十余载,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嘛。不去计较,也不去想它。
他缓身倒在卧铺上,费力地抬起这只伤腿,抬起这只拖累了他一辈子的腿,脑海中又浮现了在贵州境内的一次战斗……
突然,他心中一颤,自己转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刻,面对的难道就是这双眼睛?一双充满着仇恨,喷着火光的眼睛?他一下子坐起来,平息内心的紧张后搭讪一句:“老哥,你是往哪里走?”
“去一个以前打仗的地方,看看战友。”对方迎着他的目光,淡淡地回了一句。双目对视的这一瞬间,陈保感到对方眼神中有一丝困惑和警觉,而自己则看清了——就是他,抬着驳壳枪,直指着自己的头颅,双眼喷火,一步一步地迈着坚定的步子朝自己走来,要拼个你死我活的红军长官。看着周围已经步步紧逼的红军队伍,他知道自己此时无路,但作为国军之营长,黄埔之骄子,他不愿也不能被这些衣衫不整的赤匪俘虏,他毅然转身,身后是陡峭的悬崖……
所幸,半山腰中伸出的一蓬蓬树丛救了他一命,但他腰部负伤还摔断了这条腿,脸上这道长长的划痕给他留下了永生的印记。因为这些,他离开了一线的指挥岗位,这是他人生的转折!不然,一个大有作为的黄埔生,官阶绝不可能戛然而止!就是这双充满仇恨的眼睛迫使他杀身成仁后侥幸存活,终止了他一线拼杀的使命,那是命呀!这双眼睛已经烙上自己生命的印记,永不能忘。今天可以肯定,就是他!虽然现在他岁月染霜,两鬓雪白,但那双眼仍炯炯有神,咄咄逼人。
眼前的这位共军长官仿佛也有所悟,但还未回过神来。“他的经历应该比我多,他想不起来,就让他去想。这是在大陆,在共军掌控的地盘上,自己千万不要造次,不然后果难料。”
陈保回身重重地靠在卧铺上,硬硬的床,软软的枕头,休息吧,拼杀一生该休息了。“你共军掌江山,我送兄弟骨灰回故土,两不相干。”只是他没想通:“为什么这双眼睛我一见就认出了他,他却没弄清怎么回事?这些共军要么是经历太多,这样的事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碟小菜。要么他们都是打仗不要命的土包子,不在意那些性命攸关的事。性命攸关哪!那一刻都是命悬一线的人,要不是自己已经枪中无子弹,眼前这位神气的共军长官早就是自己的枪下之鬼,化为黄土一杯了。同样,自己当时转身走向悬崖的那一刻,想着即将到来的是射向自己的一排子弹,但枪声没再响起。如果当时那枪声一响,自己也肯定命丧黄泉。这都是命,命中注定。”
丁苟沿着高高的石梯拾级而上,他的前方是一座高耸的纪念碑,泛白的纪念碑上鲜红的字体表明这碑是新立的。碑上那鲜红的字体,在他眼中仿佛是数千红军流淌着的鲜血。这是一段被人为湮没的历史,今天终于昭告天下。当他看到“红军在此遭受惨重损失”时,泪水禁不住悄然而下。他心里淌着血,这血仿佛与他已在此捐躯的战友们的血融在了一起,流在这片土地上。
他默默地转过身来,眼前一座座山峰兀立,山峰不知,山峰无奈,当年这座座山峰上吐出的火舌一片一片地吞噬着红军,吞噬着他的战友,倒下的红军一个压着一个,身上流出的鲜血一点一点地汇集,最终形成一股股溪流从山腰往山下流去。负伤的战友在血泊中呻吟着、挣扎着……
当年阻拦红军的深沟,现在是一道不深的土垄,当年架在这深沟之上的水槽已不知所踪。岁月有痕也有知,当年一排排地倒在深沟的红军,那呼喊的声音震动天际,至今仍在他耳边嗡嗡作响。
丁苟慢慢地走下这高高的台阶,左边就是当年那个笼罩在大雾中的小镇,他的远房叔叔就血洒镇中。小镇今天已初具规模,略显繁华,全无昨天的模样。岁月在这里延续,历史在这里进步。那场战斗的印记,已被时间冲刷得荡然无存。今天的甘溪已经没有半点当年的模样。想到甘溪他又突然想到了那双眼睛,那双鹰隼般的眼睛:“难道是他?”这个念头刚浮起,马上又否定了它:“不,不会。我亲眼看见他跳下了悬崖。”
回到宾馆,丁苟久久不能入睡,那双眼睛总是在他脑海中闪烁,难道真有那么巧合,那么不可思议吗?这是发生在十个小时之前的事。
火车缓缓地在站台边停了下来。上车的人流中,一个须发皆白的小个子老人使丁苟感到好奇。原因是这老人应该八十有余且衣着光鲜新潮:大红条纹的衬衫,配以细麻纱的灯笼裤,怎么看也不像一个老年人的打扮。其次是这个老人个子很小,腿也不方便,应该是有伤,可他却背着很时髦却又很沉重的双肩包。包内的物品很沉,已经将这个包拉变了形。他不时抬抬头,看着一个又一个从车上走下的人。他那新潮、质地很好的红条纹衬衣,也被这个沉重的背包压皱了样,挤变了形。
下车的人没了。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人。上世纪九十年代,能坐软卧在中国还是一件奢侈的事,若乘车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还必须是相当级别的领导才行。普通公民能乘坐软卧的,要么是大款,要么是大腕。
老人缓慢地走向车门。抬脚奋力地蹬上列车的踏板。一次,没上去,是因为他的腿伤,也因为这背包太沉。丁苟看见他双手拉住门边的扶手再用力,就快走两步用双手帮他托住包,老人一下感到背包轻了许多,没费劲就上来了。他蹬上两级踏梯,回身报以微笑:“谢谢。”他身后的人也是古稀之年的人——一头雪白的短发配着黑红的脸庞,额上的皱纹深刻且有力度,特别醒目,也特有精神。
走进车厢,老人找到座位坐下,正思量着将这沉重的包往哪里放时,他注意到他身后的那位老汉也跟着走进了车厢。他再次打量了一下这个曾助他一臂之力,又与他同在一个包厢的老汉:中等身材,胳膊显得粗壮有力,硕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对很不对称的招风耳,左耳大右耳小。再仔细看,右耳小,是因为右耳的中间缺了一块,耳轮因而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他那宽大的白衬衣下是隆起的腹部。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一个提着行李的年轻人。
“小赵,帮这位大爷把行李放一放。”刚进车厢的丁苟一脚踏进去后又退了出去,朝身后的年轻人吩咐道。
“是,首长。”身后的年轻人一声应答后闪身进了车厢,将自己的行李往座椅上一放,转身提起老人的背包惦惦重量,很沉,放在行李架上显然不行。他干脆将包往地上一放,摆平,再用脚使劲一推,推到座椅下面。动作是一气呵成,看得出他是经常做这类事的。
这一分钟的耳闻眼见,让老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特别是对方那双眼睛。他听这个年轻人称其为“首长”,立刻明白眼前的这位老汉可能是共产党军队的一位高官,这个年轻人是他的随从。他想自己与对方应该是多年前曾拼死相争过的对手,今天居然坐在同一个车厢里了。眼前这位壮老汉,年龄也应该有八十左右,既然是共产党军队中的高官,说不定自己还与他在哪次战役中交过手。
“老大哥,”丁苟的这一声喊,将老人从沉思中唤醒过来:“看你这身打扮,是从国外回来的吧?怎么带那么沉的包?”
“不是国外,是从台湾来。”老人回答一句,又下意识地朝放包的地方看看:“这包里没什么东西,就两块石碑。”
“石碑!背着石碑上软卧车厢?真稀奇!”丁苟不解地看了看这位老人,忍不住又发问:“背石碑干嘛?是碑刻还是……”
“不是,是给死人立的碑。”老人似乎不愿多讲。
“哦。”丁苟点点头,他感觉眼前这位老人有些冷淡。
窗外的田野在骄阳的炙烤下泛着一片一片的白。地里的庄稼和小树小草在太阳的注视下低着头,飞快地朝着后方闪去。疲惫使车厢里的人与外面的小树小草一样,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似睡非睡地靠在车厢上。
这位来自台湾的老人就是陈保,湖南大庸人,黄埔军官学校八期步科学员。他一生从军,与红军、日本军队以及解放军均在战场上交过手。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军队溃逃台湾后,继续在军队中从事参谋工作,官至少将。退役后过着休闲舒适的生活。正因为休闲舒适,才有了这次大陆之行。
他们一同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又同在一支部队共事的七个兄弟,一人在与红军交战中阵亡,有两人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捐躯,还有一个在国共内战时期的徐阜会战中下落不明,剩下的三人逃到台湾。几年前,那两位兄弟相继病逝。两人临终前对陈保的托付是惊人的一致:一定要陈保带着他们的魂回故乡走一趟。陈保听得懂两位兄弟的托付,或是人生经历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这两个相同的托付成了他这几年不懈追求的事。起初他想做,但办不到。因为当局正严格推行“三不”政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这三个“不”对他这个曾是国军高官、一生均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来说,如同三道比海峡还深的鸿沟,因为当局的禁令不能公然违背。但两岸人民血肉相连的同根之情,也不是几条禁令就能禁止的。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轨迹,他没想到,也没料到,当历史的进程走到了那一刻,两岸民众的交流瞬间就成为了现实。从开放两岸探亲的第一天起,完成两位兄弟的遗愿就成了他夜不能寐的事情。他知道,必须立即着手此事,不然,自己的余生将索然无味,也会留下终身遗憾。
怎么回去呢?两个兄弟的遗骨早已入土。他想起了他家乡的风俗——“赶尸”。这个在湘西盛行的习俗是亲人在外乡去世后,家乡的亲人要聘请赶尸人远赴他乡,将在外乡去世亲人的灵魂引回故乡的习惯。他虽然不相信人有灵魂可赶之说,但认为这是一种寄托亲人哀思的方式。还好,他在从军之前当过石匠。他决定将两个兄弟的姓氏卒年等相关内容刻在一块小石碑上,将小石碑埋在他们故乡的泥土里。也算叶落归根了。
这两个兄弟一个是贵州玉屏县人,一个是贵州瓮安县人,故乡离得不远,还顺路。到大陆后,他特意去买了一张大陆现在的交通图以确定行走的路线。他在宾馆的房间里用放大镜在地图上查找玉屏县与瓮安县时,突然,一个久违的地名跳入他的眼帘:“石阡!”他感到自己的血压在升高,拿着放大镜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再找,不远处,又一个记忆深刻的地名就在石阡县的左下方:“甘溪!”这个在他脑海中不时游荡着的地名,又一次浮上眼帘。
这个地方有他从军一生中经历最为不解,结局最为莫名其妙的战斗。也是自己最为不堪回首的战斗经历。说最为不解,是因为在战斗的第二天清晨,被数十倍兵力还有周围几个县上千人的民团昼夜搜索防范、铁桶一般围住的红军六军团,在那个雾满山峦的清晨,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毕竟是几千人的部队,他们怎么可能像那笼罩着大山的雾一样,随着阳光的升腾消散于无形呢?
阳光将大山的深壑照得透亮时,我军经过一天的激战,以偷袭、伏击等多种战法给红军以重击,其主力部队死伤累累,并被紧紧锁住包围。这个早上,胜券在握的我军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强大的火力扫射之后,国军兄弟们朝着固守一座孤山的红军发起攻击。持续一天惨烈的拼杀声,惨叫声,像刮风一样的射击声,此刻都像散去的雾。激战过后的山岭寂静得可怕:随处可见拼弯的刺刀、砸坏的枪托、红军遗弃的大刀梭镖,还有一堆一堆的尸体铺在这山间树丛中。这里实实在在发生过惨烈的战斗。但现在呢,几千人的红军除少量宁死不屈的重伤员外,活着的人没找着一个。
这是场奇怪的战斗。他清楚地记得在发起总攻之前,他听见红军阵地上传来一声爆炸。他站在指挥所掩体内,循着爆炸的声音往红军的阵地上瞭望,清楚地看见这山腰的密林深处升起一缕雾,一缕带着血色的雾,在阳光下泛着血腥的光,朝山间散去。这血色的雾从容缓慢地溶入阳光。这缕诡异的雾后来成了一根无形的绳,捆着他,在他心中几十年不曾散去。
那股被打散,已经与他们主力部队失去联系,流窜在这一带的小股红军,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肆活动。最后在自己围剿他们时反遭他们的突袭,数十个兄弟力战而死,自己也被逼跳下悬崖。
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要去甘溪,去重新品味那场战斗!去解开那困扰他几十年的谜!他要把在他心中飘了几十年的带血的雾从心底彻底驱走。他经常想:“如果那场战斗是按常规进行,红军没有在战斗的最后时刻遁于无形,那将是什么结果?得到的情报和红军的拼死抵抗都表明这支被围的红军队伍中,有数名国民政府悬赏数千大洋的共产党高级将领。还有,那缕雾怎么会泛着血色呢?”
那个地方又是他心中永远的痛:“要是自己不轻敌,特别是在那个他们突袭民团的夜里,如果自己主动出击,那又是什么结果呢?”历史没有如果,逝去的时间就是历史,时间不会再重来一次,不堪回首的战斗使他不敢再亲临其境。
“老大爷,为去世的人立碑为什么一定要从台湾背过来呢?那么沉。”小赵的一声问话,把陈保从遥远的遐想唤回现实中来。
“哦,你是问我?”陈保回答道:“那是我亲手为我两个兄弟做的墓碑,他们临终前念着想着的是故乡。我给他俩做两块石碑,送到他们的家乡,埋在家乡的泥土里,了却他们的心愿,让他们能嗅着家乡的泥土长眠。”他轻叹一声,自语道:“家乡呀,是我们台湾老兵永远缠绕在心中的痛。了个愿吧!”
“台湾老兵”坐在陈保对面时,已经轻轻打鼾的丁苟突然睁开了眼,那锐利的目光顿时像两道闪着寒光的剑直刺过来。陈保立即就感到这目光似曾相识。陈保暗想:“这人一定是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是有着丰富阅历的人。这眼神,也是我见过的。”
陈保判断正确。丁苟现在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离休干部,是从一个大军区副职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按现在的军衔应该也是中将级别。他的姓名很不中听,容易让人听成“丁狗”,但他原名确实也是这个意思。穷苦人家嘛,生个小孩不容易养活,什么猪呀狗呀命贱,反而容易活下去。在江西吉安红军扩红时,他报名参加红军。
红军问他:“姓什么?”
“姓丁。”
“叫什么呢?”
“小狗仔。”
扩红的女红军一听就乐了:“你们叫小猪小狗的人还真不少。参加红军了,别人都改了名,你也想一想,改个名吧!”
“我不改,这名命大。”
“那就叫丁苟,怎么样?”
“行。”
其实姓名嘛,就是一个符号,只是在战争年代这样的名字经常受到嘲笑。仗打好了,得到的表扬是“狗日的,打得不错。”仗打得激烈之时,那更是满耳充斥着“狗日的,你一定要顶住”、“狗日的,你一定要冲进去”等难听的语言。得表扬不管你叫什么,因为高兴。战斗激烈也顾不上你叫什么,那激烈的战斗中,比这难听的语言多的是。“狗日的”只是小菜一碟,谁也不会去计较。战斗失利,那麻烦大了,经常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而且主语或者是前置词都是“狗”。仗没打好,心中惭愧,不想也不敢去计较。能计较的时候,很少听见这种叫法。倒是丁师长、丁参谋长、丁司令这样的称呼不绝于耳。能叫他“小狗仔”骂他“狗日的”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
听到对面老人的一句“我们台湾老兵”时,丁苟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睁开眼睛向对面盯着看了一阵。他自认为自己的目光是很犀利的,但今天这个被他盯着的台湾老兵则若无其事,神色坦然。他暗自思忖:“这个台湾老兵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为了完成兄弟们的遗愿,背着自制的石碑到大陆,其表达的意愿与行事的方式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眼神好像有故事……”
“老大哥,你这次回大陆,就单为你的两位兄弟还愿?不到自己的家乡和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家乡的建设嘛。”
陈保见对方的语言诚恳、态度随和、提的建议也合理,就欠欠身回答道:“回来一次也很不容易,不仅要做成这件事,也准备到各几个地方去看一看。家乡嘛,留到最后。”
“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丁苟又问。
“主要是为战友还愿,是否到几处记忆深刻的地方看一看还没想好。”陈保补充道:“很想到几处仗打得激烈,一直忘不了的地方看一看。”
“打过仗的地方?”前面就要进入贵州境内,丁苟想:“难道他在贵州境内也打过仗?”在贵州境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正规军基本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斗。只有红军时期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贵州与国民党军队有着数次惨烈的战斗。让这位台湾老兵记忆深刻的战斗,就是与红军的作战。想到这里,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丁苟又问:“前面就是贵州,你在贵州打过仗吗?”
“打过。开始是一边倒的仗,他们很惨,主要是他们钻进我们的套子里了。后来嘛,后来的仗就不说了。”陈保这几句话喜忧参半,回答得十分平静,但他那双露出了几分狡诈的眼睛又在丁苟眼前扫了两个来回。
“这双眼睛是在哪里见过。”丁苟迎着陈保的目光,内心再次进行判断。说到打仗,红军在贵州有几次大的战斗,娄山关战役是我军主动出击、敌军伤亡惨重、我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的战役。青杠坡战斗虽说失利,但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一渡赤水摆脱了敌人。还有红军九军团在金沙老木孔的激战,那是红军设套却钻进了敌人圈套的战斗!丁苟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残缺的右耳,他一路都在惦着的地名一下占据了脑海:甘溪。“难道甘溪战役有他?”
丁苟此行的目的地正是甘溪。甘溪战役的纪念碑已经落成,他要去看一看这个数千红军血洒的故地。数名亲密的战友和许多他认识与不认识的同志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要去探望他们,与他们共叙数十年的离别之情。同时,他还想找一位老乡。正是这位老乡,将已经弹尽粮绝,身陷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的红军从绝境中救出来。这是一次绝处逢生的经历。丁苟和他的战友一刻都没有忘记这位救出红军的老乡。解放后,听说地方政府找到了他。一个老实巴交的大山山民,关键时刻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深入绝境救出几百名红军,是何等的伟大!他要带去幸存的战友们的问候和谢意。
历史就有那么巧合的事,当年拼死战斗的对手,今天坐在了同一车厢。他俩确实在战场上交过手,地点就在甘溪,一个双方都经历了胜利和苦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