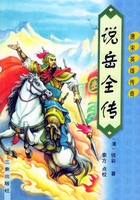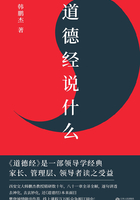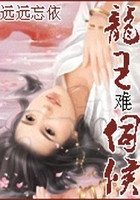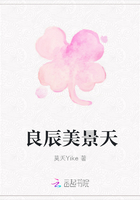春老了,草也老了,夏天轰轰地来了,原野成了一个绿色的海。连招学会了刮绿肥,用一把小镢头,把猪鞭菜、狗尾草、打碗花……都刮下来。刮满一筐,交队上,记分员记过数,就倒粪池里了——好大一个粪池!全队社员交的绿肥都沤在里面,一层层压上牛马粪、人粪尿,在太阳下晒着,没几天,草也化成粪肥了。大粪池在阳光下咕咕冒泡,像文火炖着一锅稠粥。虽然臭一点儿,孩子们还是喜欢看。男孩子还喜欢往里扔石子儿,眼看着石子儿丢下去,粪池冒出一串泡,蠕动着嘴,一会儿工夫,石子就给吞下肚了。男孩们更兴奋了,扔得愈起劲。但是队长一来,轰一声,就黄蜂似的散去了。
连招不扔石子,但是她喜欢看粪池冒泡;她也喜欢上了刮绿肥,随身带着个小筐子,带个木楔子,把小羊往草地一钉,什么都不耽误。她爸她妈很高兴,说连招勤快了,说连招的勤快都是苏巧带的。他们很喜欢苏巧,跟老光棍和苏巧妈说话也客气了。
苏巧妹妹大了些,会坐了,苏巧就随身带一块旧布和干活的家伙,到了草多的地方,铺下旧布,让妹妹坐上去,她开始干活。那时计划生育还不怎么普及,村上孩子很多,大人又没时间照管,在野地里乱蹿乱跑的,有的义务做了苏巧妹妹的临时看护。苏巧就趁这机会抓紧干活,镰刀霍霍舞起来,很快割出一筐猪羊的食料。
那时候闲地多。也不叫闲地,叫绿肥地。蓬蓬轰轰地长满了苜蓿、田菁、苘麻、蓖麻和别的野草。夏天一到,是草是绿肥都开花:苜蓿开紫花,田菁开黄花,苘麻也开黄花,蓖麻开很小的猩红花——艳极了,但是太小了,几乎没法子摘。这时候女孩子总喜欢去绿肥地玩儿,紫花黄花摘了一捧又一捧,自己头上戴,再给伙伴戴。然后,扮起戏文来。做主角的,一般都是连招。连招任由她们撮弄:头上戴一条长手巾冒充戏里的长辫子,黄花紫花插一头!几个女孩叫:“娘子——!”翘着兰花指,翘得又不得法,一个个奓着两只手。连招的眉心点一粒血红痣——紫穗槐割了去,新生的嫩芽儿一掰,就淌出黏稠的血红汁液来,拿来点在眉心间,比印度妇女的吉祥点还要艳几分;耳垂上粘两朵苘麻花——这花黏性大,一粘就粘得很牢了。因此,虽没有脂粉,还是扮得很艳。她们扮《花为媒》《朝阳沟》《西厢记》《马兰花》……一样样演起来,苏巧混在中间,也能演点儿什么。这时候她总快乐得像是过节,什么烦难、劳累、喝酒的爸、苦着脸的妈,都忘脑后了。连招演小姐,她演丫环;连招演新媳妇,苏巧演婆婆。然而——苏巧发现,连招生得惹眼、胖大,但是她的心眼儿要比她的身体发育滞后很多。她几乎完全没有心眼。演小姐、新妇,再是俊,再是风光,都是丫环和婆婆的掌中物,想怎么安排怎么安排,想怎么拿捏怎么拿捏,连招的事,连招自己不知道。
连招演的小姐叫:“丫环,扶我到花园看看。”苏巧演的丫环上来,搭着连招的胳膊,扶她到苘麻地边转了一转,说:“小姐,张公子来信,叫你晚上在花园等他。”连招说:“哦。”于是,一回身,就晚上了,连招到苘麻地边,翘着个兰花指等着。另一个女孩扮演的张公子来了,道一声:“小姐——!”
连招演新媳妇,挑开一道并不存在的门帘,问:“婆婆,今天早上喝什么茶?”苏巧演的婆婆搭拉着眼皮子说:“白糖鸡蛋茶!”连招转过身,捧着一只麻叶杯来了。苏巧一边喝“茶”一边吩咐:“去叫车,今天走亲戚!”连招又“出去”,就有个女孩拖着根树枝来了,嘴里模仿着拖拉机的声音:“嘣嘣嘣嘣嘣……”
小孩子做戏,大人也爱看一眼。他们割苘麻,牵着驴儿打滚,瞧一阵子戏,有人就说:“连招吃饭光长个儿,不长心眼!”
也有人说:“别看苏巧瘦瘦小小,这丫头有心思,长大能当家!”
旷野的风吹来又吹去,吹到连招耳边,跑了。苏巧却抓住了这些声音,她心里有小小的扬眉吐气:长大,长大就好了。她一下子想起那些戏:贫寒公子中了状元。
夏天慢慢也老了,苘麻割下来,沤到水塘里——很青很绿的一个水塘,沤了几天苘麻,水就红了,红得像一汪胭脂。大人赤着脚,下到胭脂样的水塘里,把沤好的苘麻捞上来,剥皮,雪白的麻秆一般是用来烧锅的,孩子也爱拿来做玩具,挥着,舞着,模仿刀枪剑戟的战争。麻皮晒干了,梳好了,可以搓绳子。有人家死了人,孝子孝媳妇就把未梳的粗麻勒腰上,长长的在地上拖着——要不怎么说是披麻戴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