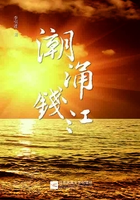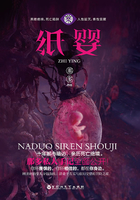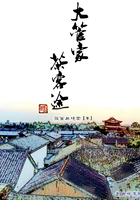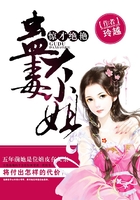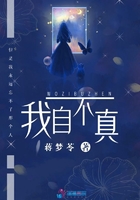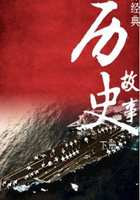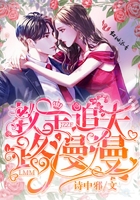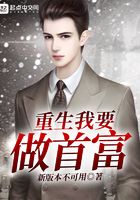来源:《星火·中短篇小说》2007年第06期
栏目:重磅中篇
大老刘进校时,是我们年级年龄最大的一个。
那是“文革”结束后的七七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为了缓解全社会人才匮乏、思贤若渴的燃眉之急,这次招生对历经坎坷的“老三届”年龄不限,政策从宽,显出令人感动的垂青与怜爱。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最初那两届大学生,“老的八十三,小的要人搀”。
那时我们在大教室上课,课间我发现有人对坐在前排的一个同学指指戳戳,悄悄议论,神气里颇有几分好奇与惊诧。那同学,短发,敦实,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卡叽中山装被他粗短的身子撑得紧绷绷的,感觉上与其说朴素,不如说寒碜。
他就是大老刘。
大老刘确实不小了。当时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二十出头,最小的应届毕业生仅仅十八、九岁,这一来,三十又六的大老刘跟大家在一起,就不仅是老大哥与小老弟的差距,简直是两代人了。其实生活中三十大几充满朝气充满活力与小年轻滚在一起搅合在一起的人多的是,可大老刘与之相比差距远矣。大老刘的“老”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老,一种精神性的老。古人说“枯藤老树昏鸦”,如果用“枯藤老树”四字来形容大老刘平时的形状,真是再准确再贴切不过了。什么叫“老气横秋”?你只要看一眼我们的大老刘,包你对这个成语的含义全部领会。
有一件事,大老刘给我的印象极深。
七九年,文化政策放宽,学校给我们放映一批开禁电影。电影在露天放,学校将篮球场用绳子一圈,想看电影的同学缴一毛钱即可入内。那时同学们每人都有一张小板凳(学校发的,押金两元,丢失不退),看电影时带着,黑鸦鸦坐下一大片。一些对看电影收取一毛钱(那时一毛钱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心怀不满的同学,便对学校采取了流氓无产者式的抗拒——只坐在绳圈外,等电影放了一刻,趁朦胧夜色,头一低,腰一躬,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入绳圈。其时大老刘也属远远坐在绳圈外面看电影的少数同学中的一个,他跟他们所不同的是,他始终坐在那里,从电影开始一直到电影结束,脸仰着,肩微微塌着,身子不动一下,保持一种雕塑的姿势,到后来,那些机灵的同学已像一尾尾鱼钻入绳圈,可他仍在那里,孤伶伶的,像独守寒江的一只笨鸟。
在大家印象中,大老刘是个沉默如金没有脾气的人,他就像山里的一棵树,一块石,一眼泉,跟大家隔得很远。但到后来,大家突然发现,原来世上根本没有永居不变的事物,过早给大老刘作出上述结论显然有失草率。理由是,大老刘与同宿舍的姚小元“翻”过一次脸。
事情发生在国庆节。那天,住在本市的同学都回家过节了,没有回去的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到公园划船,或上街遛达,临了找一家不太贵的小酒馆,摹仿美国西部牛仔的豪气,吆五喝六地闹腾一下。那天傍晚,大家勾肩搭背哼哼唱唱喷着酒气回来,推开宿舍门,不由一下愣住了。
宿舍里简直跟发生过地震一样,每一张桌上,每一张铺上,都被翻过,那乱七八糟的状态使你觉得宿舍里闯入过一群飞天窃贼。宿舍里静静的,这种静类似于风暴或地震发生后的那种废墟式的死寂。
有一个人躺在铺上,一动不动的。是大老刘。
姚小元弓着腰头伸到大老刘床头,“喵”地学了一声猫叫,神经兮兮道:“烦问刘大人,我们宿舍这番乱相,可是齐天大圣到这儿走了一遭?”
大老刘身子往床里翻了一下,不理他。
姚小元不肯善罢甘休,“刘兄,外面秋阳如金,风景如画,你阁下这般陇中高卧,可是情场失意?”
大老刘对这戏言,就像一头老牛对待嗡嗡作响的苍蝇与蚊蚋。
姚小元耸肩摇头,觉得无趣,只得转身跟人下棋去了。
可是大老刘却从床上蛇一样冷幽幽把头昂起,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笔记本?”
这一下轮到姚小元摆谱了,他面对棋盘,手往对方脸上一点,
“快呀!走棋呀!走棋呀!”
“你有没有看到我笔记本?”大老刘把脸转向姚小元问。
姚小元手里把玩着一粒棋子,脑袋向大老刘歪过去,两眼微眯,细声细气问:
“你说什么?”
“我的笔记本。”
姚小元惊呼:“笔记本?可是你放在床头天天看的那个红皮本子?”
“对。是它。”
“原来整个宿舍被搞得天翻地覆,一塌糊涂,都是因为找那个笔记本?”
“你有没有看到?看到就告诉我。”
“噢,噢,这本子我倒是很熟悉的,里面好像还有些……东西。”
跟姚小元下棋以及围观的几个同学都禁不住暗笑,觉得好戏来了。那本笔记本他们都看到过,时间就是这天上午。当时以姚小元为首的几个铁杆舍友准备出去周游,他们这一走,宿舍里就只剩下大老刘一个孤家寡人了,其时就有个细心的同学为大老刘一个人独守空房心有不忍(当时大老刘到盥洗间汰衣服去了)。姚小元下巴一翘很无所谓地说,你别烦他,他打发起时光来绝对水平高超,并且那种甜美与浪漫,你我一辈子望尘莫及。姚小元的这番话使大家感到如听天语。姚小元神秘地一笑说,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秘密。转身爬上大老刘的床从枕头下掏出一本笔记本。那笔记本是“文革”期间最常见的那种,硬硬的红塑料皮面,虽用的年数长了,但上面烫金的毛主席头像和一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金字依稀可见。姚小元将本子打开,大家立刻发现里面夹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七、八岁男孩,大眼睛,五官端正,有点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嘎子;一张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合影,那女的长得还可以,样子有些腼腆,一看就是七十年代作家浩然笔下的农村妇女。等到大家目光转向旁边那人时,大家的嘴一下张得足可放入一只汤圆了。
这不是我们的大老刘吗?
这女的可是他老婆?
这小嘎子是他儿子?
其实这种诧异与奇怪很没有道理,因为在这之前大家早晓得大老刘结了婚有家有室,但那似乎仅是个抽象概念,无法与照片上的内容联系起来。姚小元手里掂着那本笔记本,神秘兮兮地说,你别小看这破笔记本,它可绝对是我们刘老兄的心肝宝贝加精神食粮,晚上临睡前或周末宿舍没人,总要悄悄将它翻开,深入学习,细心领会,真有点到了韩愈先生所说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地步,那种如痴如醉陶然忘机的情状,绝非你我这些后生小辈所能想象的呀!姚小元说到这里,眼睛骨碌一转,立刻生出一个坏点子,鬼笑道,他马上回来,见宿舍没人肯定要捧读这本红宝书,我们何不把它藏起来,让他今天发一下急?大家觉得这个玩笑很有质量,立刻欢呼赞同!可宿舍就这么大,笔记本往哪藏呢?姚小元抓了两下后脑勺,一扬手,将笔记本撂上了大老刘的帐顶。帐顶铺着报纸,笔记本撂在上面一点看不到。
围观棋局的同学们见大老刘的脸很少见地阴沉下来,而且越阴越黑,嘴里说出的话已不好听,担心事情发展下去不好收场,其中一个就不声不响站起,足尖踮起,悄悄从帐顶取下笔记本放到大老刘床边。
大老刘抓过红皮笔记本,很生气地骂道:
“搞的什么鸟玩意!”
声音不高,闷闷的,状态类似于黑云深处滚出来的沉雷。
大老刘再一次引起大家的瞩目,则是后来三年级时候的事了。
记得三年级第一学期开学,大老刘坐了三年从未离开过的那个位置让人坐了。我感到很诧异,于是便把目光编成一张网在大教室角角落落打捞,可打捞了半天,始终没有大老刘的身影。我想,一定是他家出事了,要不然他怎么会不来上课呢?可是两三个星期过去,那个位置仍被别人坐着,大教室里始终没有出现大老刘的身影。
一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刚巧碰到姚小元,我便问他。
“他提前毕业了。”姚小元回道。
“提前毕业?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放弃本科,拿个大专文凭,立刻工作。”
“这是为什么?”我惊诧得像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姚小元很难得地叹了口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为人叹气),蹙着眉道:“没法子,最近我才听说,他家里很穷。他下放后,娶了个农村老婆,一直未能返城。老婆最近生病,家里快要揭不开锅了。”
我一时无语,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再没有话,心里在努力想象大老刘的近况:他那徒有四壁的草屋,他老婆躺在床上的病相,他儿子背着书包放学回来穿得破破烂烂的样子……我无法想象得很切实很细致。我一时只感到我想象力的贫乏。
姚小元默默望着路边花木,一路无话。
我也无话。
花圃里,花木蓊郁,鲜丽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