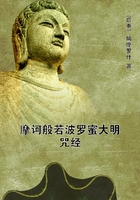十七岁那年刚放寒假,妈妈递给小河一张去长沙的火车票说,年就陪他过吧。
小河莫名其妙,问:“谁?”
“你爸爸,七岁那年你是见过他的。”
“你不是说我爸在我还没出生时就死了吗?”
“现在真要死了。”
在去长沙的前两天,何小河一直在回忆她七岁那年见过的男人,哪个是她爸爸。她只知道,那年总有人领着不同的男人到外婆家,妈妈看也不看,便把人家轰出去。
外婆叹息说:“我看这些人都比那个混蛋强,你咋就看不上眼呢?我要死了,你连个依靠都没有。”
妈妈说:“我有小河呢。”
现在想起来,外婆眼中的混蛋应该就是她爸爸。
好几次她想问妈妈,终究没张开嘴。她知道,那是妈妈一生的隐痛。
接站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见到何小河时表现出的兴奋让她有点不知所措。一路上,他喋喋不休,因为过度兴奋还有点语无伦次。
“我当年和你爸一起插队。你爸年轻时长得好,有才华,还会拉小提琴,也会做小提琴。”
何小河第一次听人对她很自然地说“你爸”,她感觉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你很冷吧?长沙就是这样,冬天又潮又冷。”
“你长得很像你爸。”
“你妈妈还好吧?”
何小河点点头。
“她这么多年就没再嫁人?”
何小河摇摇头。
“她还在村里的小学教书?”
何小河摇头。
“你爸爸两个月前查出肝癌晚期,一直在医院住着,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睡,医生都说难过年关。你来了,他一定能过得了这个年。”
“对了,我姓刘,你就叫我刘叔叔。”
“你有一个妹妹,叫小溪,十三岁了,上初二。你爸爸和小溪的妈妈十年前就离了,小溪跟了妈妈。你爸爸现在孤身一人,我们几个队友轮流照顾他。今天是我值班。”
“你和你爸爸一样,话不多。”
“天妒英才,我们一起下乡的,就你爸爸最有才,偏偏就他先倒下了,其他人都硬朗着呢。”
“可能是这些年想你想的,也想你妈妈,身体都想坏了。”
“当初他为什么不要我和我妈?”小河冷冷地问。
“当初,插队的人都发了疯似的回城,就是一块石头,也会被大浪卷跑的。再说你爸爸会拉小提琴,在乡下拉小提琴是很可笑的,你能明白吗?”
“那他为什么不把我和我妈带到城里?”
“他自己还没地方落脚呢。一会儿见到你爸爸可千万别提这事。你就让他舒舒坦坦地走。”
“他就没有别的亲人了吗?”
“你爷爷是大学老师,教哲学的;你奶奶在中学教音乐,你爸爸遗传你奶奶的才华。他们‘文革’时挨批,读书人面皮薄,自杀了。你爸爸有个哥哥,还有个姐姐。哥哥去年出车祸死了;姐姐在你爷爷奶奶死后就得了精神病,现在还在精神病院住着呢。”
“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
“不能叫‘这个人’,是你爸爸,见了面你得喊爸爸,要不他哪天去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何小河沉默。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天下起雪,越下越大。这场雪,一直下过了何小河的青春,下过了她的大学岁月,下过婚后的沉闷与琐碎,直到有一天被北京的灯火辉煌、摩肩接踵融化,变成冰冷的雪水融化在她的血液里。有一天朱颜改问她,来北京这么多年有什么感觉?她说,越繁华越孤独。朱颜改当时就哭了,她是个泪点很低的女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当上财经部主任的。
病床上薄如纸片的父亲,让人担心随时会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他的鼻孔里插着氧气管。
“老李,小河来了。”刘叔叔在他耳边说。
老李睁开眼,眼中的光芒让整个病房变得耀眼。他努力地笑着。何小河第一次听说这个给了她生命的男人姓李。
“小河,来。”
刘叔叔把她推到他面前,又搬来张矮凳子,按着她坐下,这样,她就能和老李平视了。何小河回忆起七岁那年,似乎见过他。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他抬起手,刘叔叔立即会意。刘叔叔把她的手放在老李手中,她立即缩了回来。
“手真凉。”
“你妈妈还好吧?”
何小河点点头。
老李看了看刘叔叔,又朝床头努力地扭扭头。刘叔叔拿起床头的小提琴盒放到床上。
刘叔叔打开琴盒,一只精致、漂亮的小提琴呈现在小河面前。七岁那年见到的那个男人像面前的大雾,时而散开,又时而聚拢。
“想起来了吗?”刘叔叔问。
“不要催她,让她慢慢想。”老李喘着气说。
歇了一会儿,老李说:“那年,我一整年都在做这把琴。以前一个月能做一把。这也是我做的最后一把琴。这把琴是一个兵哥哥定制的,他出了高出别人十倍的价钱。他的部队离我那里有点远,需要采购的时候,他才路过那里。他有老乡在小店旁边的军营里。你还记得我当时在一座军营边开了个小商店吗?你还指着墙上挂的小提琴问,这些都是你做的?我想送你一把,你外婆不让。
“中间他来过一次,你见过。那天你外婆带你来看我,我第一次见你。他来看他的琴做得怎么样了。我当时刚托人买到一块鸟眼枫木料。你把一个彩色皮球踢到马路对面,是他帮你捡回来的。他只停留了大约十分钟就走了。他走后一周,那座军营突然空了。他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后来听说因为裁军。再后来,军营变成养鸡场。我等了他两年,他一直没有来。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小店生意越来越难,旁边的养鸡厂变成养猪场,臭气熏天,我怕把琴熏臭了,就离开了。”
老李说完大口大口地喘气。刘叔叔说:“小河,我们出去,让你爸休息一会儿。”老李摇摇头,不让她走。
“你长大后,有空的时候,就去找他,把琴还他。”
“他叫什么?”何小河问。
“他没说。”
“我要是找不到他呢?”
“一辈子心里有个念想总是好的。人哪,就怕心都空了。”
“他长什么样?我记不起来了。”小河有点歉意地说。
“大眼睛,高鼻梁,宽额头,厚嘴唇,白皮肤,个头不高,笑的时候还有酒窝。他很特别,放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来。”
护士过来催促说:“病人说的话太多了,你们让他休息一会儿。”
第二天深夜,何小河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小河,小河,快,你爸不行了。”刘叔在门外大声喊着。
何小河跟着刘叔走出宾馆,又返了回去。
“怎么,小河?你爸不行了,你害怕见他吗?”刘叔焦急地问。
“我小时候学过小提琴,还会一点……”
“那你快去取。”小河听到刘叔声音有些颤抖。
赶到医院时,老李床边围了几个医生和护士,还有几个陌生的叔叔阿姨。心电图在发出停歇的警告。
“小河,快叫爸爸,要不来不及了。”刘叔推着她。
“快叫啊。”那些陌生的叔叔阿姨催促。
何小河打开琴盒,拉了一段《化蝶》。小时候,妈妈每周末都要带着她挤公交从小镇到市里,跟一个老太太学琴。妈妈很固执地只让她学这一段。她也只会这段,而且拉得残破不堪。老师告诉妈妈,她不是学小提琴的料。妈妈说,会拉这段就行。
那天,何小河被自己的琴声感动了,这是她拉得最完整、最动听的一次。当初那些残破不堪的声音是她故意造出来的,她不想挤半天的公交,去学一小时的琴。她的眼泪扑簌簌落在琴上,流淌到父亲搭在外面的手上。她看到父亲眼角滑落的泪水,她理解了父母的感情。但终究,她没有开口叫爸爸。
在父亲简单的葬礼上,她见到了那个叫小溪的女孩。小河冲她笑了笑,拉着她的手,捧着父亲的遗像,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关于骨灰的存放问题,父亲的队友们请来小溪,还有小溪的妈妈。他们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她和小溪一人一半。刘叔叔不同意,这不是把老李分开了吗?有人说,轮流放。这样小姐妹俩还有个联系。
何小河问小溪的妈妈:“阿姨,您已经成立新家庭了,对我爸还有感情吗?”
小溪的妈妈沉默。
何小河说:“昨天我明白了妈妈一生只爱我爸,一生也只强迫我做过一件事,就是学会《梁祝》的最后一段《化蝶》。她是希望死后和我爸葬在一起。”
四年后,小河的妈妈死于子宫癌。爸爸妈妈的骨灰埋在一起,葬于他们野合过的麦田。小河给他们立了碑。来北京的前夜,她在爸妈的墓前拉了一整夜的《化蝶》。
后来,她再没有碰过那把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