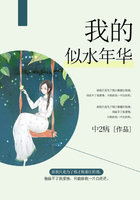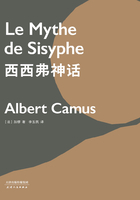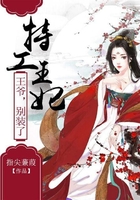来源:《鸭绿江》2017年第09期
栏目:小说
人们都在忙着过年。这年劲一上来就猛。离大年三十还有十几天,有人就在住宅楼楼前楼后舞着双臂抖起了嗡葫芦、学名叫空竹——嗡——嗡——嗡——空竹的发声孔随着空气灌入,发出特有的响声。这发声孔的数目分八响到二十四响,响数越大声音越大,空竹的材质一定是竹子的,不能塑料材质那种的,这声音上入苍穹,下入耳郭,传得很远,一听到这独特的响音,让人心中有点莫名的慌,有点喜,有点没着没落,连走路的步子都快起来。
淘气的孩子们在小区楼群里跑来跑去,衣兜塞满拆散的炮仗,手里捏支细香,香头红红地闪,点炮仗,“啪”“啪”,撩人的脆响。
当你初来乍到这座城市,印象是什么?成片成片的老住宅楼,土红暗旧的外砖墙,楼高六七层、也有八层的,如麻将牌横竖排列成一个一个区域。
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串门或住进来,会发现每座楼有三到四个楼栋口并被隔成四十多到七十多个不等的单元,每单元面积四五十平,小的二十几平,厨房、卫生间都很小,厅更小了,有的干脆没有厅。这座城市多数家庭住在这样的老居民区里。这里也有变化,政府让实行物业式管理,搁围墙一圈,成了一个个“小区”,太多了,都是这种普通小区。
平时不常见的面孔,打头碰脸多了。外地来河湾务工的、小生意人、初出道的外来城市白领,跟老河湾人混杂居住着。一女子拉旅行箱走出楼栋口,操生硬普通话打手机:是打车还是怎么样子的?……好的,好的。一听是上海周边宁波一带人。一打工哥穿皱褶西服,斜挎黑造革背包,背带从左挎过脖子。看来要回老家。他眼盯河湾名吃“煎饼馃子”——这是特别受河湾市民推崇的早点,摊煎饼馃子的在河湾城怎么也有上万家吧,人家做得地道的:纯绿豆面,双蛋锅篦儿(从前是煎饼夹棒槌馃子,老人们讲至少有百年历史,这算是改良品种吧),锅篦儿薄如纸,炸得金黄透亮,酥脆咸香,面酱甜咸适中,腐乳纯正,最后再撒上芝麻,那味道简直绝了。价钱,自然也贵点。可好多摊主别看不使真材实料,做的更稀孬,涨起价来,眼皮不带眨一下的。这会儿就听打工哥的乡音问:甚价钱?摊主现傲睨态:八块五。显然嫌贵。旁边一广西妹,她的特色普通话带着喜悦:快回家,河湾,晒,太阳太烫了。跟前烙烧饼大哥不爱听,大过年的,说哪门子三伏天,你们广西好,把人放罐儿里一样闷死。
许三越从自家老偏单走出来,他边走边望望步履匆匆的路人,心里在考虑一个问题,今年大年三十,全家在哪聚?
想到这,他就想起母亲包的饺子特别好吃,三鲜馅饺子,虾仁、肉、韭黄,特别是调馅这道活儿,她必亲手来,那味道绝了。他大学刚毕业时报名到青海支教一年,出发前在市体育馆集训一个月,母亲在清冽的秋风中,带一盒饺子来看他,用两块厚毛巾裹着,打开饭盒饺子还热着。
河湾这地方过年吃饺子有讲究。老三的妈素常俭省得要命,可是过年饺子早早准备开了,说三鲜饺子除夕时候吃,这叫——“更新交子”。素馅饺子,把绿豆芽、芫荽、豆腐干、木耳、粉团、黄花菜、冬笋、棒槌果子都切碎碎的,配上芝麻酱、腐乳、香油、蒜泥调拌。你光是看那馅,不怕您见笑,快流哈喇子了。老妈说,素馅饺子要大年初一吃,咱们寻常百姓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一年到头素素净净、碎碎(岁岁)平安。老三嘻哈哈说,您这老例儿简直是民间宪法。唉,三年没吃上母亲包的饺子啦。
今年还去大哥家,不行,他腿撞坏了。
去二哥家,怎么总也联系不上他。
就来我这小家,对。本来嘛,轮流坐庄也轮到我了。
他思忖着,迎面过来一“狗骑兔子”送桶装水的。这不老曹吗。老曹是自己老门口“发小”,多年没见,几个月前撞见了,撞见就认出来。他下岗后干送水工,给一片儿小区,还有驻这片儿的企事业单位送水,有个上湾区群文馆,老三就在那儿上班。
老曹也瞅见他,停车,屁股倚车座,俩人聊,三越问:“今年哪聚?”老曹知道是问大年三十团聚的事,“不聚了,聚不起来了。”老曹答。
老曹兄妹六个,他排行老六,这几年全仗着他大哥把一家子往一块拢。老曹兄妹们每到大年三十都到他们大哥家团聚。后来,他大哥闹场大病,命没保住。打那开始,家里再也没人张罗了。“唉,老娘没有这才几年,兄弟姊妹们基本不来往啦!”老曹闷声说。三越不客气地问:“你是干什么吃的?”
“甭提了……”老曹尴尬一笑,“我想张罗,没那能力。”然后问三越,“伯母身体还好?”
“三年前,过世了。”
“啊?”老曹一惊,“那你们哥几个在哪聚?”
“我大哥那吧,我们哥们儿还不错,走得挺近,有点事你帮我我帮你。”三越踩着便道牙子说。
老曹问,这是去哪?三越说,理个发。瞧你长毛贼了,一块儿吧。
门口挂块小牌“吴师傅理发点”。叫“点”,一屋一座那种,居民区里常见,不是大街上那种“国际”“全球”“环球”造型烫染连锁店;也不是外挂皇家、帝城、帝都,显示人上人耀眼牌匾的。三越在这理发十几年了,说起这吴师傅做的头等大事着实了得,脑袋到他手上就像把玩一件艺术品坯子,先使热毛巾给你擦两把,让你放松下来,然后只消十几分钟,蓬头垢面啦,胡子邋遢啦,就被他打理得一番新气象,人似乎还年轻了好几岁,收费还便宜。一牵狗男,狗前人后,跟个十来岁男孩,推门,并不进来,探过头,冲座上理发者扬下颌,吐字,这个完了。又转脖至小孩,复点下颌,意思给他理。老曹看个满眼儿,心说会说人话吗,见狗挡门口,嚷:“狗先进。”牵狗男斜眼儿,瞅老曹那大块头,没说话。
三越冲镜子看,不禁笑,座上的这不退休蒋老师,都在近旁住着。吴师傅扭头招呼,许科,来得够早班儿!呵,还带来一位。蒋老师从座上下来,招呼声三越,和老曹点头笑笑,问道:几位发现了吗,咱这几条街面上,报刊亭——改煎饼馃子摊啦,不卖《河湾晚报》、杂志了,摊煎饼馃子。吴师傅问,是吗?不对,工商(局)不是说可以捎带经营饮料、饼干、糖豆吗?蒋老师摇头,不行,来钱太慢。现在不叫自谋出路,叫“自谋收入”,变着法地来钱快,不管不顾了。
蒋老师的京腔继续说,我楼上住着这家,早晨卖煎饼馃子,晚晌儿还卖糖堆儿,北京叫糖葫芦。这大冷天,人心火大,吃串糖堆儿,甜、酸、凉、脆,让人胃口大开,好。看人家蘸糖堆儿——山楂,竹签串成串,文火熬糖,下锅快蘸,旁边早备一块平整石板,石板薄油,一串串往上平拍,晾凉后即得。呵,山楂果外罩冰糖,晶莹透亮,看着就直流口水。我楼上这家不,在家蘸好了,使篮子提到报亭卖,这也没关系,问题是他家里没有石板,使木板也行,抹点油,不,你看脚底下这地面吗,使湿墩布一带,还滴答泥汤子了,啪啪啪,水泥地上给了。
吴师傅一龇牙说(刚给小男孩理完),外面这屌样,家里能好得了。爹妈还活着啦,兄弟姊妹为房子、退休费、为点儿存款打成热窑了,还有骗的、偷的,为了钱嘛缺德事都干出来啦。
过去是什么?蒋老师叹口气,人心多安稳,一家一家的,生活水平,谁跟谁差距都不大。现在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的太富,穷的太穷。什么——你问在春萌小区那买别墅、原来住咱老门口那俩暴发户?
一说春萌小区老曹来了兴致,他咂咂嘴说:我一送水的,成天走东家串西家见得多了,现今小区跟小区比,差大发了。小区的人都是自个儿掏钱买房凑一块的,你有钱的就买高档住宅区房子,你没嘛钱就买普通、次小区的,人以群分啦。吴师傅插句,瞧人家高档住宅区住的,吃的,玩的,戴的,开的。老曹摆手道,那都搁其末末(天津方言:不经意间的意思)——让你下辈接着穷。人家官贵富豪区的人在孩子身上投资,上最好幼儿园,中小学。买学区房,“分”不够,小事,拿钱找齐,上好大学,留学去。让后代有美差,有地位。有钱垫底,早形成圈子啦,还接着往下辈传。
三越听罢说句,寒门再难出贵子。老曹晃晃磕膝盖儿又说,普通小区的人家不行,我老门口的,儿子考重点高中,差一分,让缴三万。缴不起,好,给悠兜底校去了。兜底校能去吗,男孩,抽烟、打架;女孩搭伴,穿露肚脐裤。这孩子亲叔,就住春萌小区的别墅里。
吴师傅褪下套袖问,这弟弟条件那么好,不能帮帮他哥吗,亲兄弟啊。
谁帮谁,别闹了。老曹冷笑一声。
蒋老师插话,也别光说人家富人,人们的价值观念全变了,在一家子中穷的已经不是人穷志不穷,是能沾就沾。
吴师傅回一句,都让这经济给闹的。
三越说,《老残游记》书上有句“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那可是晚清时期。
蒋老师没理会三越,蹙着眉头道,现在物质生活提高了,几位,我这是纵比,没横着比。人们享受高科技的种种便利,不假,你就说这交通,从河湾这儿吧,到济南,二十多年前,1988年我出差,坐火车还是内燃机车,车程要七个小时。现在坐高铁,一个小时十几分钟到了。世界变小了,变近了,人心却越来越远了。
三越从理发点走出来,他心里对自己这个家感到庆幸。我们兄弟间关系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