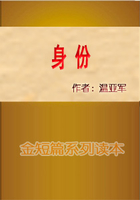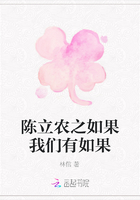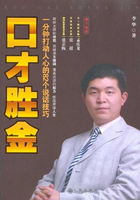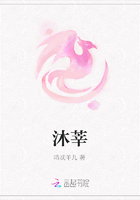来源:《时代文学·上半月》2010年第03期
栏目:时代广场
马戛尔尼子爵抱恨终生的是他在1793年那个夏天的中国之行,倒不全是因为他辜负了英乔治三世国王陛下的神圣使命,令他无法宽恕的是自己,他竟愚蠢地允许大清帝国的官员在公使船的桅杆上悬挂用中文写成的告示,那告示写的“红夷进贡”四个汉字明显带有屈辱性,伤了大英帝国的面子。没有适当的理由可以解释,那么他一定是被东方燥热的阳光烤昏了头。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夏季格外酷热,即便是天津卫的入海口一大沽口,太阳也像熨斗一样烘烤着海面,海水仿佛煮沸的汤,泛起阵阵泡沫。
一支由三艘大船组成的洋人船队停泊在海岸边,远远望去洋船很高大,潮湿的海风扑打着白色船帆。船头镶嵌一个金色的狮子头,面目狰狞地盯视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古老帝国。甲板忙碌着许多穿奇装异服的洋人。一个个黄头发、蓝眼珠,面带古怪的表情。他们从洋船上搬卸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送给乾隆皇帝过八十三岁生日的礼物,尽管两位帝国的首脑谁都没见过谁。但惺惺惜惺惺,英王的礼物十分昂贵稀罕:有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洋乐器、两驾马车和一个热气球,礼物大约将近600多件。因为洋船吃水大。进不了内陆河,只能装卸到清朝派来的平底船上运到内陆。洋船上站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儿,他伏在船舷边,瞪着好奇的眼睛,凝望着这片神秘的土地。男孩叫斯当通,是英国派遣使团副使的儿子。他好像并不在意岸上神态悠闲的瞧热闹的中国人,他关心的是刚刚捉到的一只虫儿,中国人管它叫“蛐蛐儿”。
这支英国使团船队,正是由爵士马戛尔尼率领的。执行乔治三世的一项重大使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9月,马戛尔尼率领由八百多名成员组成的庞大使团,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踏上艰难而危险的旅程。沿大西洋南行,经佛得角,穿越赤道,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经阿姆斯特丹至雅加达,又沿邦加海峡至南海,他们几乎用了将近九个多月的漫长航行,途中风暴和疾病夺去不少同行者的性命,好不容易于1793年6月21日在中国的澳门口外的老万山靠了岸。
大清国到了康(熙)乾(隆)两朝,帝国已走向登峰造极。在当时世界上它属于最富的国家之一。“抚有四海”,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丁旺盛。在那些稍微知道中国的外夷眼里,大清朝像个巨人,拥有财富、神秘而又令人畏惧。其实“巨人”富而不强,它被自负和妄自尊大迷惑了自我陶醉了,整天把自己关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充耳不闻外面的世界究竟什么样儿。甚至唯我独尊地认为,世界上的其他所谓国家,不过是愚昧笨拙、不足挂齿的番邦小国,那里的人民都是茹毛饮血的野蛮种族,根本不配跟大清国比。就是闭上眼睡大觉,他们也比不上中国。就当“巨人”关上大门睡大觉的时候,它的远街近邻开始闻着味儿,陆续集中到门口。他们垂涎三尺,又心怀忐忑和恐惧,战战兢兢地前来叩门,企图跟巨人套关系,讨点好处。马戛尔尼使团代表英国来中国,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英国使团的到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已经当上太上皇的乾隆寿诞将近,他自然高兴。又一个遥远的番邦前来朝贺,多少为他的寿日增添几分喜庆色彩。他明令地方官员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迎接远方觐见者。于是,马戛尔尼率领三艘大船一路顺风,经福建、浙江、山东沿海,到达天津,然后再由水路通州赶往北京。一路上,清朝官员大肆喧哗,船队鸣锣敲鼓,桅杆上悬挂写着“红夷进贡”的汉字告示。在陆路行进时,英国大量沉重的礼物不得不用90辆马车、40辆手推车和200多匹马、3000多人运送,进入京城后,按照乾隆的旨意,所有“贡品”被分别放到紫禁城、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陈列。
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让位他的儿子嘉庆之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退休,以“太上皇”的名义,仍控制着拥有三亿八千万人口的庞大帝国。在他眼里,中国是天朝,是世界唯一的强盛国家,其他的都是外夷番邦,都没有清朝强大,没有清朝富足。他们只有磕头进贡的份,根本无权和帝国平起平坐。虽然他并不知道大不列颠位于何处,有多大的国土面积,但他认为这些夷族仰慕天朝,无非是怕挨打而自愿臣服,所以他们的礼品无足称道。
骄傲的英国人却不这样看,小斯当通后来回忆道: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说,为了向中国皇帝陛下表达其祟高的敬意,礼品的选择不能不力求郑重。贵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任何贵重礼品在贵国看来都不足为奇,一切华而不实的奇巧物品更不应拿来充当这种隆重使命的礼物。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现的礼物。两个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礼物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珍贵。其实,这不过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一番客气话,恰好说中乾隆皇帝的心思。清王朝疆土广阔,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一个远在天边,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国能有什么稀罕东西?当他率领众臣参观英使展示他们的礼品时,乾隆表现出极大的不屑。那六门架在车上、能连发的铜炮,是准备带到承德避暑山庄鸣放礼炮用的。乾隆却对其很反感,后来命人丢在圆明园的茅房里。60多年后,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大肆劫掠时,又将它们拉了回去。至于那个热气球以及跟随来的驾驶员根本没派上用场。
不论乾隆皇帝和朝臣们,当时都忽略了英王信中的一句话:两个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礼物所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珍贵。很明显地暗示英国使团此行是有目的的。
说起来有些滑稽,英国人造访中华帝国的起因,是源于茶叶。1664年国王查尔斯二世见到了由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奇特的叶子,那就是中国的茶叶。在以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茶叶已经风靡欧洲,成为英国人普遍欢迎的饮料。到了1785年英国人几乎离不开这种温和而刺激的东西,每年从中国唯一对外的广州港口进口茶叶高达1500万磅。尽管中国也购买英国的一些产品和原料,但茶叶在英国的销量远比英国的白洋布、铁和锡在中国的销量要大得多,由于用白银购买茶叶是清政府唯一能接受的支付方式,因此,英国的白银几乎为购买茶叶而消耗殆尽,双方贸易差额逐渐增大。18世纪末叶,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日不落帝国迫不及待地开辟新市场,遥远神秘的中国成为他们垂涎已久的目标。所以,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使团千里迢迢拜访中国,中肯地讲,他们的来访的初衷并无恶意,只想打通中国的商贸关口,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或者可以说这个英国使团是企图叩开尘封千年的帝国之门的第一个造访者。
中英两方各怀一厢情愿:乾隆帝只把英国使团当作巴结他的贺寿者;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他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赠送礼物,进而建立友好互利关系。认识上的殊途和情感上的落差,让这次中西方的初次碰面从一开场便蒙上了阴影。乾隆皇帝扮演着天朝大国太上皇的角色。为了炫耀天朝的大方与“皇恩浩荡”,对于来朝贡的各藩属国一律赏赐有加,来自西方的大不列颠使团也属于此列,先后受到乾隆66次的赏赐,礼物多达130种,大约3000余件。然后。乾隆皇帝降旨恩准在承德的行宫避暑山庄觐见各国使臣。
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和隆宠?偏偏英国人不识抬举。于是在觐见仪式上出现了不愉快的插曲,按照惯例,藩属国的进贡使臣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使者自然也不能例外。但马戛尔尼等人却极不情愿,他们认为对中国皇帝跪着磕头,有伤大英帝国的体面,只答应行单腿跪的英式礼节。双方为此争执不休。一直到了觐见的那一天,关于三跪九叩还是单腿跪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1793年9月14日凌晨三点。
“太阳刚刚升起,照亮了这座广阔的花园,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早晨,由柔和的器乐和洪亮的铙钹伴奏的庄严悦耳的国歌声打破了大自然的宁静……
“皇帝坐上龙椅,立即万籁俱寂。时而有音乐声打破这寂静。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更增添了仪式的庄严肃静……”仅从使团成员回忆的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中国皇帝的宏大排场。尽管接见并不是被安排在紫禁城,而是避暑山庄的一个巨大的帐篷里,衣着华丽的百官、整齐排列的仪仗队。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足以对他们形成极大的震撼。
马戛尔尼子爵率领他的主要成员100多人隆重登场,他身穿大红的外套,佩戴肩带和钻石徽章,还有表明他属于英国特权阶层的“巴斯骑士”星标。饶有兴味的是12岁的小斯当通也随从其中。马戛尔尼对乾隆皇帝的初步印象非常之好,“他是位优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过60岁。”轮到该行礼了,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早晨,马戛尔尼究竟行了英国式的单腿跪,还是五体投地地磕了九次头?后来的中外史学家们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说词。当时一位中国官员,写诗描绘洋人跪拜的情景:“献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仪野鹿腔,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无法猜测当时这位官员在捧臭脚呢,还是马戛尔尼等人心甘情愿地拜倒?其实这并不重要,即便英使真的跪拜,也是为了不辱乔治三世交给他的使命。
乔治三世的使命就在他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函中。行礼之后,马戛尔尼向乾隆呈上了英王的那封信函。于是,可怕的结果在所难免:事后,信函被翻译成中文,乔治三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要求与中华帝国建立贸易关系和平等的外交关系。包括开放新的市场和经商口岸,自由贸易,互相在对方首都建立驻外机构……这封信大大挫伤了乾隆皇帝的自尊心,他原先以为英国人仅仅是来朝贡的。没想到他们居心叵测,一个小小的异邦藩国竟然企图同天朝平起平坐,甚至还要互派使节?简直就是自不量力,异想天开!于是,他龙颜大怒,生硬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天朝法律森严,对于那些怪异的要求“断不可行”。为使英王“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他让马戛尔尼给他们的国王捎去一封敕文。敕文不同于平等的外交信函,而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训斥文字,相当于老子训斥儿子。敕文言:“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所派人留京一事,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无益。特此说晰开示,谴令安程回国……”
乾隆的话直截了当。他说:朕的天朝德行天下,威望远播,物产丰富,什么都不缺,所以才有万国朝贡的景象。这都是你们亲眼目睹的。而且我们从不看中奇巧的玩艺儿,更不稀罕你们国家的东西。至于你们国家提出的要在京都派人驻使的种种要求,不合乎天朝的体制,对你们也没好处。朕说得已经很明白了,命你们赶紧打道回府吧!
既然皇上发了话,清政府立刻催促英国使团起程回国。特派侍郎松筠为钦差大臣,监护马戛尔尼一行由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经过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山西,最后到了广州。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七,英国使团的船队被灰溜溜地赶出国门。西方第一次的叩门,就这样碰了壁。他们带着失望和愤懑,结束了他们的处女航,离开了目空一切的古老帝国。
并非没有温情的插曲,多少带有诗意的温情就发生在祝寿的那一天:乾隆接见时,好像很喜欢使团副使的十二岁儿子小斯当通,因为那乖巧的孩子不光在中国之行中逮了不少蛐蛐儿,而且沿途学会几句汉语,尽管说得磕磕巴巴,但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他当场恩赐小斯当通一个荷包。这个黄色丝绸的荷包代表中国皇帝的无尚恩宠。
然而,就是这位小斯当通,在时隔四十年后的鸦片战争前夕,他在英国议会坚决主张对中国作战。
大清王朝的国门如此坚固,而英国人并不就此罢休,执意要推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