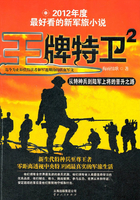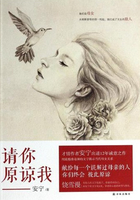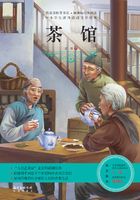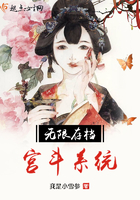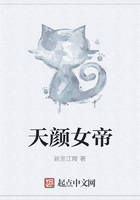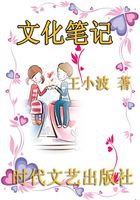来源:《山西文学》2017年第02期
栏目:非虚构
甲午初冬的一天,我去了一趟金泉北边的木塔。木塔是银杏坪区政府的所在地,我去那里是为了打听两个已故人的踪迹。其实,我跟这两个人都不认识,之所以要打听他们,还得从几年前我买的几份资料说起。
退休之后,逢双休日,断不了去金泉东庙那里的旧货市场转转。去那里不是买古玩,咱对那玩意儿不懂,也没有那份闲钱。我去那里只是在旧书摊上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书,遇上了花个十块二十块买上几本。
2009年夏一个礼拜天的上午,又去了那里。来来回回转悠了几圈,没有一点收获。正准备打道回府,听有人喊“卖玉茭来”。这一声让我停下了脚步。不是觉得肚里饿了,而是那熟悉的乡音。因为一般卖玉茭的人喊的都是两个字“玉米”,最多在前面加上个热字。而这人嘴里喊出的不光是四个字,并且叫玉米不是玉米而是玉茭。因此,我断定他不是本地人,是我的老乡。
等他走到我的跟前,我说,给饿(我)拿上一外(个)玉茭。那个卖玉茭的一听我的话,笑了,今天碰上了老乡,你也是原平(皮)的?我说,是。那天,我从他的口中得知他的老家距我的老家有三十来里地,不是一个乡,但他和我却是同一个姓:皇甫。他的名字叫晚秋,像琼瑶小说的人物。他的个子一米六上下,长相也一般,最突出的是那一口獠牙,把个嘴唇顶得噘了起来,有点难看。
那天,晚秋管我叫大哥。他说,大哥,你买下甚了?我说,这不是,就一穗玉茭,也是因为你卖。晚秋说,你来这里主要是想买甚?我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碰上喜欢的书买上一半本。噢。我夜儿见了一沓信纸写下的东西,是“四清”时候一个民办教师写的检查,两个人因为价钱没有闹成。我问晚秋,要多少钱?五十。那人只给出三十。我一把将晚秋拉在一旁说,给你五十,你悄悄过去把那东西给咱买下。晚秋点点头说,行。可不知道卖了没有。一会儿,晚秋笑嘻嘻地回来了。他从怀里取出那一卷信纸,还有十块钱。说,我跟他搞了搞价,另外,我在这里卖玉米,他们都认得我。我说,谢谢你,老弟。这十块钱就归你了。晚秋说,哥,你把我看成甚人了。我说,你是我兄弟,老哥没有别的意思。记着,以后碰到这一类的东西,你给老哥买下,要是不方便,就给老哥打个电话。说完,我掏出名片,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米良的16份检查
我把那一沓信纸装进背包里,到马路上拦了个出租。回到家中,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取出了那一沓信纸。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信纸上究竟写的是啥,有没有价值。
那些信纸保存得很好,没有一点损伤。纸是那种常用的红道道信纸,漂亮潇洒的字,流畅通达的语言,条理清楚的思维,这些文字出自一个不错的民办教师米良之手。我那天忘记了饥饿,一直把那厚厚的一沓信纸看完。检查共16份,检查最长的达13页,6000多字,16份检查总计5万多字。
这16份检查均写于“四清运动”时期。
“四清运动”的全称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这次运动,我知道一些。那时,我在原平老家的农村务农。“四清”工作队进村那年,我虚岁十五。按现在的说法,还属于未成年人。可那时候的我,已经是生产队的“干部”了。我的职务是生产队的保管。保管这官儿说大不大,上面有会计、生产队长,说小也不小,生产队的粮食、种子、蔬菜以及农业生产所用物资,一句话,队里所有的东西,只要是会计入了账的东西,都归保管管。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保管的重要性了。其实,我那时也没有感到自己有多大的权力,社员们到地里干活,需要什么农具,就找我领,用完了,我再把它们放进库里锁起来。饲养员要给牲口领饲料,手里拿着会计开的条子,我就打开库房,给他秤上。每天就是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有时候手里正端着饭碗,有人要领东西,我就得放下饭碗出去,怪麻烦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能够代表我身份的叫作印板的东西。那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长约50公分,宽约20公分,木板的一面有木匠用凿子刻了第×生产队字样,另一面钉着一个木制的把手。它的用途就是往粮食上盖。生产队的粮食入了库,保管就拿着印板在粮食堆上印几下。别小看那几个字,如果保管印在粮食堆上的那几个字没了或者变了形,就证明有人动过了它,就得报案。当然,如果是耗子在上面捣乱,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当了保管没多久,“四清”工作队就进了村。他们一进村,就开始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调查摸底,召集干部们开会、学习,然后让大家发言。对了,我开始忘了向大家交代“四清”工作队是来干什么的。所谓的“四清”,开始是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为以“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为中心的“四清”运动。“四清”工作队先后分三批入村,因为我们那个村子不大,不足七百人,工作队是最后到我们村的。我们村的工作队一共有7个人,外县的4人,本县借调的1人,部队的2人。部队的两个人年纪大的姓段,河南人;年轻的姓池,大同人。姓段的是个营级干部,也是工作队的头儿。两人都在番号为496的部队,部队的驻地就在离我们村20多里的一条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