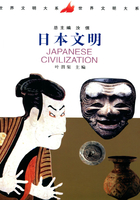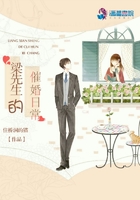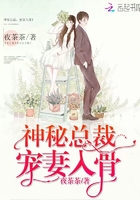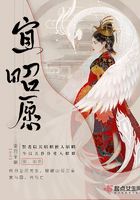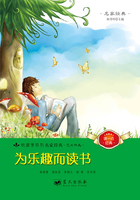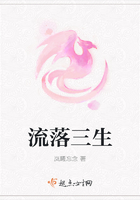一
去年偶与朋友谈起,拟有关于《老子》之作;朋友说,你写过《樗下读庄》,当然该谈《老子》了。其实我倒不以为这么顺理成章。将近二十年前阅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意思浅近,不过他把庄禅算作一路,孙老韩算作一路,倒对我启发不小。此前我尚且被通行之“老庄”说法束缚着呢。后来读到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原来他早就讲得明白:“实则《老》自《老》,庄自庄也。”然而冯氏此语亦自有据,即如其所说:“《庄子·天下篇》,凡学说之相同者,如宋牼、尹文,皆列为一派,而老聃、庄周,则列为二派。”
《天下》晚出,绝非庄子所作,实乃一部先秦思想小史,于关尹、老聃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于庄周则云:“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冯氏一番议论,最是鞭辟入里:“据此所述,《老》、庄之学之不同,已显然可见矣。此二段中,只‘澹然独与神明居’一语,可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言,有相同的意义。除此外,吾人可见《老》学犹注意于先后,雌雄,荣辱,虚实等分别,知‘坚则毁’、‘锐则挫’,而注意于求不毁不挫之术。庄学则‘外死生,无终始’。《老》学所注意之事,实庄学所认为不值注意者也。”如果细读《庄》《老》,当知二者实有本质区别。虽然《庄子》讲“道”,《老子》亦讲“道”;《庄子》说“道不当名”(《知北游》),《老子》亦说“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本一章);至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澹然独与神明居”,皆指其所体会之道,乃无限超越于普通生活表象。然而《庄子》之道,并不同于《老子》之道。
概括说来,《庄子》之道是事物自然状态,乃是本来如此,如《知北游》所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老子》之道是世界根本规律,可以加以利用,如王弼本三十九章所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庄子》讲“无为而为”或“无为而无不为”,前一“为”字作目的解,后一“为”字作行为解;《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指行为,“无不为”指结果。从根本上讲,《庄子》哲学只涉及个人,而《老子》哲学针对社会。《庄子》说“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逍遥游》),《老子》则津津乐道于“为天下”(王弼本十三章)、“取天下”(王弼本四十八章)。《庄子》说“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应帝王》),与他人无关;《老子》之“圣人之治”(王弼本三章),显然是针对“民”或“百姓”的。如果各取一语为代表,《庄子》是“吾丧我”(《齐物论》),《老子》则是“柔弱胜刚强”(王弼本三十六章)。世间“老庄”一说,人云亦云,众口铄金,其实无甚道理。我前著《樗下读庄》,已经讲明此事,这回把《老子》重新研读一过,愈加确信无疑也。
二
从前写《樗下读庄》,曾说:“如果我们把《庄子》看成一脉人即庄学、庄学的后学和后学的后学的著述,那么作为其中被寓言化的原型的老子可能在庄学形成之前,而《老子》的作者则是在庄学形成之后,即在庄学的后学与后学的后学之间。换句话说,《庄子》的大部分内容是完成于《老子》之前。”当时虽已读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却尚未见着《郭店楚墓竹简》;现在看来,这番话也许该作些修正。盖过去仅仅觉出《庄子》非一时一人之作,却未想到原来《老子》也是如此,而出土文献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郭店楚简年代,多数论家以为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三〇〇年左右)。其中有三组与帛书及其后通行各本《老子》有关,学者分别称之为《老子》甲、乙、丙,或《老子(A)》《老子(B)》《老子(C)》。当然这都是“姑妄言之”。楚简这一部分(确切地说是这几部分)真正名义如何,不得所知,根据后出文本予以命名,终究有些勉强。郭店楚简不止与《老子》有关者,这里因为话题只涉及这一方面,不如称之为“楚简甲”、“楚简乙”、“楚简丙”更其恰当。楚简甲相当于王弼本《老子》十九章、六十六章、四十六章中段和下段、三十章上段和中段、十五章、六十四章下段、三十七章、六十三章、二章、三十二章,二十五章、五章中段,十六章上段,六十四章上段、五十六章、五十七章,五十五章、四十四章、四十章、九章。楚简乙相当于王弼本《老子》五十九章、四十八章上段、二十章上段、十三章,四十一章,五十二章中段、四十五章、五十四章。楚简丙有十四枚不见于帛书以后各《老子》,学者另分出为《太一生水》,此举未必合理;其余部分相当于王弼本《老子》十七章、十八章,三十五章、三十一章中段和下段,六十四章下段。总共二千余字。单论与今本《老子》相合部分,约为后者的五分之二。其中六十四章下段,既见于楚简甲,复见于楚简丙,字句略有出入。
这样就有两种意见。一曰楚简甲、乙、丙,并不属于同一整体,而是各自独立的三种文本,但均可以视为《老子》前身,以后融合为一体,并补充新的成分,成为今本《老子》。一曰三组竹简乃是选本,或删节本,战国早期已有《老子》书在,且较郭店楚简三组的总和为多。先秦文献中与今本《老子》重复而不见于楚简者,也被后者视为这一据说早已存在的全本《老子》的内容。这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在没有更早于郭店楚简之有关《老子》文献出土前,我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
按照前一说法,《老子》之形成过程为时不短;而此一过程,基本上完成在帛书《老子》之前,即汉初时候。据此重新审视《庄子》与《老子》的关系,或许会对《庄子》与《老子》某些话语重复的问题,有一更为切实的认识。《庄子》中与今本《老子》重复的话语,情况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前冠有“老子曰”、“老聃曰”、“故曰”、“故”和“夫”者,指为引文尚且说的过去;若是行文中有一两句相近,乃至连文字都不一致者,譬如《庄子·应帝王》之“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与《老子》王弼本七十七章之“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也说成有所沿袭,则未免牵强附会。盖发此论者,头脑中尚有《老子》五千言早出的印象在也。
《庄子》文本驳杂,自相矛盾,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且早出与晚出,亦非过去区分以内篇与外杂篇那么简单。内篇中有庄学后学之后学作品羼入,外、杂篇中有属于庄学或庄子后学的篇章,而这些篇章中又夹杂着晚出段落。所以泛言《庄子》,最容易生出偏差,须得看在《庄子》哪一篇,又在哪一段也。譬如外篇《知北游》,立论甚为精辟,与内篇《逍遥游》《齐物论》相当,然则“知北游于玄水之上”一节中之“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道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无为也’”一段,早经论家指出其为后人羼改。恰恰其中颇有与《老子》重复之处,然而只不过涉及这很可能是羼改的一小段话而已,既不能代表《知北游》其余部分,亦不能代表《庄子》全书。也就是说,不宜将《庄子》视为一个整体,当作推论的依据。
《庄子》与《老子》重复话语,有见于楚简者,如《庚桑楚》之“老子曰:‘……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在楚简甲;《胠箧》之“故曰‘大巧若拙’”,《在宥》之“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寓言》之“老子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让王》之“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在楚简乙。有仅仅见于今本《老子》者,如《胠箧》之“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帛书相当于王弼本三十六章处;《达生》之“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相当于王弼本十章及五十一章处。上述二者实有区别。即以前述《知北游》之一段话为例。“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近乎《老子》帛书之“[知者]弗言,言者弗知”(王弼本五十六章)和“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王弼本二章);“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无为也’”与帛书相当于王弼本四十八章部分基本一致,而这些又分别见于楚简甲、乙中。又“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道也’”,与帛书相当于王弼本四十八章部分大体相合,却为楚简所无。前二句有可能是引自作为《老子》前身的楚简;至于后一句,或许别有所本,未必一定是从《老子》中来也。
《庄子》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其可能沿用《老子》者已如上所述;《老子》之形成亦自有过程,其间未必不曾取材于其他文本,甚至包括《庄子》某些段落在内。那些今本《老子》所有而楚简所无的部分,尤其可能如此。譬如,《庄子·大宗师》之“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与《老子》帛书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王弼本二十五章);《庄子·胠箧》之“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犠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与《老子》帛书之“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车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王弼本八十章);《庄子·天地》之“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与《老子》帛书之“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此取彼”(王弼本十二章),实在很难断言究竟《老子》在先,抑或《庄子》相应段落在先。
三
《庄子》一书中,有关老子或老聃的段落很多,计《养生主》有“老聃死”,《德充符》有“鲁有兀者叔山无趾”,《应帝王》有“阳子居见老聃”,《在宥》有“崔瞿问于老聃曰”,《天地》有“夫子问于老聃曰”,《天道》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天运》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孔子见老聘而语仁义”,“孔子见老聃归”,“孔子谓老聃曰”,《田子方》有“孔子见老聃”,《知北游》有“孔子问于老聃曰”,《庚桑楚》有“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则阳》有“柏矩学于老聃”,《寓言》有“阳子居南之沛”,《天下》有“以本为精”;此外《外物》尚有“老莱子之弟子出薪”。今本《老子》某些与《庄子》重复话语,就见于这些段落之中。《庄子》中之老子,本是一寓言人物,与那里的孔子、庄子本人,乃至许多稀奇古怪名字相当,我亦不把这些老子言论一概当真。不过可以由此得一启示,即当时(指一段时间之内)记载老子言论的文献或许不止三组楚简;例如《庄子》上述段落,亦未始不可视为有关老子的原始文本,假如它们出现在今本《老子》之前的话。如果把《庄子》与今本《老子》重复之处,全都指为取自《老子》;那么对此外这些为《老子》所不载的老子言论,又该是如何说法呢。
《庄子》上述章节中的老子,乃是一个复杂形象,有时是庄子及其后学的化身,所说与今本《老子》不无抵触之处,譬如《天运》之“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便与《老子》帛书之“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拱之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而进此”(王弼本六十二章)不合。不过此一老子,更多时候还是后学之后学面目,抨击仁义尤为著力。如《在宥》云:“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肱,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天道》云:“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天运》云:“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这样的话,不见于三组楚简,却与今本《老子》某些章节意思相符,譬如十九章之“绝仁弃义”,三十八章之“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皆是也。
论家指出,楚简与今本《老子》思想上的重要差别,是并不直接反对儒家的仁义学说。我联想到《庄子》中那个激烈攻击仁义的老子,颇有些怀疑在由楚简到今本亦即《老子》形成过程中,《庄子》某些章节(或者其所代表的思想)对于《老子》这一观念变化,可能起过一定作用。这里有个例子。《庄子·胠箧》说:“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在宥》也说:“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后一段乃是引述老聃的话。而相当于王弼本《老子》十九章处,楚简乙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帛书却作“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意思颇为不同。其本诸《庄子》之语而修改乎。
我这么讲话,倒不是一口咬定今本《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如前所述,《庄子》并非一时一人之作,上述章节,多系庄子后学之后学所作,未必早出;甫面世时,也未必就在《庄子》之列。其较早出者,或另有所本;较晚出者,或袭自今本《老子》较之楚简增出部分也未可知。《老子》增出部分或别有取材,其中不排除某些后来归属于《庄子》的章节。《老》《庄》关系,可能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绝非简单的《庄》本《老》,或《老》本《庄》,多半还是在各自形成的过程中,互相有所影响。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抨击仁义的言论,于《庄子》是晚出,于《老子》亦为晚出,—以楚简比帛书《老子》可知,以“绝智弃辩”比“绝圣弃智”可知,而凡此种种,皆不支持有一全本《老子》早出之说也。
四
《韩非子》中有《解老》《喻老》二篇。《解老》引文涉及王弼本《老子》之三十八章、五十八章、五十九章、六十章、四十六章、十四章、一章、五十章、六十七章、五十三章和五十四章。《喻老》引文涉及王弼本《老子》之四十六章、五十四章、二十六章、三十六章、六十三章、六十四章、五十二章、七十一章、四十七章、四十一章、三十三章和二十七章。其中四十六章、六十四章和六十三章见于楚简甲,五十九章、四十一章、五十二章和五十四章见于楚简乙,六十四章又见于楚简丙,其余各章则为楚简所无。二篇所引《老子》之顺序,与楚简及帛书《老子》均不相同。
《解老》《喻老》皆为摘句诠释,二篇之作者所见原本,或许比所谈及的为多;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其所见只有这些,乃是不同于今本的另一《老子》前身。又王力指出:“《解老》多精到语,《喻老》则粗浅而失玄旨,疑出二人手笔。”果然如此,则《解老》所“解”,与《喻老》所“喻”,依据又未必是同一种《老子》。
我们且将《解老》《喻老》所引《老子》,与楚简及帛书《老子》作一比较。其中涉及相当于王弼本五十九章、四十一章和五十四章者,二篇之引文与楚简、帛书除个别字句外,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相当于王弼本六十四章部分,在楚简甲中分为互不相干的两段,故上文称作六十四章下段和六十四章上段,六十四章下段又见于楚简丙中。帛书甲、乙本,均合为一段。《喻老》有两段文字,含有该章引文,一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一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和“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间却隔着《老子》另外两章,显然所据原本不是一章。而这两段话,在楚简中正好分别属于不同段落。这说明《喻老》作者所见《老子》这一部分,大概与今本并不相同,而是类似楚简那个样子。
其它几章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于王弼本四十六章部分,帛书较之楚简甲,多出开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四句,而此四句,已见于《解老》《喻老》,又“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三句顺序,帛书同于《解老》《喻老》,而楚简甲中,“咎莫憯乎欲得”在“祸莫大乎不知足”之前。相当于王弼本六十三章部分,帛书较之楚简甲,多出中间“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数语,而“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均见《喻老》。《喻老》又有“圣人蚤从事焉”,为帛书所未见。相当于王弼本五十二章部分,帛书较之楚简乙,多出开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和末尾“[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是谓袭常”数语,其中“见小曰明,守柔曰强”,见于《喻老》。这说明《解老》、《喻老》或其所依据的文本,可能也是今本《老子》的来源之一;在今本形成过程中,对楚简或许起过某种补充作用。
《解老》《喻老》所据《老子》文本,时而与楚简相合,时而又不合,与今本六十四章下段重出于楚简甲和楚简丙中,似乎不无类似之处。可以想见在《老子》最终形成之前,不同时期出现的各种原始文本既各自独立,又从早出者有所取材的情况。而这仿佛也反映了某种演化进程。前述《庄子》与楚简和今本《老子》话语重复,亦未必不可作如此解释。今本《老子》很可能是综合三组楚简和其他原始文本而成。帛书《老子》实际上也显露出这一迹象:在相当于王弼本五十一章与十章,五十二章与五十六章,五十五章与三十章,五十六章与四章,六十四章与二十九章,七十七章与二章,二十四章与三十一章各部分之间,均有同文复出现象,而考察文意,又未必一定需要如此,很像是由不同来源撮合而成的。
楚简丙中有十四枚竹简,内容为今本《老子》所无,学者遂名之为《太一生水》,算是另外一篇文章。其实如果以三组楚简为《老子》前身,则其较之今本多出若干亦无不可。或许此“太一生水”云云,正与前述《喻老》之“圣人蚤从事焉”一语性质相当,亦为今本《老子》形成过程中所舍弃不用的罢。
除《解老》《喻老》外,《韩非子·六微》《六反》《难三》,《吕氏春秋·贵公》《制乐》《大乐》《乐成》《君守》《别类》,《战国策·齐策四》《魏策一》等,均有与今本《老子》重复内容,或冠以“故曰”,或径自行文,个别亦见于楚简之中。这些段落大概与前述《庄子》与《老子》重复者类似,未必不是今本《老子》的某种来源。
五
如前所述,郭店楚简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在于《老子》形成经历了为时不短的过程。这样就又涉及到《老子》的作者问题。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述凡三老子,其一李耳,字聃,早于孔子;其一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其一太史儋,在孔子百余年后。关于相当于后世《老子》一书之写作,则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且不理会这一写作经过有否实现之可能,单从“上下篇”及“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看来,其所见者显系今本(甚至是帛书之后的本子);如果认定《老子》并非一时完成,那么这段话便不是事实。至于三组楚简,其年代较之本传所载老子即李耳要晚得多,恐怕不宜与其直接建立联系。当然楚简未必就是最初文本,或许还有来源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同时老子又确有其人的话,要说其间有何关系倒也不无可能,但是目前说这些都还只是揣测而已。至于把楚简或继乎其后的今本《老子》作者归之于太史儋,其实也是牵强附会的。
论家指出,《老子韩非列传》所述老子之事,如“周守藏室之史也”,袭自《庄子·天道》之“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而“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则本诸《庄子·外物》之“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与《天运》之“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然而《庄子》“寓言十九”,所述老子事大多不能当真,《史记》因之成说,也就不能不打些折扣了。
在我看来,老子或许当初曾有此一人,孔子可能曾问礼于他,也可能没有这事;以后逐渐成为传说人物,他人立论,往往依托老子名字;而年代不同,内容也有差异,起先不反仁义,后又反对仁义,即其一例。《庄子》记载老子言论如此,《韩非子·解老》《喻老》所依据者如此,今本《老子》也是如此。作为《老子》前身的三组楚简未著作者姓名,然而从《庄子》及其他著作引述情况看,至少后来也归在老子名下了。
六
我开始读《老子》,尚在读《庄子》之前。二十年前家母曾以苏体为我抄写过一遍,至今仍置诸案头。十五年前,我起念要把先秦诸子研习一遍,未读的读过,读过的重读,遂由打《庄子》起头,写了一本笔记,题曰《玩庄闲笔》,即为后来所著《樗下读庄》之雏形。接着便是《老子》,写了三五页即告中止,—当时乃对其中意思觉得不大舒服,尤其是名为“道”,实为“术”的那一套,实在太过刻毒。虽然《老子》文章我是佩服的,五六年前还特地写了一篇《无情文章》加以讨论,后来收在《如面谈》里。我写《插花地册子》,把对我最有影响的散文归为“正”、“变”两路,“变”打头是《韩非子》,而《韩非子》显然得力于《老子》。《老子》不成就于一时,各章文笔亦有参差,最好的时候,真是干净利落,不留余地,但绝非写到满满当当,就像时下美文似的。相反《老子》很少形容,往往能够刻画得恰到好处。这里形容以“刻画”一词,最是合适不过,《老子》文章确有一种金石之美。说来《老子》书中绝少商量口吻,简直是说一不二,在他看来这世界没有或然,只有必然,他也拿这副态度对待他的文字。这恐怕一靠气魄,二靠功力,光是想着如何还是不成罢。
由于佩服文章的缘故,这些年来常常翻看《老子》,但是始终没有想过要专门写一本书。原因如前所述,一是有意回避它的意思,二是不知道该作何等评价。《老子》是中国文化重要原典,喜欢也好,反对也好,都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其中意思明明白白,又歪曲不得;而且自成一个整体,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至少我是做不来的。现在偶有机缘,写成这本小书,也还是没怎么评价,当然这么一来,我之中意与否也就无所谓了。况且我想,《老子》这路意思,如果真实行起来,的确有些可怕,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做得来的,我怀疑大家多半没有他所要求的那份耐性。譬如:“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王弼本三十六章)对于一点亏都不吃的人,这种办法肯定没法采用。所以《老子》哲学到底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上起过多大作用,实在也很难说。
也许更重要的影响是在另一方面。当《老子》讲“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王弼本二十五章)和“反者道之动”(王弼本四十章)时,其中隐含一个时间概念,即“我”必须有足够的剩余生命,等待这一终将有利于自己的过程自行完成,否则“弱者道之用”(同上)就落空了。《老子》之所以很重视“身”,原因大概就是这里。所以这一哲学的根本,在于“活着”,乃是一种现世哲学。这与孔孟之儒家,韩非之法家,甚至庄子之道家,正是一致的。我想在这一方面,它们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虽然在别处他们又何等不同:孔孟相信有社会终极价值存在,《老》韩根本不承认,庄子则以为终极价值在于自己。
我写这本书,其意不在评价,甚至不想引申发挥,那么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闲翻《老子》,每逢不解,辄尔略过,这回于此等处,皆花费不小心思,说句老实话,也不过是弄明白了而已。我所写的就是这一经历。对我来说,这样的收获胜于一切议论,一切评价。没搞清楚就在那里瞎说,为我素不喜欢。我自己只是普通读者,如果将心比心,那么一个读者所真正需要的恐怕也无过于此了罢。
此番读了郭店楚简,帛书《老子》甲、乙本,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以及历代的几十种《老子》注本。虽然帛书早出,楚简更早,但是要说最好的本子,恐怕还得数王弼本,因此拿它当作底本,参校以其他各本,包括帛书在内。两种帛书均不分章,其先后次序有不同于王弼本处,却要比王弼本合理,也就据此予以调整。但是帛书先“德经”,后“道经”,却没有照样采用。马叙伦《老子校诂》、奚侗《老子集解》、高亨《老子正诂》等,对《老子》字句做过不少订正工作,虽然不一定为后出土的帛书所支持,但是帛书乃至更早的楚简未必就没有错讹之处,故我仍然择善而从。还未动笔之前,就拟定题为《老子演义》。《现代汉语词典》将“演义”释为“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我虽然不曾引申,敷陈却是难免,所以还是这个出典。
末了找补一句,我在这里一再讲《老子》如何,《老子》思想如何,原本是针对帛书以后即已经基本完成了的《老子》说的,然而又强调《老子》形成经历一个过程,其间似有自相矛盾之处。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不过我读《庄子·天下》,发现那里讲到老聃,也是以今本《老子》为依据的,若拿楚简求之则多半没有着落,那么就姑且搪塞说早有先例罢。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