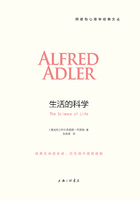“望舒,醒醒。”
“好冷,我这是在哪里?是不是死了?”
“别怕,你还活着,你会一直好好地活着。”
“你是谁?”
……
望舒的意识最后定格在一片巨大的爆炸声中,火光四溅,人声鼎沸,她被强劲的水波撞翻,从后面摔进湖中,顷刻间便沉入湖底。
在梦中一直有人低声唤她的名字,声音附在耳畔,热气钻进耳廓,连着神经通入大脑,一阵阵刺痒和心动。她觉得声音很耳熟,却始终睁不开眼睛。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她的身体被一股股热流包围,逐渐变得温暖。越是这般,她越渴望温暖的源头,一直在梦中追索、靠近、小心碰触,终于得偿所愿,落入温暖的胸膛。
温暖的胸膛?
望舒猛地一惊,意识慢慢回归。眼刚睁开一条缝,就被透亮刺目的白光闪到,她又立即闭上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霎时间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他们应该是在一辆透明的水晶“马车”里,可以看到四周的深蓝色水波和各种各样的海底生物,背壳朝下的大海龟、成群的虾兵蟹将、五颜六色的鱼和海草……拉着“马车”在海中飞快穿行的却不是马,而是八名雄性鲛人。他们一人执一根铁索,一头背在肩上,一头缠在水晶车厢上。上身是半裸人形,下身是鱼尾,在海中游弋的速度相当惊人。
她就在四面隔水的水晶车厢里,仿若刘姥姥进大观园,惊讶地看了会儿海底世界,直到背后的温度逐渐升高,她才意识到车厢里还有一个人。
重点是,她还靠在那个人怀中。
梦中熟悉的声音与现实的人影渐渐重叠,望舒慢半拍回头,见爵微紧闭双眼背靠在水晶壁上,脸色略微苍白,额头渗出了一颗颗汗珠,看起来似乎很难受的样子,她不禁心下一紧,急忙问道:“你怎么了?”
听见声响,爵微缓慢睁开眼:“我没事,旧疾复发,休息一会儿就好。”
“什么旧疾?”
她将他扶起来一些,手搭在肩后虚搂着他。见他不回应,她自顾自说道:“你哪里有什么旧疾?近年来也只伤过一次,华井生怕我忘恩负义,将你的病情都告诉我了。神魂假离之法后你没有好好休养,落下了寒疾,碰不得水。”
“你这话让他听到了肯定又要倒苦水,他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糟蹋身体,才说些病人的事警醒你。他做任何事情都为你打算,心里是向着你的。”
“我知道,但是他嘴巴坏。”
她是下意识的反应,不自觉流露出小女孩的模样,爵微莞尔一笑:“你待他也更亲近些。”说完将她的手从肩后抽走,向她摇摇头,“不必如此,我没那么虚弱,只是刚刚在湖底找你费了些功夫,没什么大碍。”
“既然这样,为什么又来救我?你明知自己碰不得水,为什么还……”
话说到一半,被不知名的复杂情绪裹挟,想到前夜才受过他的恩惠,望舒顿时变成哑巴。
“怎么不说下去了?我以为你又要同我说不再见面的话。”爵微叹了声气,“望舒,你要报仇,我要寻找死灵城的下落,可是蓬莱只有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也能见到,更何况三方战局又与你我有撇不清的关系,那些友人还都牵扯其中,就算我想刻意避开,也会有难以预料避无可避的意外发生……其实你我之间不必那样。”
他话没说尽,但望舒已然晓得他的意思。那些恩与债他都不在意,她也无须在意,还当初识他那般相处就好,这样彼此也能相安无事。但这是他的想法,她并不认同,以前她就不肯稀里糊涂地和他相处,往后也绝对不会这样。
沉默片刻,她干脆将话题转移:“你怎么会在雪园?我还以为……”琴声散去之后,他也跟着离去了。
“梭罗子担心王邢笑借桃花大会招兵买马是个幌子,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那你可看出什么?”
爵微看她,细细地看:“你这么问我,又是看出什么?”
她是聪明绝顶的人,而他是能看懂她的人,眼睛一对,就知道彼此都发现了桃花大会的问题所在。若只是想要鲛人族的十五万兵马,王邢笑本可私下将画皮仙子送给杨巍,但她偏要利用画皮仙子做大会噱头,公然交易,便是心怀鬼胎。
鲛人族刚经历过内部清洗和新族长上任,正是军心不稳的好时机,杨巍性子耿直,一击则怒,王邢笑便利用他对画皮仙子的感情,为他精心布置一场杀局,将他困于雪园让他们互相残杀,以换取兵力,出其不意地抢占西海。
这场大会从根本上来说,重夺冰城是假,图谋西海才是真,王邢笑从一开始接近杨巍的目的就不纯粹,但她没有想到王琅摆了她一道,泪嬛珠会在画皮仙子手上。
棋差一着,险些玉石俱焚。想到这儿,她不免想起同在长堤的秦昭雪等人,不知他们有没有逃出去。
爵微看出她的困惑,说道:“我赶到时雪园已在火海之中,不过你不必担心,他们不比你,个个都是修为上乘的仙尊,要保住性命应该不难。”
“那杨巍呢?他当时已近痴傻,还能……”
说话间,又一辆透明的水晶“马车”从她身边疾驰而过,她看到里面趴在水晶壁上冲她挤眉弄眼的杨巍,到嘴边的疑问又咽了下去。
杨巍怕真是傻了,但这些鲛人又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在湖底找到你时他们已经在了,二话不说就将你我押进水晶车中。我寒疾复发修为大减,也担心湖面之上火势太大不能护你周全,索性没有反抗。后来我看他们从雪湖之下一直西游,穿过数十条水沟山涧汇入大海。如我所料不错,我们应该已在西海海底,应该也快到鲛人族的领地了。”
他说得漫不经心,望舒却听得暗暗心惊。
横穿数十条水沟山涧,听起来不过尔尔,但要确保河流最终能汇入雪湖就难了,在水下探路的人必然是游过千山万水,试验过无数次,才能将数十条水沟山涧排列组合,最终验出一条正确的路。
这绝对不是一件易事,也绝对不是杨巍能想出来的事。后来在鲛人族掌事的验证下,望舒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王琅死前安排好的。从杨巍频频出海与九重天上的人来往之时,他就已经猜到鲛人族将有大难,于是将真正的泪嬛珠偷龙转凤,还早早安排了人“挖地道”。
掌事说王琅有帝王之相,望舒相信他所言,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因为就在他们刚刚到达鲛人族的大本营时,王邢笑事先埋伏好的兵马也到了。
纯洁的深蓝色水晶宫都变成了刺眼的红。
望舒不知道王琅有没有算到这一天,但她在席间猜到王邢笑的真实目的时,就已经料到这一刻。只是她没想到这一刻会来得这么早,而且就在她的眼前上演。
她细细思索,将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按照吴歌所说,西海大战发生时,鲛人族族长也就是王琅并没有将他赶尽杀绝,而是将他交给了一个白头翁。白头翁制造了他的假死,骗过所有人,之后将他带去瓠犀酒楼,藏在与蓬莱咫尺天涯的无间狱中。
这个白头翁应该就是在天机阁上救他们一命的老头,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和用仙魂与王琅做交易的白头翁会是同一个人吗?否则,王琅怎会将吴歌交给他处置?
望舒想不明白,但她隐约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握在白头翁手中的一张网很大很大,几乎网住了整个蓬莱。从西海大战的很多年前开始,他就在织网了,不只是吴歌,连王琅也是他网中的一个结点,或许……或许还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
她忽地抬头,目不转睛地看向爵微,心思越发复杂难解,连带着眼神也变了味,平白惊出一身冷汗,脸色苍白如纸。爵微以为她是哪里不舒服,连忙上下打量她:“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她一动不动,任由他将她翻来覆去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伤口后不得不询问她:“望舒,说话。”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吴歌……”她一张嘴声音都哑了,喉头好像被利物堵着似的,一阵阵疼。她想告诉他曾在无间狱看到吴歌的真相,但随即一想到少年临死前的重托,就咬着牙忍下来了,只是情绪涌到心口,让她无端变得哽咽,“秦昭雪告诉我的,你的弟弟吴歌……”
爵微不出声,神色说不上有多自然,但很显然在听见这个名字的时候变得落寞了。他往后一靠,双臂下垂,问道:“你想说什么?”
“当年是王琅害死吴歌的,事后你怎么……怎么没有为他报仇?”
他笑了一声:“我要想杀王琅,只是手到擒来的事。”
其实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若非画皮仙子在席间旧事重提,他已经忘记“王琅”这个人。当年西海大战,他虽人在北荒平乱,但心思都在西海,每日战况都会传递到他手边。普天之下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王琅为人,鲛人族能取胜全靠他的深谋大略。
大面积散毒制造混乱,以值钱的鲛人泪珠私下收买仙界守将,以此作为要挟,逼守将打开牢门,还知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声东击西分散各部兵力。鲛人族上下齐心,势如破竹,只用三日就将整个西海瓦解。
就算当时他在场,也未必能保得住西海,保得住吴歌。
“吴歌死后,我不是没有找过王琅,他是个有心之人。当时我不杀他,是不想再添血债,再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我想吴歌也不愿意我这样,后来我便洗了手,再不过问九重天的事。”
“你后悔吗?”
他又笑一声,这声笑将他眼角的细纹勾勒出来,都是被沧桑岁月间的物是人非磨的,磨得痕迹深了,即便是笑,也显得十分寂寞凄冷。他不说话,望舒便知他内心也是极其复杂的,不杀王琅,便对吴歌有愧,倘若杀他,便对苍生有愧。
直到这一刻,望舒才记起当年王琅同她说的第三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
“我曾去西海小住过一段时间,当时阿爹就是将我托付给王琅照顾。他对我说这辈子只做过一笔交易,但是他最终后悔了。”
“后悔什么?”
“倘若没有西海之战,也许鲛人族至今仍被困于仙界海底,终年不见天日,但是他们不用上阵杀敌,不必历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年鲛人族血屠仙界,如今历史重演,仙界血屠鲛人族,也许王琅早算到结局,所以他后悔了。他曾答应永不掺和九重天的事,永不走出西海,但他最终还是食言了。”
这一天也终究来到。
马车外的鲛人一个接一个坠落深海,鲜血染红了水晶壁,在上面绘画涂鸦。爵微陷入一段时间的沉默,他没有看残忍的杀戮,但他一直紧锁眉头。
须臾,他扬眉看她:“王琅不会后悔。”
“为什么?”
“因为鲛人族不会输。”
拉车的鲛人被杀死了,铁索直穿胸口,将他们与这辆“马车”永远地捆绑在一起。他们不停地下落,下落,仿佛要落到海的尽头……血融入大海,像炸开的烟花一样绚烂、耀眼。
望舒还未反应过来,高大的身躯已经压下,从后面将她揽在怀里,低沉的声音说道:“抱紧我。”
这一刻她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找回了丢失的灵魂一般,心缓缓落到实处,全身又积聚起力量。
霎时间,水晶“马车”炸裂了,无数碎片伴随着海水朝他们涌来。她被爵微紧紧护在胸口,没有感受到一丝海水的凉意,但她还是本能地拂开一片血光,看向一处,朝着那唯一一处光亮破水而去……
王邢笑手中能上战场的兵马不多,她原先打算等杨巍交付了约定的十五万兵马之后再行抢夺西海之事,却因一场大火愤然出动,兵行一夜赶至西海,布置仓促,准备不够万全,被爵微翻出海面毁了几艘主战船后,便立刻偃旗息鼓。
再加上王琅事先已做多手准备,在海上遍撒矛珠,珠子都浮在海面上,矛尖往上,只要船只一靠近就立刻会被扎得千疮百孔。船只翻沉,贼人落水,又不如鲛人熟悉水性,三个一围,两个一困,鲛人族便以数量庞大取胜,王邢笑不得不先撤兵休整,再做打算。
鲛人族大获全胜,夤夜高歌不息,杨巍被人簇拥在上座,抱着青梅酒笑得像个大傻子。
听闻此酒是画皮仙子生前最爱,也是王琅亲手酿制的。鲛人天生酒量差,青梅酒度数低,喝上两小盅也不会醉。想到这些往事还历历在目,往事中的人却已经走了,唯一活下来的还傻了,族中老掌事突感悲从中来,抹着眼泪呜咽出声。
望舒与爵微因为出手相救对鲛人族有功,也被奉为上宾,就坐在老掌事下方,见状不得不上前安慰。老掌事便抓着他们说了一夜关于王琅、杨巍和画皮仙子三个人之间的故事,说得最多的还是王琅。
明知杨巍对他有异心,还是将他留在身边,不管亲信如何劝谏,还是信任杨巍;为人重情重义,待鲛人子民有如亲生,事必躬亲,所以很得民心;并非鲛人族忘恩负义,不给王琅发丧,而是他事先就安排好的,不希望因为此事闹得民心不安;不仅如此,他还嘱咐老掌事在他死后要像辅佐他一样辅佐杨巍,不得有二心,更是将亲信早早安插进杨巍一部,以让他们上下齐心,生死相依,务必将杨巍视作真正的族长。
如此可见,王琅心胸之宽、仁德之广,这样的帝王之才生前却只困于西海,从未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实在是可惜。
老掌事一连三叹,泪雨涟涟,望舒不禁想到阿爹和黔公,一时心软,安慰道:“他虽没走出过西海,但我想他的心已经去到很远的地方了。”
老掌事一愣,顿时忘了悲伤,在灯火中细细打量她。
面前这个女娃子长相稚嫩,看起来也就三千岁的样子,可眉眼间却深藏一股雄厚之气,深沉似海,与她年龄实不相符。
先前敌人进犯、战火纷飞时,他曾在杀红眼之际举目四望。碧海潮浪间匆匆一瞥,只瞧见了这个女娃子。当时她站在大礁石旁,风吹得她头发散乱,厚重青衣紧裹上身,将她瘦小的身影勾勒得越发弱不禁风,然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海浪拍着礁石卷起惊天骇浪、一道血柱横眉泼下时,哪怕被风浪打得连连后退,她的眼睛也没有眨一下,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任由满脸满身被泼上鲜血,自始至终没有眨一下眼。
是时老头子心中便热流滚滚,眼底浮现泪光,仿佛看到少年王琅昨日重现。想当年西海大战时,王琅也是如她这般屹立在礁石旁,满身风雨,兜头血光,岿然不动。
那股深藏在二人眉间的坚定与孤勇简直如出一辙,老掌事的心思就在打量中历经百转千折,忽地伏身朝她跪下,痛哭道:“王琅已去,鲛人族群龙无首,难成气候。西海陷入血战,万年安乐难再守,老头子有愧先祖,深负王琅厚望,今看小女有大将之风,遂斗胆做一回主,拜请小女接掌鲛人族。从今往后是生是死,是荣是衰,鲛人族上下必将全意跟随,矢志不渝。”
他一席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直将望舒说愣了:“老掌事你……你莫不是醉了?”
不仅是她,连在场诸位鲛人首领也都愣了,七嘴八舌地询问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将鲛人族的生死大权交给一个……一个才认识不过一晚的女娃子?莫不是疯了?
老掌事思来想去,只给出一句话:“是王琅托梦给我,让我做这个决定的。”
望舒一听,便晓得他是在说瞎话,糊弄这些将王琅奉为天神的鲛人也就算了,她又怎会相信?为鲛人族挑选族长不是小事,堂堂一族大掌事怎会如此草率?她连忙推拒,再三表示无法胜任。
正当众人相持不下时,一直抱着青梅酒傻笑的杨巍忽然爬上桌子,甩出长枪往桌上一磕,场面顿时陷入死寂,只见他缓缓敛了笑意,双手拂面,逐渐将鬓发理顺……他的目光在这须臾间几度变幻,最终温和地定在众人身上。
“我是王琅。”
他一开口,鲛人们全数伏地叩拜,叩拜之后便是一声声哭泣。杨巍与王琅同为一族,是有血缘的兄弟,五官也有相似之处,眼下他看着众人,就仿佛真的王琅回来了。
这一刻,王琅的笑容终于到达了眼底。
望舒从没见他这样笑过,安心适意,充满温暖。他说:“我要走了,这一生我得到过很多,也失去过很多,但是最终我一无所有,落得满身轻松,可我却觉得很快乐,所以你们不必伤怀,便是去了阎王那里,我也希望你们如我一般快乐。”
这句话是对鲛人族说的。
“吴歌曾和我说过你许多事,他说你是真正的神佛慈悲之人,我本不信,但在这万年间我终是信了。我后悔的从不是当年受人撺掇,起义反叛,而是没能交下你这个朋友。”
这句话是对爵微说的。
最后一句话是对望舒说的。
“你不好奇当年为什么长元会将你送来西海托付给我吗?只要你接掌鲛人族,我就会给你答案,届时你心中的谜团都会解开。”
“可是我……”
她一句话没说完,眼前的王琅面目渐渐模糊,很快就又变成疯疯癫癫的杨巍。她猛一回神,好像做了场梦似的,待老掌事解释后,她才知道刚刚那一幕是王琅用鲛人族秘术在遥远国度为他们编织的幻影,令他们产生错觉,看着五官相似的杨巍便以为看见了他。
交代完遗言,王琅终无牵无挂地离去,从今往后天地间将再无他踪迹。鲛人们亲见王琅寂灭,纷纷抱头痛哭。望舒却因他突然而来的托付,陷入漫长的思索之中。
她到底该怎么办?
望舒想起雪园长堤之上那一声巨大的轰鸣,想到顷刻间化成一团烈火的画皮仙子,想到疯疯癫癫地说着“我没你想的那样伟大”的杨巍,想到方才定定注视着她微笑的王琅。
闭上眼睛,她仿佛找到冥冥之中一直牵引她的那股无名的力量,仿佛从绵长遥远的风声尽头,又一次听见了王琅的声音,他在呼唤她,请求她,以对生命前所未有的热烈邀请她——救一救鲛人族吧。
她一个颤身,朝前走去。
忽地她又想起黔公,想到衣不蔽体被人吊在房梁上的老人家,想到被情蛊折磨三千年的阿爹,理智一瞬间回来,神色又变得淡冷。
她答应了老掌事,接掌鲛人族,对抗王邢笑。
次日深夜王邢笑率军卷土重来,鲛人族再次遍撒矛珠,王邢笑早有对敌之策,弃大轮改用小船,在船底涂蜡,矛珠一碰即粘在船底,反倒增加浮力,令船速行进更快。他们夜袭鲛人族,悄无声息地围逼主帅营帐,掳了杨巍威胁鲛人族。
杨巍背叛王琅,王琅旧部早就心存杀意,不愿相救,但老掌事和杨巍新部都曾受命于王琅,誓死要保护杨巍,更要维护鲛人族尊严。两方意见相悖,一时争执不下,到最后不得不由望舒来做决定。
王邢笑只给他们半日思考,若是明天晌午还看不到投降的十五万俘虏,便会杀了杨巍,让他的血流遍西海。
大家都看着望舒,等着她定夺。
这是前一夜王琅为他们选出的新族长,一个完全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小女娃,忽然就掌控了数十万鲛人的命运。
望舒站在十米高的石峰上,俯视海下群鱼,周身被冷风海浪包围。她想了很久,最后说道:“杨巍背叛王琅在先,间接害死画皮仙子在后,他是鲛人族的罪人,罪该万死。”
鲛人们稀稀拉拉地哭起来。
人群中有一抹灼热的视线一直定在她身上,望舒想忽略却忽略不了,声音一顿,下半截话好像被鱼刺卡住一般,怎么也吐不出来。她狼狈地跳下来,头也不回地往外逃:“再让我想一想。”
可是没逃多远,就被他追上了。
爵微从后头三步并作两步跨过来,一把揪住她,不管她如何挣扎,都将她死死圈在胸膛中。他的眼眸从未这样深邃过,在波澜壮阔的大海和星空中,被衬托得一望无际。
“你为什么要跑?”
望舒转过头不看他,小声推拒:“你先放开我。”
“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跑,我就放开你。”
“我没有跑。”
“……望舒,你的心思这样明显,以为能瞒得住我?”爵微无可奈何,叹了口气,手指微微一松,她又要跑。
他一时不察让她挣脱,心下更气,直接喊道:“以你之心,舍杨巍无关紧要,哪怕舍弃整个鲛人族都无关紧要,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只是把他们当作你报仇的工具,对吗?”
望舒脚步一顿,浑身僵硬。
“王琅选择你,才是他平生最后悔之事。”
这句话可谓失望透顶,不只是王琅对她,更是他对她。
“以你一己之力要杀王邢笑是天方夜谭,所以借鲛人之手是最快捷便利的。你根本就没想过要救鲛人族,不管成功与否,你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只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便要负王琅,负长元,负许多人曾对你施以援手的善意,还有……”
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他将君子协议交给她,放手让她去报仇,是想让她成为那个“我就是我”的望舒,而不是第二个秦昭雪,更不是第二个萧演。
爵微一时气闷,眉心攒聚成小山头,看她这样自然气愤,气到最后亦是无奈。他想转身就走又不舍,忍了忍,又逼着自己回过头去,不搭理这狼心狗肺的小东西,谁知刚抬脚,她又走回来,瓮声瓮气地告饶:“你别走,我……”
他当真是一丁点儿气性都没了,又和她讲起道理。
“你看过许多书,可知人间的宋仁宗赵祯?”
望舒摇头,他便与她细细说起宋仁宗在世时的政绩,最后道:“他那个时代被后人传颂为仁宗盛治,远过汉唐,风采无人可及,得到过当世多名才子赞美。他驾崩后整个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小到乞丐稚子也为他焚烧纸钱,哀悼痛哭,全因他在世四十一年没有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很得民心。”
“我不知你怎样看他,这个人政绩一般,只是给了百姓想要的太平,如同王琅给了鲛人族想要的安定,所以他此番离去,鲛人族上下痛哭不舍。也正因宋仁宗做得太好,之后历任帝王都不曾得到如他一般的称颂,还常常拿来与他相比较,所以你该知道,王琅之后,鲛人们再也无法像信任他一样信任后面的历任族长。”
“可是做与不做,做得好抑或是做得不好都是其次,最主要的是你该明白,你的选择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报仇,还是真心为鲛人族设想?”
“如果你只想报仇,那便一心一意地去报仇,不要拿其他人当靶子。一千个人不要,一百个人不要,十个人也不要,一个人都不要,就一心一意地去杀敌人,那样报了仇才得劲,才解恨。”
“望舒,一步错,步步错,我今日跟你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抛弃一切他人所想,只扪心自问,你扛得起吗?这么多条人命,这样的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你敢吗?”
“如果你真的不敢,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望舒摇摇头,她很累,推开他朝外走去。
西海是吴歌的故里,鲛人族是王琅的心血,天下无战是爵微毕生的心愿……他们都曾对她有恩,她究竟该怎么做?
距离天亮只剩两个时辰了。
由于大战,水晶宫内外破败,尸首还未清理干净,虾兵蟹将介入不了鲛人族这种相对他们而言皇室阶层的事,也不知杨巍被掳,心特别大,正背靠着背睡大觉。
她走到一个老龟身边,见他断了四肢,翻不过身来,不停地低声哀怨,正要上前帮他一把,忽然从旁边蹿出来几个老弱病残的战友,相互帮衬着将他翻了身。老龟赶忙吐出一大串气泡,也不说谢,傲娇地抬起下巴,几个老友便挨个爬上他的背,骑着他浮上海面,逍遥自在地享受月光。
不久前的杀戮血气还未消散,死亡近在咫尺,他们却全然不在意的样子,活着一刻,享受一刻,生存一刻,酣战一刻,喜怒哀乐都是这样自由随心。
望舒不得不扪心自问,她想要怎样的生活?想起离开长庚岛时周臣对她说的话,又是满腹困惑,为自己而活,心中有爱?
所以宋仁宗是真心为百姓着想,王琅也是真心为鲛人筹谋,他们都爱着自己的子民,因为爱才能深得人心,对吗?那么王邢笑呢?她用媚术和蛊毒来掌控人心,这样不是更易掌控吗?
究竟何谓爱?
望舒再往前一步,一脚从湿滑的礁石上踩空,摔进海里,顷刻间被翻腾的海浪淹没。她干脆展开手臂,任由自己被海浪推来推去,寻找自由的感觉。
月光就浮在头顶上,远远地有清风捎来暗香,她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一番场景,万年老榕树下的棋盘,对坐的一白一青两名男子,皓皓月色,漫山冷雪……温暖与之同来。
望舒瞬间清醒。
不知何时爵微来到她身后,以热流推动她在海浪中起伏,某一刻钻出水面,踏浪逐月而去。望舒如驰骋在草原的烈马,翱翔在天空的雄鹰,浮游在世间的尘埃,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自由”二字,那感觉令她酣畅淋漓,浑身发烫,好比新生。
她像是第一次去市集的小孩,被各种新奇花样吸引,转不开眼,高兴得眉飞色舞。
“你看到了吗?刚刚在我眼前突然钻出来的一条大鱼,它好大好大,通体雪白,太好看了!”
“我好开心,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鱼,像风暴一样。”
“海上的月光是我见过的最明亮的,比长庚岛后山成片的星光还亮,还璀璨……”
她说到后面也意识到自己高兴过了头,脸一阵阵潮红,显得很不好意思,爵微却觉得这样的她才是真实的、鲜活的,充满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应该有的明艳,十分耀眼,耀眼到他几乎怔忪,想将手臂收紧,实实在在地拥住她。
念头一经而起,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虽然只有一瞬,但他不得不承认,看着她笑起来的那一瞬间,确实动了歪念。
歪念让月色变得含羞带怯,缩回了半张脸,泛着点点星光的茫茫大海暗淡了几分,却徒增暧昧。他们拥在一起,隔着很近的距离,鼻尖对鼻尖,呼吸纠缠呼吸。
热闹之后的安静里,一切小心思都变得敏感而细腻。
望舒往后退一步,他下意识地往前一步,寸寸相近就是不放手,她羞了恼了推他一把,却反倒被调皮的海浪又打回他怀中,这一回真是身体贴着身体、皮肤挨着皮肤地亲近了,距离已到零点,不能再深入。
望舒的呼吸一道比一道沉,心脏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我……”她浑身好像被火烧一般,脸红到脖子根,“不知道修罗大人找不到我,会不会担心。”
现下的暧昧里,她顾左右而言他,说起煞风景的话。当日在雪园,一直不离她身的修罗被派去保护青草精,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知道是不是被王邢笑的暗卫发现,出了什么事。
“你放心,梭罗子尚在蓬莱,不会让他们有事的。”
“嗯。”
她点点头,一个话题过去,两个人再度陷入尴尬。
过了会儿,望舒鼓起勇气抬头看他,说道:“你先前的话,我……我隐约有些明白,也不是很明白,但我还是想接掌鲛人族,想手刃王邢笑,想替阿爹报仇,但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我想试一试,试着找一找我真正想要的东西,试着明白何谓爱,何谓大爱。”
两个人四目交接,有的没的欲望一下子都蹿了出来。月光又变得明亮,涛声滚滚,白浪翻腾,然种种喧闹都沦为陪衬,不及这一刻,这一刻的靠近浓烈。
还是爵微先回过神来,往后一步拉开与她的距离,却没有离太远,将近不近地护着她,以防她再被海浪冲走。停顿片刻,他回应道:“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的我是对的,吴歌是对的,王琅也是对的,那么今时今日走上这条路的你必然也是对的。我不信因果报应,只相信事在人为,这片天地往后就交给你守护了。望舒,向我证明你是对的。”
望舒心中一动,忽然想起无间狱中吴歌对她说的话,他说曾有一个人告诉他,鲛人天性纯良,所流眼泪皆是珍珠,所以一直到最后他仍心怀期慕,一直咬牙活着,就是为了等一个答案,后来他终于等到了——他的兄长不会错。
那个传说中真的无尽温柔的南珠侯,永不会错。
这一刻,她莫名地、无比坚定地相信他,他不会错,她也会是对的。
她浅浅一笑,有点儿孩子气:“今夜月色真美。”
爵微低头摸她的脑袋。
确实,今夜月色很美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