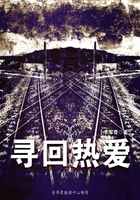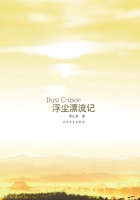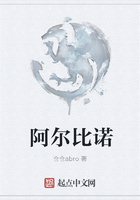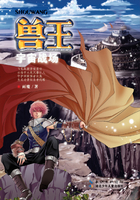像拍一个人一样拍雕像
像拍一个雕像一样拍人
这不是克里斯·马克告诉我的
Dear R
有一天我在读布列松。他说,有两种摄影师,一种拍出好的负片,一种拍出好的照片。
这和我想的一样。有一些人永远要在技术上达到正确,但是有些人追逐的是状态的正确。我要的是后者,前者是我的辅助。我一直认为,模糊的模糊可能是精确,而精确的精确,很可能是尽头。
新的艺术形式、观看方式的降临,增加了人们观看这个世界的可能性。高分辨率,高速摄像镜头——这种对自然的时间以及自然的观看进行放大、推近、定格、延展、扭曲的创作行为,实质是我们这个时代向时间作伪证的新的方式。
在绘画过程中,只有当这一笔下去,是回应本质的,这一笔的清晰才是有效的。我们所见的清晰,更多的是无效的清晰——清晰作为一种泄露,使事物失去遮掩。越来越多的解剖就是越来越少的秘密。信息被挤压,想象空间被压制。清晰是一种焦虑。清晰剥夺了临界状态。
技术自身的裂变与迭代的速度,是无可阻挡的。我们的感官正迎向新的开关,以及阈值。瞬时的愉悦与恐惧都会被进一步激发与计量。会来的,这一天。但如果我们随时都能触碰感官的极限,那么这样的感官也一样会被取消,因为它们不稀罕了。
在技术的时代里,我的厌恶总是数不尽。我厌恶因无根的概念而生成的艺术,厌恶轻巧的创作缘由,厌恶投机的艺术行为。厌恶愚蠢的策展人和画廊,厌恶某些艺术家。或许我是古典的,或许我并不能从这个时代获得我倾心的那种愉悦。
我有时候在想,人类是否正面临这样一种伦理困境:当视觉图像清晰化的技术水平超越了自然人类能负荷的程度,人便逐渐放弃使用自身的视觉机制(视网膜传导大脑),而选择芯片传导图像信息的机制。技术把人驱赶至肉体的极限——要求眼球接受更高的帧率,以此获得更多的信息。人类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选择——维持自然的肉体还是进入下一种观看方式——基于硅元素的观看。
当新的观看境遇出现时,人如何安置自己的目光呢?清晰化以后,什么被确认了,什么被禁阻了?技术是否延展了人的自然人部分,成为我们身体的新的经验?或者说,技术是否成了被赋予思想的义肢?这其中有没有一种边界?人如何面对自然人经验与新经验交织在一起的存在状态?这些问题,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带着一些惶恐,当然更多的是好奇。我好奇未来我没有机会看见的世界。我也嫉妒未来我没有机会看见的世界。
我们的眼睛早就被宠溺了。不会有偶像了。偶像出现,是因为大众准备好了。而我们不可能准备好了,就像现在。太多的清晰又无用的图像在流动,来不及厌恶,更别提等待。取消偶像的方法就是放置一百个偶像。
如今的艺术躺在取消艺术的伤痕上。从玩笑到宣言——宣言被重复——重复落入日常话语,落入架构性而非本质性的体系里。架构不是本质,本质是最深处的流动的石头。
马丁·泽尔在《显现美学》中谈到鲍姆加登时,说:“混沌并不是作为清晰性(Klarheit)的反义词提出来的,而是作为概念命题式认识的可区分性(Distinktheit)的反义词而提出来的。审美认识所谓达到的是与科学认识截然不同的一种精辟性(Pr?gnanz)。前者的成就对后者构成补充。因此,在鲍姆加登看来,一种‘完满的’认识只有通过科学兼审美的思考才能达到。”也就是说,审美不是一种单纯的分析活动,而是“为了通过密集的直观让它当下化”。认识一件事物,同时不去区分一件事物,从而完整理解一件事物,这成了此种混沌的感性认知的奥义。
的确,在光之中去除阴影,并不见得使一切更为真实。真实需要争执,需要张力。
人类观看的进程,是一个清晰与幽深的争执过程。光与影,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张力。清晰与幽深,也是一种张力。而穷尽清晰的行为,把这样一种张力减弱了。智性的理念无法洞穿的,光影二元论无法解答的,恰恰是那些在明暗中闪烁的动词。这个动词是等待,而非清晰化。
当一切都惨白地被照亮后,剩余的美感是什么?原有的被注视的事物,经由我们的双手、双眼的攫取而消失的过程,便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学享受。消失的美感,每一代人都在体会,但并不是每一代人都能亲见到加速燃尽的烟花的最后一程。
没有秘密的图像最无聊。秘密在数量巨大的数据里被稀释了,然后被淡化为概率。没有诱惑与被诱惑的人生太长了。
W
记于W 24th 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