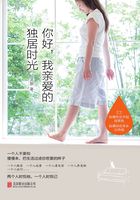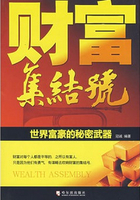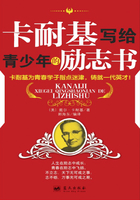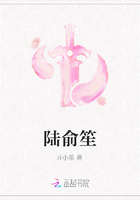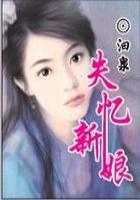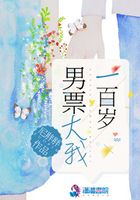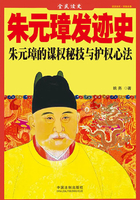1
第一次收到小孩满月酒请帖时,我读大二,二十岁。
小孩的妈妈是我的初中同学莲芳。我惊讶于她的邀请,毕竟和她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记忆。
初二那年,莲芳和我同班、同宿舍。莲芳是这个乡镇中学里少数长得好、会打扮,拥有MP3和诺基亚手机的女同学。
她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少女,却是其他同学眼里自带主角光环的传奇。
她打架,逃课,公开交男朋友,经常夜归或干脆夜不归宿。因为舍长的身份,我时常和她起冲突,却时常败下阵来。
每到周末放假,就有男生骑摩托车来接莲芳。莲芳和其他几个女孩坐在摩托车后大笑着绝尘而去。
与我结伴走回去的女生,在飞扬的尘土里咳嗽着。有人羡慕说:“要是我也有人接,不用走路该多好。”
我说:“不用羡慕她,那是停滞不前的虚张声势。”
初三,学校将班级重新编排。我和莲芳分在不同班,总能听到她逃课被批评处分的消息。中考时,逃课好几天的她被父亲押着来考试。
后来莲芳和男朋友一起去深圳打工,她的校园传说渐渐被淡忘。直到她结婚生子,请我们去喝满月酒。
我没参加,给她寄了一套孩子的衣服。
到场的同学说,莲芳她老公在酒席间闹起了脾气,很不满莲芳邀请那么多老同学,说多摆几桌又多花两千块。
一向泼辣的莲芳在老公的责骂下没有出声,默默流泪。
老同学悄悄在给孩子的红包里加重了分量,希望她老公不要太难为莲芳。
同学们感慨莲芳变化很大,她现在这么没脾气,完全不像当年那个她了。打开她的QQ空间,看她手抱女儿低眉顺眼地笑,我有点心酸。
2
摆满月酒是莲芳的第二胎,第一胎生的是女儿,那年莲芳未满19岁,没有满月酒。
三年多过去,她的相册从青春时代洗剪吹式的飞扬跋扈,到一家三口的合照,虽为人母,却稚气未脱,眉目间的泼辣荡然无存。
生下第一个女娃后,莲芳辞职了。他们一家三口在深圳某个城中村的一个单间里住着,老公是工厂工人,她在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偶尔带孩子逛公园。
她的空间说说从努力赚钱的口号变成了对孩子老公絮絮叨叨的抱怨。
闲时她会上QQ,偶尔找我聊天。
莲芳问我:大学生,忙吗?
我:没有,在搜些期末考试需要的资料。
莲芳:好有学问。
我:恭喜你,都结婚生孩子了。
莲芳:是啊。不过是女儿。
我:男女都一个样。当时没考上高中,怎么不去读技校?
莲芳:不想去。读技校后还不是要出来打工,还不是要找人嫁了?我现在挺好,老公养着,不用工作。不过,还是在学校时好呀,没生活压力。我习惯自由和潇洒,读书不适合我。
莲芳:孩子醒了,我去喂奶。
我:去吧。
我想,即使再回到过去,很多人也是无法改写命运的。很多人或许都和莲芳一样,只想回到那段青春时光再享受多一次放纵,而非改变。
莲芳只想延续青春期的放纵和浪费。放纵之后,把人生一切变好的可能都押在一个男人身上,押在一次婚姻上。自己所有改变的可能,也都被屏蔽掉。
然后,生活给予的回答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谁能拯救一个对生活举手投降的人。
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工作,需要抚养孩子,老公粗鲁,当众嫌弃她——她的生活陷入困境,却无力挣扎,被凌乱和困顿拖着走。
生活的每一步,把“别人”计算得太实在,就容易缺少那点未知的可能性。未知,往往不是失败和痛苦,里边还有希望。放弃选择未知,一开始就是失败。
习惯的力量很大,当你习惯走同样的路,吃同样的饭,见同样的人,那样你会错过另一条路上别样的风景。
过早地习惯放纵和享受,就容易错失努力带来的“生活的控制感”,就容易缺乏对未来的“期待和欲望”。
另一条路或许并不难走,可能是路上的一处拐角,也可能是原来路上的往前两步,为什么不试着走一下呢?
3
与莲芳对生活的“实在”态度刚好相反,朋友小A几乎看破红尘。
小A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当柜员,每天的工作就是点钞票、拉业务,给客户送点小礼品,然后再点钞票。
一年半前她击败上百名竞争对手,获得这个岗位。本该是众人羡慕、薪资丰厚的工作,没想到才一年,她就感觉到生活很无聊,日后几十年一眼看到底,她活得很无力。加上同事间对客户量的竞争,父母对她单身的不理解,她觉得身边的人很冷漠,没有人会帮她,没有人和她交流,她充满了无助感。
她说,有时想想,生活也就是这样了——苦难的、辛酸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往复。
她跟我说这话时,感觉像苍老了十几岁。
为什么不自己先去交流呢?为什么不先求助呢?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给自己一点小惊喜呢?
去买一束花,去参加同城的跑步活动;或者只是去书店、咖啡厅待一天;抑或来一场短途旅行。
只要度过这个无望的时刻,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活在这世上,总要有点活下去的欲望。这点欲望可以是变酷、变美,赚很多钱,有个男朋友,有个女朋友;抑或只是下一顿吃什么,明天换什么发型。
如果那件事让你有快乐或期待,就多想想,然后去做。
没有一点变好的欲望,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改变,你也很难做出。
生活,需要在不断地打破和建立平衡中,寻找和建立越来越美好、自信、舒适的自己。